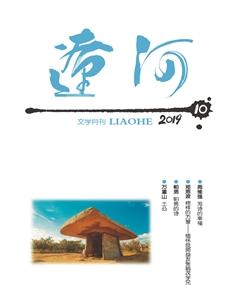土公
万重山
一
大港村有一座古厝,五十年前住着一个人,五十年后,仍然住着那个人。
这个人有一串不正经的外号:“流涎啊大头旺”“流涎啊”“大头旺”,很多时候,人们更喜欢直接叫他“旺啊”。
旺啊“无某无猴”。“无某无猴”是闽南光棍的标配,没有老婆,家里连只猴都养不住。旺啊是一名土公。土公当然不是土地公公,土公是把死人正式公开有仪式感地送走的人。平日里村民们看到他,就像古代细民撞见县太爷出巡时走在队伍前头鸣锣开道的衙役高举的那两张牌,“肃静”“回避”。你没事找土公干嘛?找他时,大半说明你家里有人归天了。
死者为大。死是一件悲伤的事,郑重的事,只有神经线瞬间短路的人才会“鼓盆而歌”。曾经有个小年轻死了爷爷,在棺椁前手机自拍发朋友圈,结果被叔叔伯伯们劈头盖脸掴成了猪头,在网络上获赞超万。也真是的,你从哪学来的这么冷血?人生在世,多久才死一回啊!
话说这一天,到底哪天就不翻日历了——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镇上的老王家死了九十八岁的太爷,按理说老老王已远远地赢在了人生终点线上了,属喜丧,应该走简单程序,火一烧就完事了,活着的人继续没事人一般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但王太爷的子孙偏偏要扮古装,要讲排场,想用钱一沓一沓垫起一把登上天堂的梯子,以此尽到最后一孝。于是,“拜脚尾饭”“点脚尾烛”“做功德”“辞生祭”“送脚尾”“引空魂”等风俗仪式,一个都不落下。哭啊哭,拜啊拜,绕啊绕。丧属中的零零后绕棺绕得晕了头,失了耐性,抱怨说,都微信时代了,人间早就改用手机支付了,天堂那边怎么搞的一点改革的动静都没有?要不然用手机刷点买路钱给上帝不就得了……家中长辈竖起眉毛厉声斥道,闭上你的乌鸦嘴!不懂,就不要歪歪唧唧!乖乖一边去,听旺伯安排。
旺伯,就是旺啊、流涎啊大头旺。平日里大家没大没小地旺啊长旺啊短,仿佛他是一根横在路面的稻草。现在是关键时刻,可不敢这么干,得改口叫旺伯。毕竟上天堂这条路竞争剧烈,很拥挤,岔路纷纷,万一流涎啊大头旺心情不好或打个喷嚏,后果会很严重的。
丧礼进入“分手尾钱”,旺啊将事先放在死者衣袋中的若干铜钱取出,按房头均分给死者子孙。接着“祭棺”,丧属备牲醴祭奠,道士诵《劝亡经》,孝子孝妇跪爬棺材三九二十七圈,再回到棺前哭拜。一切按旺啊的指示办,该怎的就怎的。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封棺”,只见旺啊大手往后一压,高喊一声:停!满堂哀哀戚戚、撕心裂肺的悲嚎声戛然而止,像突然停了电。孝子贤孙个个丧服加身,挤挤挨挨地聚拢在以他为核心的灵堂里,目不转睛竖着耳朵听他发号施令。大头旺一边钉棺材一边唱吉语:“围甲圆圆圆,给您内外儿孙一代比一代大赚钱!”丧属齐应:“好啊!”“围甲密密是,给您内外儿孙吃百二!”“好啊!”“好运来坏运去,给您内外儿孙个个出人头地!”“好啊!”……气氛凝重,场面肃穆,呼应整齐有力。个把顽童以为是在玩游戏,咯咯咯笑出声来。他们的小胳膊立马被捏出一块青紫,耳边传来一声闷雷:闭嘴!
众人膜拜的眼光热乎乎的,大头旺感受到了,他想极力保持住一脸庄严,可惜一张口,老毛病又犯了,涎水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顺着左嘴角边淌了出来。他嗤溜一吸,却没有完全成功,涎水的大部分被他吞咽进肚子,另一小部分却溅到棺材上,洇湿了一片。他装着不知道,挺了挺腰,站直了,吐纳一口气,又接着钉。忙乱之中,他把封钉的顺序给颠倒了。本来应该先钉脚下后钉头上才对,结果他却先钉了头上,钉下去才发现错了。这是个极其严重的人为安全事故,王老太爷的命运可能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从云端跌下地狱,下油锅去了。大头旺大有愧疚之意,手脚发凉,额头冒出了阵阵冷汗,脸膛刹那间变成了猪肝色。丧属以为他尸气中毒缺氧了,一杯热茶早端到了他的唇边,一条崭新的白毛巾几乎同时递到他手上:旺伯,您歇下!旺伯,您擦下!
丧礼办得如此风光、妥帖,给足了丧属面子,到了最后和最关键的那一幕,丧属说,多少?大头旺说,我打直拳,“淡薄薄”来落好。“淡薄薄”就是不用多,跟穷人家祭拜祖宗的水酒浓度差不多……他每回都这样说。手接过红包就当场拿捏,嘴里连说好,好好,嘴角的涎水,滴,滴滴。给少了的丧属看得心里难受。事后,有人说流涎啊这招聪明,什么“淡薄薄”?那是反话吧。既巩固了市场,又体现了他全心全意为死人服务的态度。看来,世间最聪明的人,当属憨人。当然,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他的出场费也水涨船高。原来只是“带红”,给点小红包,两角、六角、八角,一块六,两块、六块六,后来是六十、八十、一百,现在是两百、六百、八百……一路看涨。拿四十、四百的很少,四跟死是谐音,家里刚死了一个,缓一缓吧。
死者到底有没有得到那个上帝的许可上了天堂,再议;但他眼前的上帝掏钱掏得出来,也掏得心甘情愿,还将吃不完、用不上的东西尽数送给他。鸡、鱼、猪头等三牲,苹果、梨、葡萄、柑橘等水果,糖果、碗糕之类的东西,丧属都会慷慨地馈赠他。还有一些死者生前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物件,谁敢要啊?你要什么都拿去!他也不忌讳,照单全收。已经低到尘埃里去的人,你还想对他说东道西,省省吧。
二
大头旺的院子和十几座被遗弃的燕尾脊古厝连成一片,被称为“社内”。近几年来,“社内”的原住民陆陆续续搬到公路边建上宅下店的楼房或者到新村点住别墅样的楼房去了,因此,“社内”也被形象地叫做“空壳村”。大港村的这个“壳”里,还有生命活动的迹象。大头旺,算一个。还有几只野猫,它们是那几座老旧甚至坍塌了的燕尾脊古厝的主人。也不知咋回事,大概今年桃花提前开了,或者他要走桃花运了,这几天,野猫们闹得特别凶,一到更深人静的时刻便集体发情。叫声像刚出生的婴儿啼哭,时高时低,丝丝绕绕,缠缠绵绵,传得特别远,也特别往他心里去,扰得他死心睡也睡不安稳。他踢开被子,恨恨地骂道:死猫,死猫,骗死人没当过猫!
前些天死人相对密集,猪头吃不完,他便卤起来,酝酿着搞一次大型的宴请,请山上县火葬场的人下來喝喝烧酒,一来解解闷,二来顺带积点小人情。他们经常关照他,给他提供致富的信息。有一次,县城一栋32层公寓的顶楼死了一位老阿婆,丧属不让乘电梯下来,说是有下地狱之嫌。谁背下来?孝子贤孙个个摇头。山上的老梁获悉后,立马想到他。那次丧属给了他3200元。后来老梁他们分析,丧属大概是依据现行房地产的价格,即每上一个楼层每平方米加价100元的标准来计算的吧。
流涎啊大头旺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顿请,居然请出了一位水渣某,破了他六十年不败的童子功。
接到大头旺宴请的电话,山上的人一阵狂喜,他们已经好久没用酒精润滑一下肠胃了。也难怪,谁吃饱了撑着要请火葬场的人?
老梁是运输队的副队长,运载的主要是尸体。老梁是大头旺宴请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一听基层一线的土公要请客,他便千叮咛万嘱托:行,行。你就江螺炒一盘、芥菜砍一棵,卤肉有吧、鸡有吧、鱼有吧。行,行,就这些,够了,多了我们下次不敢去了。完了还和蔼地交代,酒,你就不要买了,我们自己带去。
锅炉工老唐听到大头旺说晚上一起嘬江螺时,正通过机台往一具尸体上浇油。一点火,那尸体突然弓身坐起,像活过来一样。老唐左肩一耸将手机压在耳朵边,双手一长一短拨弄长铲,三下两下把它捣平了,大声说,好啊,好啊!多叫几个人热闹热闹。
殡葬车司机老毛接到电话时,正载着一副棺椁和十多个丧属。老毛也不顾忌什么,高兴地嚷道,吝啬鬼!还嘬江螺啊。
请他们,一盘热炒江螺是少不了的。要江螺还不简单,旺啊院子前的小河石缝里,摸一会儿就一大面盆。那天他还摸到几只小河蟹和大头虾,它们也喜欢躲石缝里。大头旺把江螺抓来,在水桶里静养三四天,让它们吐净肚子里的泥垢,尔后洗净,剪去尾巴,放姜丝、蒜头、油葱、酱油、辣椒、少许的醋、白糖,甩上一点白酒,热炒。每次见他们用筷子或手夹上一粒,左嘬过来右嘬过去的那种满足和惬意感,你会觉得世上再无美味佳肴了。
老梁他们下班后,家也没回,便统一打的下了山。老唐又约了县城开寿金香烛店的老五。山上的这些大土公们难得出笼一次,他们事先约定好了,要扮演“假包”出巡,乌龟扮包拯,以壮声势,一洗平常被人漠视、被人鄙夷、被人轻薄、被人践踏之耻。他们往往陶醉于自己的尊严指数在丧属装出来的信赖甚至敬畏的短暂时光中呈现出的报复性反弹的自我感觉中,而一旦下山,他们需要宣泄,需要制造一种虚荣的自慰。他们称块头大的、国字脸的老唐为阮县,啤酒肚、头发梳得油光连蚂蚁都休想爬上去的老毛为陈局、长得清秀白净的装殓师小高为王局。为了掩护最高级别,老梁的头衔为汪股,官职最小。其他几个临时工也副乡、副所、副站地乱叫。他们的头衔都没有具体单位,也没有一个正职的。正职的,人们容易对号入座,被人识破。
大港村的村民哪曾见过这种架势?只知道流涎啊旺啊跟这些“头家”常有走动,也算朝中有人,从此以后看他的眼色自是不同。
土公见土公,彼此不忌讳,烧酒热烘烘。他们在酒桌上杀了几个回合之后,有些人讲话就不那么着调了。
你说,活人与死人的区别是什么?
这不简单。断气的是死人,还没有断气的是活人。
错!我告诉你,你认识的人,是活人,你不认识的人,统统是死人。你的周围有太多的死人,世间上有太多太多的死人。你知道吗?
什么话啊!喝!
也有略懂文词的搖头晃脑吟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
花酒不曾离,
醉醺醺酒淹衫袖湿,
花压帽檐低,
帽檐低,
吃了,穿了,是便宜。
……
对对,讲得很实在,很有道理。吃了,穿了,是便宜!干!
桌子,是摆在院子前临河的红砖大埕上的,他们临时拉了电线:用竹竿撑起一盏灯,飞蛾禁不住灯光的诱惑,雪花似的从黑暗中赶来奔赴这场盛宴;一条碳烤过的鱼正在被众多的筷子肢解。几个男人伴着音乐,在大埕上或激情或柔曼地唱歌跳舞。几个“领导”刚开始很拘束,正襟危坐。主持人老五抢过麦克风说,请各位“领导”唱起来跳起来,晚上是来开心的,不是来开会的。音乐震耳欲聋,几个人很快被拉下水了,张牙舞爪,煞是搞笑。中有一人,他们叫她小燕子,看样子也就二十二三岁,长得高高的,穿超短牛仔裤,露脐造型,两腿一片白,是足以把一本正经撕得稀巴烂的白。大头旺睃了她几眼,睃得他眉开眼笑,睃得他脑洞大开,嘿,嘿嘿,嘿嘿嘿……嘴角的涎水如瀑布般不要命地扑到地上去。旁边的老五见猪八戒又转世了,连连捅了他几下,他才回过神来擦擦。这时,有人叫小燕子喝酒,她说已经喝到脖子上了,那人一把拎起她。大头旺见状,手一拦——喝不下去,就不要为难人嘛!
大头旺还英雄救美!行,她的酒,你喝!
临别时,小燕子摸了一下他的头,眼神迷离打个酒嗝: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三
日头,挂在西边的大帽山巅上,起初是圆的,像烙红的烧饼落在苍茫的天地间,后来被谁啃了一半,眼看着另一半也要被吞下去了,他才想起一件燃眉的事——他已几天没洗澡了。
早上,他拨通了她的手机,邀请她今天晚上到乡下来共进晚餐,还以客户经理的口气说道,我打直拳,路费多少,我给你报销。好像知道他早晚会打这通电话似的,她嘻嘻地笑了,行啊,行啊,大哥,那你发个红包过来。他说,只懂手机的接和打,不会微信。那边又嘻嘻地笑了,老土哦。
大头旺的家是一块风水厝宅,用闽南话说,不是一般艰苦人建的。它坐北朝南,单进一厅四房(前后房),屋顶很特别,别人家只有两个左右高高翘起像燕子尾巴似的屋脊,他家又多出了两个燕尾脊,这种造型叫双脊吻燕尾。主房的左右两边各伸出一间灶房,中间是庭院。院子里堆满了死人用过的破旧床板、桌子、柜子等家什,它们被丧属扔到河里或路边,他一板车一板车拉来劈作烧柴。那晚小燕子见他烧柴煮饭,高兴得直叫,柴火饭呀,柴火饭。院子的围墙一人多高,上覆绿沉沉的琉璃瓦,镂空雕刻着嫦娥飞天、八仙过海、龙凤呈祥等图案;围墙外一片坦荡荡直逼河岸的红砖埕;岸边是他用篱笆和渔网围成的一长条状的菜园。此时,菜园里青翠得流油的蔬菜,鲜艳得着火的花朵,正和着彼岸低垂柳丝的节奏一起在风中向他招手、向他点头。
流涎啊大头旺扯下墙壁上挂着的一条死人用过的粉黄色浴巾,围着裤裆往河里跑。院子里的两只鸡正张开两翅“咕咕咯咯”叫着。大头旺差点被它们绊倒,他来了气,一脚将它们踢翻。
他趟到河里,等河水没到肚脐,便蹲下身,解下浴巾。一只喜鹊站在岸边的柳枝上跳舞,见他拼命左搓搓右搓搓,像要把身子褪下三层皮,荡起的涟漪比母牛大,吓得喳喳直叫。
暮色起来的时候,他走到灶房,用心用意炖了一大锅猪头骨绿竹笋汤,炒了六碟小菜,在房中摆下桌子,碗盘排列齐整,热气腾腾地等着。
左等右等,菜凉了又温了好几回了,仍不见她的踪影。打了她的手机,没回。不会出什么事吧。会不会搭上黑车,被……他开始不安起来,又拨了她的手机。回复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过后,再打,有时候开机,没回。有时候,关机。搞什么鬼嘛!不来就说不来,打直拳不就得了。看了下时间,已是晚上十点三十七分,她一定不会来了。
夜,已深,外面的世界漆黑一片,几声狗吠兴奋了他的神经。他走出院子,在大埕上四处张望。一个捕蛇的头戴矿灯正在河对岸寻找蛇的踪迹,一条蛇逃往河心,在灯影里荡开两行波纹。四周的蛙鸣,咕咕呱呱,此起彼伏,像潮水一浪接着一浪向他涌来。
他踱回房间,桌上并肩排着的两只酒杯,两个碗,两双筷子,它们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他也可怜巴巴地望着满桌子的菜肴……
晚上没戏,洗洗睡了。
大约下半夜四点钟,大头旺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拍院子的大门。大哥!大哥!
门,刚打开一条缝,他等待的女人就像聊斋里的女鬼轻吟一声飘了进来。
原来她每晚都要赶场,他这边是晚上第五场了,因路途远一点,她安排在最后。
银河,在寂静的乡村,在燕尾脊的屋顶上空跨过,繁星闪烁,牛郎织女听到了凡间的两句台词。
我打直拳,我身子很脏……不是洗过澡了吗?哦,是他的涎水如山洪暴发了,还是他受过三千女尸的辐射?
我,比你脏……声音像从一座幽暗的大山下挤上来的。
四
纸是包不住火的。小燕子虽然年轻貌美,惹人怜爱,但她这种行业毕竟是不光彩的。民风淳朴的大港村,哪能容下这种行为。这有伤风化,有违祖训,离经叛道。流涎啊旺啊何德何能?“吃来六十土,还会睡水渣某!”六十土是六十出头,水渣某当然是漂亮女人啦。几个老家长、族中长辈看不惯——他旺啊一个贱人凭什么,轮也不该轮到他——约齐了到他家来兴师问罪。
你那一只是坏只,赶紧甩了吧。他们把小燕子当成狐狸了。
旺啊大头加流涎,长得实在对不起陈元光。大港村有五千多人口,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后裔。旺啊穿的都是死人的衣裳,又经常几天不换,邋里邋遢,阴气太重。本地曾经有几个残疾寡妇,见他始日勾着一颗大头,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在瑟瑟的风中拖着一条棍子似的身影,实在可怜,便起了下嫁他的念头。没想到旺啊居然一个也对不上眼,还在心里埋怨人家看扁他,话讲得很难听,说,您爸是捡尸体的不是捡垃圾的……媒婆脸上挂不住,气得牙痒痒。过后,妇道人家疯传一种说法,说他亵渎过女尸!几个妇女本来是同情他的,一下子变成憎恨了:死夭寿啊流涎啊!你还是人吗?
唉!人嘴毒毒的,直铁棒传来传去也会变弯。旺啊“本地猪屎——无肥”,可怜祖宗给他筑下的大巢,他连一只雏鸡都没引进来,更别说啥火鸡、凤凰了。
大头旺被老家长们骂得蔫头耷脑,好像被泼了满头满脸的屎。他一急,涎水汩汩而出,梗着脖子反驳道,您爸娶婊来做某,卡赢别人娶某去做婊!——闽南语中,“某”是老婆;“卡赢”,是赢过的意思。
大港村陈氏家庙理事会会长陈孝全,曾经当过大港大队革委会主任,他的儿媳妇出台,他家才盖起了楼房,这已经是全村不公开的秘密。大头旺一句话戳到他的心肝。老陈恼羞成怒,便挖了他的老底,骂道,臭地主臭狗屎!
您爸的事,关你们屁事!
大头旺嘴巴硬,但心里虚。陈孝全的余威还在,他见到陈孝全还会产生条件反射。那个年头,陈主任叫他蹲,他不敢站,甚至他憋了好久的一声快出肛门的屁,见到陈主任也慌忙泄了气,蹑手蹑脚从肠子直通裤管溜出去。他一家人被整惨斗怕了。他的双亲在他小时候被斗没了,他无依无靠,衣食无着,便死鸡死鸭的找来胡乱填饱肚子。他嘴角流涎的毛病就是那时候落下了。后来当土公的外公见他可怜,便收他为徒。外公临死前将土公这一行业的武功秘籍传授于他,还拉着他的手说,只要你“认路衰小”,任何朝代干这一行都不会饿死!“认路衰小”,闽南语大概是认命的意思。
他怕陈孝全他们。服了,还不行吗?他不想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被“扫黄”扫到而晚节不保。他更不想让这帮人抓到把柄。
回过头来跟小燕子紧急商量这件大事,小燕子犹豫了。大头旺咬咬牙,把涎水擦干净,拍着胸脯说,我打直拳,你陪我过,每个月我给你六千元……
五
她说,超喜欢这里哟,有天有地,阳光和空气都是野生的,能够让心静下来。
她晨起浇菜,日落洗衣。她那些花花绿绿的衣衫、裙子、袜子、内衣,现洗现晾,就晾在河边的竹竿上,它们无死角地接受阳光的照射、乡村和风的吹拂,穿起来一身太阳的味道。
公鸡每日在草垛上仰脖啼鸣时,她铺开凉席就在大埕上迎着熹微的晨光练瑜伽,她感到浑身的细胞像一朵花儿一样,柔媚舒缓地展开。几只肥嘟嘟的麻雀旁若无人,边低头啄吃砖缝里的谷粒、蚂蚁,边古怪地看着这个长发披肩的尤物。
到了晚上,或泡一壶茶在红砖大埕上静坐,听手机播放禅音佛乐,或携手在花香四溢的河岸边漫步,或撑开小船,任风儿将他们带离村庄,枕着船头潺潺的水声入梦。她把闽南水乡的美景及时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姐妹们羡慕得直流口水,连连点赞。还说,还有没有像“姐夫”这样的人,也给介绍一个。她不怕姐妹们笑话,很实诚地回复说,流涎的,没了;瘸脚的,还剩一两个。
她们如果要笑话,就让她们笑吧。记得本地的一个名人说过,人生在世,无非就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让人家笑笑。
哦,差点忘了交代,她叫单燕,老家离这里很远,那里秋天一走鹅毛大雪就落下来了。离开老家的时候,她已办妥了离婚手续,一岁多的孩子由夫家抚养,她净身出户,恢复了自由身。前夫是好人,她不想让他戴綠帽子。他们是一起长大的,表面上骨头是断了,可仍然筋脉相连。她每个月都把几千元的“工资和奖金”寄给因车祸而瘫痪的丈夫。为了治病,丈夫把以前赚的钱赔出去不说,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债,而后继的治疗费用更让她筹措无门。家里还有两个病弱的老人,一个小孩需要照顾,当坐台小姐,灌酒灌到肠胃穿孔,你说,我愿意啊……那天晚上大头旺听得鼻子酸酸的,两滴很肥的浊泪来不及擦就滚了下来。
“婚宴”那天,“阮县”带领“王局”“陈局”等“领导”亲临捧场。大头旺懂政策注意影响,只小范围邀请了最亲近的人。老五带着一帮佳丽也来凑热闹,他好这一口,不可一日无“腥”。他炫耀地说,公园边老瞎给他算过命,说他的前生是皇帝。他说三千佳丽算什么,他这辈子的目标是五千。他的“正宫娘娘”原是县城开棺材店的窦建德的女儿,叫窦秋红,是出了名的美女。窦秋红见老五寻花问柳,夜不归宿,于是吃了几次安眠药死劝。他不仅不改,还将私生子带到这个不该来的世间。
那天老五当着大小土公和几个坐台姐妹的面给小燕子塞了一个红包,小燕子不尴不尬地收下了。以前的事,不是事。知道吗?以前她是大众情人,像一朵无主的野花,风可以来弄一下,雨也可以来弄一下,她始终都持开放的姿态,迎着风雨招摇。而现在她是朋友“妻”不可欺。人啊人,在这风火轮般快速旋转的年头,有时候装鬼,有时候装神,有时候就是鬼和神的混合物。
小燕子见旺啊鱼肉“死人”,几乎天天见财,抽屉里面的红包隔一段时间就塞得满格,不觉眼红心动。有一天晚上,配合旺啊完后,她突然按耐不住,强烈要求当一名土公。
孝男,闽南人讲究效率,哭丧的不论男女,统一叫孝男。孝男的责任就是哭,最好能把丧属的眼泪哭出来。她闽南话一窍不通,大头旺就教她专门唱芗剧《梁祝》“哭墓”那一出。她一字一句,一个腔调一个音节地学,虽咬音不准,普通话加本地地瓜腔搅在一起,但十二拜的腔调很快练得差不多了。
“……
九拜梁哥怨难平,
怨我出世做女人,
三从四德杀人刀,
重重枷锁不由心。”
听了这几句歌词,很多妇女的脚拔不开了,泪汪汪,眼光都转到她身上了。
她接着唱:
“十一拜梁哥天地转,
浑时浊世难容人,
英台拜哥十二拜,
抛弃人间与哥会瑶池。”
小燕子一身缟素,衣袂飘飘,唱着唱着,不知道流的是汗还是泪,妆被冲得一塌糊涂,数道血色的泪痕竟然从眼窝里被逼出来了。殡葬现场有一个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调控音响,适时地配以雷声隆隆,狂风大作。丧属和围观的村民至此,无不以手掩脸,哀嚎一片。
她扮演的孝男很入戏,哭到眼睛流血,惊动了“阮县”等“领导”,他们专程前来祝贺。“领导”们轮流握着她的手久久不放,心疼地说,你们看,你们看,小燕子同志晒黑了。说得小燕子脸红红的,呵呵笑着称感谢。他们见她热爱殡葬事业,脸上挂着从容和自信的笑容,竟比先前更加丰腴光润,心中自是喟叹:钱,既然可以将人变成鬼,也可以将鬼变成人。
阴历六月的一天,日头赤炎炎,好像烈火在田野上燎。狗,很识趣,不敢到处乱跑,吐着长长的舌头,闪在树阴或屋檐下呼哧呼哧喘粗气。中午的时候,阳光更是亮得刺眼,空气像要冒烟似的,人在家里哪怕蹲个厕所,也大粒汗小粒汗地冒出来,浑身黏糊糊的有一千种的不爽快。
小燕子和旺啊一大早就出门了,他们一起参加了李家的丧礼。李家早上十一点十六分就出山了,没有她孝男的事了。她便赶了另一场——下午一点十八分才出山的王家。她正跪在棺材脚作磕头状,甩出水袖,向天悲呼:梁哥,你死得好惨啊……就有丧属挤出来喊停,说,快快,出大事了!你們家旺啊可能不行了……小燕子来不及卸妆,甚至头上盖着的白头帕也来不及摘下,便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旺啊摔得头破血流,嘴角边流出的不是涎水,而是淋淋的鲜血。小燕子吓坏了。怎么啦?你怎么啦?早上好好的,怎么啦?凭她怎么呼天唤地,旺啊牙齿咬得紧紧的,就是一声不应。她把旺啊那颗硕大的头颅轻轻托起,抱在怀里……血,迅速染红了她胸前的白袍,白头帕低低的,青天高高的,大有霸王别姬之慷慨悲凉。想到相处才七八个月,却从此要阴阳两隔了,她不由得满脸悲容,痛哭失声。路边围观的群众不断涌来,数度引起交通堵塞。哎呀!实在可怜啊。是死老爸?还是死老公?有些平日里羡慕嫉妒恨的人,终于找到了将他们踩到脚下的机会,便大声喊道,都不是啦,是死“契兄”啦!“契兄”?“契兄”是奸夫的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瞧这水渣某哭得这么凄惨,您爸当这个“契兄”死也甘愿!大概是这句话,像一把钩子将旺啊那渺渺的魂魄勾回来了,他眼珠子转了一下,嘴巴蠕动着,在她耳边吐着三个字:尿,尿……桶……头,尿桶头……
什么尿桶头?她不懂那意思,但一下子记住了。有耳尖的村民也听到了,说,你们家尿桶里看有没有放金砖?她急忙岔开话头说,你听错了,他说要尿尿。说完,小燕子当场将他的裤子脱下来……正忙乱时,救护车“嘀噔嘀噔”到了。
县医院的医生说,他是脑溢血,幸好送得及时。
旺啊住了二十几天院后,医生叫他下床走几步看看,小燕子在后面哇哇怪叫:拐了拐了,瘸了瘸了。看来这老头注定要将破相进行到底,这次算是从头到脚,彻头彻尾破了相了。是啊,如果不彻底破相,怎么扛得住上帝和阎罗王都颁给他证书的那份重活?怎么可以既赚神又赚鬼的钱?
大头旺因病成了“新赖”, 奖金福利没给,还欠了她两个月的工资。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她不仅没有拎包走人,相反,还毫无怨言,服侍他饮食起居,屙屎拉尿。一天深夜,大头旺听到了一种异样的声音,嘤嘤,嘤嘤,起初以为是蜜蜂。又嘤嘤的,接连不断。他睁开眼,发现是小燕子在抹眼泪。看她眼睛肿肿的,玉容憔悴,估计已哭了好一阵了,便劝慰道:
我还没死呢,你哭什么呀。
小燕子哭得上气半天才接住下气——她做噩梦了,他的病情恶化了,瘫在床上起不来了……她很自责——我是不是前世造了什么孽,煞神出世的?害你们两个男人都得了瘫痪。
旺啊见她讲得体己,感动得老泪、鼻涕和涎水搅成一锅粥。
他挣扎着要小燕子扶他到尿桶旁。小燕子正要帮他捋下裤子,他站着不动,一手扶着墙壁,叫她到灶房拿一把铁锹来,要她挪开尿桶,挖,往下挖,挖挖挖。小燕子恍然大悟,尿桶头,尿桶头,尿桶头!她舒开玉臂,奋力挖掘,挖到半人多深时,果然发现有东西了——一个污渍斑斑的枕头,死沉死沉。抱到床上打开一看,哇啊,眼前赫然出现一堆金戒指、金链子、金镯子、金耳环……小燕子满眼金光闪闪,大头旺嘴角边那些已流出来了又吊在半空中转转悠悠的涎水,也成了金唾液了。
她愣怔在床边,胸口鼓鼓的,波浪似的一阵一阵起伏,喉咙吞咽的声音,很响。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就像眼前的金子在黑暗中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她说,想跟他商量个事……咱们的房子是现成的,再粉刷一下就行了,而前夫来也不会白吃,他可以坐着轮椅调音响,只不过你要委屈一些,当“大伯”。旺啊听完,不作声。半天,呵出一口长气:孩子要带过来,有孩子才像家。
屋顶上的天窗一片灰白。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