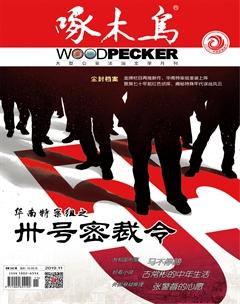张警督的心愿
【美】斯蒂芬·莱瑟 谢晓青 谢佳/编译

张警督刚从丰田空调车里下来,走进新加坡夜晚闷热的空气里,厚厚的眼镜片立刻蒙上了一层雾气。他抬头看着眼前这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一边用手帕仔细地擦拭着眼镜,一边等着李警佐走到他身边。他们一起进入饭店,乘电梯直奔六楼。张警督率先跨出电梯,踩到红得像鲜血似的厚地毯上。“往哪边,警佐?”他问。李警佐只有二十四岁,头发在脑后扎成小圆髻,试图使自己显得老成一点儿。她跟着张警督才干了两个月,仍然急于取悦他。她皱着眉头看了看笔记本,又抬头看看对面墙上的两块牌子。“634号客房。”她说,“这边走,先生。”
张警督沿着走廊慢慢地走过去。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家里,立刻飞快地穿戴停当,想第一个赶到现场。在治安极好的新加坡,一名侦探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处理凶杀案的。
他们来到了634号客房门外。张警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金发女郎。她怒视着他,仿佛他打算向她兜售人寿保险似的。张警督亮了一下警官证。“我是新加坡警察局的张警督,”他说,“同新桥路的英国刑事调查局在一起。”他朝同伴点点头,介绍道,“这位是侦探李警佐。”
李警佐拿出警官证给这个女人看。她点点头,把门开大。“请进,我们不想惊扰客人们。”她说。
张警督和李警佐走进房间,金发女人把门关上。屋子里还有四个人——一个高个子西方男人和一个长相粗鲁的印度男人,两人都穿着黑西装。还有一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中国女子和一个穿着白夹克的服务员,他站在一辆手推车旁边。
金发女人伸出手:“我是杰拉尔丁·博古伊斯,这里的经理。”张警督同她握了握手。博古伊斯指着高个子西方男人介绍道:“这是克里斯托夫·梅西埃先生,我们的安全主管。”梅西埃没伸手,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经理又把手指向印度人和中国女人。“拉马南先生和修小姐今晚在前台,”她说,“他们都是副经理。”
两人朝张警督点点头,紧张地笑了笑。两人都戴着银色的胸卡,上衣胸袋里露出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与胸卡颜色相配的手帕。张警督也朝他们点点头,然后看着服务员。“你是?”他问。
“周先生,”博古伊斯回答,“他给威尔金森送他订的客房服务,发现了尸体。”服务员点点头表示同意。
张警督扫视了一眼房间。“我没看到尸体。”他说。
博古伊斯指着一扇侧门。“在那里面,”她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套间,有起居室和独立卧室。”
“请带我去看看尸体。”张警督说。
经理带他们穿过侧门,走进一间大卧室里。房间里开着灯,拉着窗帘。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躺在床上,脚从床尾垂下来。张警督一眼就意识到这是个西方人,一个大腹便便的大块头。他头边的一摊血已经被床单吸收了进去。
“彼特·威尔金森先生。”博古伊斯说,“他是美国人,我们的VIP客户,每个月来我们饭店一次。他在美国有一家塑料制品批发公司,经由新加坡去他在中国的工厂。”
张警督弯腰看着床上的尸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注意到尸体的下巴上有个伤口,胸口上都是血。“一个伤口,”他说,“显然刺破了血管。不过不是颈动脉,否则会有更多的血喷溅出来。”他看着警佐,“颈动脉血的喷溅是很有特点的。我想这个案子里应该是静脉失血,要流一会儿才会死。如果是颈动脉被切断,他几乎立刻就会死。”
李警佐点点头,匆匆地记在笔记本上。
“注意胸口上的血,”警督接着说,“只有他站着的时候才会流到那里。这说明他被刺前是站着的,然后倒在或被推倒在床上。”
他绕过床尾去查看床头柜,上面有个钱包和一块劳力士手表。张警督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一根圆珠笔,挑开钱包,里面有厚厚的一沓钞票和六张信用卡,都是金卡或白金卡。“我想我们可以排除抢劫的动机。”他说。
李警佐飞快地记在笔记本上。
张警督回到起居室,博古伊斯和李警佐跟在后面。
“你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张警督问服务员。
“大约十点钟。”经理在服务员开口前回答,“周先生打电话给前台,我们立刻就上来了。”
“我們?你是说前台的所有人?”
“我自己,梅西埃先生、拉马南先生和修小姐。”
拉马南和修小姐朝张警督点点头,但没说话。修小姐害怕地看着卧室的门,仿佛死者随时会复活似的。
张警督沉思地点点头:“走廊里有监控吧?”
“当然。”经理说。
“我要先看看录像。”张警督说。
“梅西埃先生可以带你去保安室。”博古伊斯说。
“好极了。”张警督看着李警佐说,“警佐,你在这里向每个人了解情况,我很快就回来。不要让任何人离开,也不要破坏犯罪现场。”
“我可以叫技术人员来吗?”李警佐问。
“等一会儿再说,李警佐。”
张警督和梅西埃乘电梯下到底楼,梅西埃把警督带进前台后面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梅西埃坐下来,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六楼走廊里的场景马上占满了整个屏幕。“你想从什么时候看起?”他问。
“你知道威尔金森先生什么时候回房间的吗?”张警督问。
“大约八点半吧,我想。”梅西埃回答。
“如果方便的话,请从八点二十分开始快进。”张警督说。
梅西埃敲了几下键盘,屏幕底部的时间显示八点二十分,然后秒时开始快闪。电梯门开了,一个大块头男人和一个娇小的亚洲姑娘走了出来。
“就是他。”梅西埃说。他敲了一下键盘,录像开始以正常的速度播放。
威尔金森穿着一件黑上衣,他的同伴是个漂亮的亚洲姑娘,二十岁出头,留着齐腰的黑长发。她穿着白色紧身衣,领口开得很低,只见她抓着威尔金森的手,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开心地笑着。
“停在这里。”威尔金森和姑娘向套间走去时,张警督说。
梅西埃照办了。张警督盯着屏幕,认出了这个女人。“噢,可爱的露露小姐。”他说。
“你认识她?”
“她是城里一家最昂贵中介公司的伴游女郎。她不伴游时,你可以在乌节路的一家酒吧里发现她在拉客。”这个女人穿着难以置信的高跟鞋,可是仍然达不到威尔金森的肩膀。
“四楼(注:The Four Floors of Whores,新加坡的红灯区)的妓女?”梅西埃问,“她是个妓女?”
“不会吧,梅西埃先生。作为一家五星饭店保安部门的头头,你们一定有自己的夜间访客。”张警督说。
“我们有规定,午夜后不允许访客进入客人的房间。”梅西埃不自然地说。
“我相信你们的客人会遵守这个规定。”张警督看着录像上的时间码说,“露露小姐是泰国人,不过她到新加坡旅行用的是各种各样的名字。现在,我们从时间码上知道威尔金森先生和露露小姐是八点半到的,你能快进到露露小姐出来的时间点吗?”
梅西埃敲了一下键盘,录像开始快进。客人们在走廊里进进出出,饭店的员工飞速而过。可是那扇门一直关着,直到九点半才打开,露露小姐从里面溜出来。梅西埃放慢了录像,他们看着露露小姐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威尔金森先生付了一个小时的钱。”张警督说,“现在的问题是,威尔金森什么时候要的客房服务?”
“我不太清楚,”梅西埃说,“这个要问服务员。”
“那请快进到服务员推着车到达的时候。”
梅西埃照办了。十点差五分的时候,服务员推着车出现在走廊里。他敲了敲门,然后又敲了敲。
“要是客人没有开门,饭店的规定是什么?”张警督问。
“要是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工作人员会打电话到房间里。要是没有,他们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钥匙。”
服务员又敲了敲门,然后用自己的钥匙把门打开。张警督记下他進去的时间:九点五十五分。
“服务员什么时候给前台打的电话,说他发现威尔金森先生死在床上?”
“正好十点前。”梅西埃说,“你得问博古伊斯,她知道确切时间。”
他们注视着屏幕。约一分钟后,服务员出现在走廊里。他抱着胳膊,浑身发抖,接着开始在走廊里踱步。博古伊斯带着下属出现时,时间码显示的是十点零三分。他们都匆匆地走进房间。
梅西埃摁了一下键让画面定格,指着时间码。“十点零三分,”他说,“除了威尔金森和他的客人,没有别的人进出过这套客房。客人是九点半离开的,当他再次被看到时,已经死了。”
张警督放下笔记本,沉思着点点头:“很好。我们回客房去吧,我已经看到了需要看的一切。”
他们回到六楼,套房的门口已经站了两名穿制服的警察。他们点点头,闪开路让张警督和梅西埃进去。
李警佐正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张警督和梅西埃进来时她抬起头:“我把他们说的都记下来了,先生。”
“好极了。”张警督说着大步向卧室走去,“请跟我来,李警佐,其他人待在原地,我们很快就回来。”
李警佐跟着张警督走进卧室,张警督把门关上,用抑制不住的兴奋眼神看着她:“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吗,李警佐?”
李警佐看了一眼床上的尸体:“一起谋杀案,先生。”
张警督叹了口气:“哦,远不止这个。我们面对的是一起密室杀人案。”
李警佐耸耸肩,没有吭声。
“你知道为了一起密室杀人案我等了多久吗,李警佐?”
她又耸耸肩:“不知道,先生。”
“一辈子。”张警督兴奋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新加坡,我们没有悬而未决的杀人案,难以侦破的更少。”他叹了口气,“此刻,我真想有一顶猎鹿帽和一支烟斗。”
“公共建筑里不允许抽烟,先生。”李警佐说。
“我知道。”张警督说,“我的意思是,烟斗可以增强效果,就像一只忠诚的猎犬拉它的皮带一样。”
“新加坡的饭店里也不允许带宠物,先生。”李警佐说。
张警督无奈地叹了口气:“你漏掉了重点。这个重点是我们在一间从里面锁上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受害人被谋杀时没人进去过他的房间。李警佐,我们需要破解这样一个谜。”
“我应该通知技术部门吗,先生?”李警佐问。
“取证?”张警督重复道,“你没脑子吗,警佐?这不是一个可以靠技术解开的谜,”他敲敲自己的头,“要靠灰色的小细胞。”他没能做出大侦探波洛的效果,不过他觉得很满意。李警佐仍是一脸茫然,她皱着眉头,像个快要哭出来的孩子。“我们先四下看看,然后再决定需不需要通知技术部门。”张警督又说,恢复了正常的声音。
“先生,这不符合程序。”李警佐说。
“确实不符合程序,我在适当的时候会通知他们的。不过,我要先查看一下犯罪现场。”他回过身看着尸体,“噢,李警佐,你领会不到这种情况有多美吗?”
“一个人死了,张警督。”
“没错。他被杀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凶手找出来。”
他含笑看着她,像个和蔼的叔叔。“我们去把凶手找出来,你将是福尔摩斯的华生、摩尔斯的路易斯。”
“巴特曼的罗宾?”李警佐说。
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张警督想看看她是不是在嘲笑自己。可是她一脸无辜地笑着,于是他慢慢地点点头。“对,也许。”他说,“只是少了面具和斗篷。你知道蝙蝠侠在1939年侦探连环画中第一次出场的方式吗?”
“不知道,先生。”李警佐边说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
“他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我觉得有点儿言过其实。”
李警佐继续在笔记本上写着。“你在写什么,警佐?”張警督问。
她红了脸。“没写什么。”她说,把本子放到一边。
张警督点点头,同时慢慢地绕着房间走。“我猜你不熟悉约翰·迪克逊·凯尔的作品吧?”他问。
李警佐摇摇头。
“他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写过十几部侦探小说,大多数都是密室杀人的。他塑造了一个叫吉迪恩·菲尔博士的英雄,是他破解了这些案子。”
李警佐敲敲自己的头,“使用灰色脑细胞。”她用还算凑合的法国口音说。
张警督笑了。“说得对。”他说,“在他的作品《透明人》里,凯尔借菲尔博士之口详细说明了密室杀人的各种可能性。”他朝警佐点点头,“你一定很想把它们记下来,现在跟我来。”他们回到起居室。
张警督走到窗户前,背对着窗户。“现在,我已经查看了这套客房外走廊里的监控录像,检查了犯罪现场。”他说话时李警佐在本子上刷刷刷地记着。“监控录像显示,威尔金森先生带着一个客人八点三十分回到他的房间。这个客人是警察局太熟悉不过的年轻女人,她整整待了一个小时才离开。我需要知道的是,威尔金森先生是什么时候要的客房服务。”
“账单上有,警督。”博古伊斯小姐说着走到手推车前,拿起一个小型的皮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片。她看了一眼,点点头说:“是九点三十六分要的。”
“好极了。”张警督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威尔金森先生是在要客房服务的九点三十六分至客房服务到达的九点五十五分之间被杀的。”他皱起眉头,“这似乎发生得非常快,博古伊斯小姐。”
“警督,我们是五星级饭店,而威尔金森先生只要了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对我们的厨师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博古伊斯微笑着回到沙发上。
“非常好。”张警督说,“这样,我们可以排除威尔金森的客人行凶的可能,因为他在九点三十六分时仍然活着。”
修小姐紧张地举起手:“事实上,警督,我们知道那以后他还活着,是因为九点四十五分时他还同他妻子通过电话。”
“这是怎么回事?”张警督问。
“她九点四十五分打来的电话,”修小姐说,“电话从美国打过来时我正在前台,威尔金森太太在电话里同她丈夫交谈了将近五分钟。”
“你肯定吗?”张警督问。
“我确定那是他的妻子,他们交谈了几分钟。”她说,“我不能肯定他们交谈了是三分钟、四分钟还是五分钟。”
张警督点点头。“那么,我们可以假定电话的确是威尔金森太太打进来的。”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妻子会被一个冒名顶替者愚弄,因此我们知道威尔金森先生在服务员到达他的房门前五分钟还活着,我们还知道服务员到达前没人进出过这套房间。”他调整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依次打量着屋子里每个人的脸,“就是说,我们要侦破的是一起密室杀人案。”
他停顿了几秒钟,点点头接着说:“就像刚才我向我的同事所解释的,密室里发现尸体通常有七种解释,这些解释是由天才的侦探小说作家约翰·迪克逊·凯尔提供的,我认为了解一下这些解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第一种可能是,这起谋杀案事实上不是谋杀,而是一连串的巧合和意外给人造成谋杀的印象。一个人绊了一下,摔倒在沉重的家具上,于是有了一具尸体,但是没有凶器和凶手。”张警督停顿了一下,确定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时才接着说,“考虑到伤口的性质以及尸体躺在床上,加上只有床上有血,在这起案子里不大可能是意外。假如他意外地刺伤了自己,比如扎到床头柜上的台灯,我们会看到那上面有血。可是除了床上,没有别的地方有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死在床上的。”
他转过身,背着双手,看着窗外,接着说:“第二种解释是,的确是谋杀,不过受害人是被迫杀了自己。一种改变思维的物质可能被使用,煤气或者药丸。”
“你认为他是被毒死的?”梅西埃问,“或是煤气中毒?那煤气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有中央空调,窗户也是密封的。”
“他要是被毒死的,技术部门应该知道。”李警佐说,“他们可以进行检验。”
“他不是自己刺死自己的。”张警督很快地说,“如果是那样,凶器应该在他手上或床上。这里没有刀,所以他不是自杀的,我也没看出受害人在这间屋子里吃过或喝过什么。”
他走到小吧台前,把它打开,里面满满的:“你们看,里面什么都没少,屋子里也没有打开过的空瓶子。”
他看着服务员:“你进来时威尔金森先生已经死了?他死在床上,你看到了血?”
服务员点点头。
“所以他没有吃服务员送来的东西,我们可以排除毒害的可能。”他回到窗户前,“这是密室杀人案最令人着迷的第三种可能,”他接着说,“凶手使用一些机械装置来实施杀人。比如,一把藏在电话里的枪,从手提箱里弹出一把刀;或是一把当门锁转动时就开火的枪;或从天花板落下的重物;或者一张被你坐热后发出毒气的椅子。”他朝卧室挥了挥手。“在这起案子里,我们将寻找某种刺死威尔金森后让刀消失的方法。”他冲李警佐笑笑,“你怎么看,李警佐?你认为卧室里藏有机械装置吗?”
“不太像。”她小声地回答,仿佛害怕说错似的。
“我同意。”张警督说,“这是饭店客房,同别的客房一样。”李警佐笑着松了口气。
“这是我们最好的套间之一。”经理说。
张警督认可地点点头:“可是,屋子里没有东西被改动过,对吗?一切都同应该的那样?”
“是的,除了床上的尸体。”
“那么,我们将进入第四种解释:自杀。”
“自杀?”李警佐重复道,“可是,如果他杀了自己,凶器在哪儿?”
“要点在于把自杀做得像是谋杀。”张警督说,“要么是想嫁祸某人,要么是保险诈骗。我猜像威尔金森这么健康的人一定有大额保险。也许他得了绝症,可能是癌症,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杀了自己,以便妻子仍然可以申请保险赔付。”
“也许就是这样,”梅西埃说,“当然,你得查查他有没有保单。”
“可是,他使用的凶器在哪儿?”李警佐问,“要是威尔金森先生拿走了自己的生命,刀子在哪儿?”
“这才是要点。”张警督说,“要把自杀做得像是谋杀,凶器必须消失。凯尔先生的设想是用冰做的刀子,冰会融化,只留下水。或者一把系着长度足够的橡皮筋的枪,弹回到烟囱或窗外。”
“这里没有烟囱。梅西埃先生已经说过,我们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是密封的。”经理说。
“我认为冰也不大可能,因为他得把冰从外面带进来,新加坡的气候也不允许他带着冰到处走。”张警督说,“还有,如果威尔金森先生想让自己看起来是被谋杀的,我认为他不会让自己躺在床上,地板是更可能的地方。另外,还有个客房服务的问题。他同令人愉快的露露小姐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然后订了餐,一个准备自杀的人是不可能做这些的。”他抱起胳膊,“因此,这就引出凯尔先生讨论的第五种方案:一起来自幻觉或模仿的谋杀。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已经死了,可是凶手让人以为他还活着。”
“在这个案子里是怎么回事,警督?”博古伊斯小姐皺着眉头问。
“比如,那个妓女杀了威尔金森先生,然后安排某人打电话要客房服务。”张警督说,“这会使她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而事实上她离开时威尔金森已经死了。”
“你认为是这样吗?”李警佐问。
“这不可能。”博古伊斯小姐说,“我们的客房服务部接到电话时会显示来电号码,从饭店外打进来的电话是不会被接受的。”
张警督思索着点点头:“他订了客房服务后还同妻子通了电话,所以我不认为露露小姐是凶手。那么,这又把我们带往凯尔先生列出来的第六种可能上,这种解释是,谋杀是在室外进行的,却让人以为是在室内进行的。”
梅西埃抓抓他的秃头:“这说不通。”
“不,梅西埃先生,这很能说得通。”张警督说,“别忘了凯尔先生说到的冰匕首。假设可以通过打开的窗户或门上钻出的孔向里面开枪,或者投刀手从大楼对面的某个房间里从打开的窗户把系在绳子上的刀子扔进来,然后把刀子收回去,因此显得凶手在室内,而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室外。”
“可是窗户是密封的,门上也没有孔,况且门是对着起居室的,到卧室还有一道门。”经理说,“冰匕首必须拐九十度的弯,还要穿过两道门。”
张警督叹了口气:“女士,我并没有暗示威尔金森先生是被冰做的凶器杀害的。”
“可你老是提到这些,”经理说,朝他翻了个白眼。“要是刀没有融化,它在哪儿?”
“问得好。”张警督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刀在哪儿?如果真的有刀的话。”
“你知道吗?”梅西埃问,“要是你知道,干吗还要问我们?”
“我只是用了修辞手法。”张警督说,取下眼镜,用手帕慢条斯理地擦着。“我不确定凶器在哪儿,不过我有我的怀疑。但首先,让我说完凯尔先生的第七种解释,这种解释与第五种恰好相反。”
每个人都皱起眉头,试图想起张警督说的第五种解释,然后四下看看,彼此耸耸肩。
李警佐走到张警督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张警督,我想同你谈谈。”
“李警佐,我正在兴头上,”他说,“不能等一会儿吗?”
“不能,先生。”李警佐说。
张警督恼火地叹了口气,朝卧室的门点点头。“最好是重要的事。”他说。
他们走进卧室,站在床边。“有什么话,李警佐?”张警督问,“你似乎很不安。”
“先生,我们真的要喊技术部门了,”她说,看了看表。“都快午夜了。”
“还没到。”张警督说,“我认为不依靠技术,我们也能解决这个案子。”
“可那是程序,先生,我们必须遵守程序。”
“李警佐,你知道我会说日语吗?”
她点点头:“我们在解决寿司大厨在他的餐馆杀人的案子时起了很大作用。”
“说得对。”张警督说,“可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学日语吗?”
警佐摇摇头。
“有个著名的日本作家叫岛田庄司,他写了十三部密室杀人小说,只有一部《占星术杀人事件》被翻译成了英文。我想读他其他的作品,所以自学了日语。”
“我明白,张警督。”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李警佐。我可以解开这个谜,我想证明我自己。”他微笑着,“也许是向你证明,即使再过一千年,还是需要真正的侦探。”
“就像蝙蝠侠?”
“我认为更像夏洛克·福尔摩斯。”张警督说,“我们有个也许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的机会。在新加坡,一年要是能遇到一起谋杀案就很幸运了。”
“幸运?先生?”
张警督举起手:“你说得对,幸运不是正确的词。新加坡难得发生谋杀,我们的岛国是世界上控制最严的地方。我们的政府对公民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所以我们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加上我们处决杀人凶手,”李警佐说,“那也起到了威慑作用。”
“说得对。你没看出这个案子有多特别吗,李警佐?大多数侦探都会不惜一切地扑在这个案子上,而你却想把它交给科学家。”他环顾四周,似乎怕被偷听,“万一是个连环杀手呢,李警佐?”
“目前只有一个受害人。”李警佐说。
“这个我知道。”张警督说着,拼命地不让声音发抖,“万一有更多的呢?万一我们手上有个真正的连环杀手呢?”他打了个哆嗦,“你能想象得到吗,李警佐?”
李警佐点点头,但没回答。
“你知道新加坡只出过一个连环杀手吗?”张警督问。
“知道,先生,阿德里安·林。”
“说得对,李警佐。”张警督说。确实是这样,这个岛国的每个侦探都知道这个案子,它成了警察学校的必修课。大巴窑杀童案。案子发生在1981年,那年张警督刚刚加入警察部队。阿德里安·林杀害了两个女童作为印度教女神卡利的献祭。林和两个女同谋1988年被绞死。
“可他是凭物证抓住的。”李警佐说,“警察发现了一连串通往他家的血迹。”
“正确。”张警督说,“正是因此,我才想用推理来解决这个案子。你明白吗?”
李警佐慢慢地点点头:“是的,先生,我明白。”
他拍拍她的背:“好极了。现在,你可以考虑给我们这个案子起个名字,因为我确信它将成为一个多次讨论的课题,所以很需要有个名字。”
“名字,先生?”
“一个标题,比如《饭店密室杀人案》,或者《消失的凶器》、《张警督与神秘消失的刀》,你觉得呢?”
“我不能确定,先生。”李警佐说。
“那就好好考虑一下,李警佐。”张警督说。
张警督和李警佐回到起居室。
张警督走到窗户前,回身看着饭店工作人员。“现在我们继续。凯尔先生的第七种,也就是最后一种情况:受害人在他或她实际上死亡之前被认为已经死了。当然,这与第五种情况相反,那种情况是受害人死了,但假装活着。”
“那就是说,当周先生进入房间时威尔金森先生实际上并没有死?”博古伊斯问。
“他死了,”服务员说,“我确定他死了。”
“可你并不是医生,周先生。”张警督说,“在慌乱中,有可能他看起来像是死了,但实际上谋杀却发生在稍后。”
“不可能,”梅西埃说,“我到这里时他无疑已经死了。”
“服务员给前台打电话后你很快就到了吗?”
梅西埃点点头:“你看过监控录像,每个人至多几分钟就到了。”
“他显然已经死了。”经理同意道,“你只需看看那尸体,那些血。”
“可是有一阵子服务员是单独同尸体在一起的,”张警督说,“他在打电话那一刻,单独同威尔金森先生一起待在房间里,我们也只是从周先生的嘴里得知威尔金森先生已经死了。”
“我没有杀他。”周先生赶紧说,眼睛在众人身上扫来扫去。
“我没说是你杀的,”张警督说,“我只是说你单独同威尔金森在一起。如果他没死的话,你有杀他的机会。这是解决密室杀人的一种方法。屋子是锁着的,而发现尸体的人就是凶手。他杀了受害人,然后报警。”他耸耸肩,“这种事发生过,但我认为没发生在这个案子里。”
服务员像是松了口气,松开衬衫的领子。
“此外,如果是你杀了威尔金森,刀子在哪里?”张警督问。
“事实上,张警督,我们还没搜过任何人。”李警佐说。
“不需要搜周先生,李警佐。”张警督说,“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回到楼下的保安室里,因为那里躺着真相。”
“所有人吗?”经理问,“不需要都去吧?”
“这是传统,女士。”张警督说,“侦探在揭露凶手前都会把所有相关人员召集起来。”
经理大笑起来,刺耳的笑声就像只愤怒的狗在叫:“张警督,这里不是乡间别墅,没有什么男管家。你只需告诉我们凶手是谁。”
“这里的确不是乡间别墅,而是新加坡最高档的五星饭店。”张警督说,“请迁就我一下,跟我到楼下去。”
张警督带着他们走出房间,穿过走廊向电梯走去。他和梅西埃、服务员、博古伊斯小姐和其中一名穿制服的警察一同乘第一部电梯下去。
李警佐带着两名副经理和另一名穿制服的警察乘坐第二部电梯。他们在保安室外会合,张警督带他们走了进去。他朝监视器前的椅子轻轻地摆摆手:“梅西埃先生,你请坐上去。”
梅西埃坐下去,一只手抓着头皮。“我们已经看过监控录像了。”他说。
“我们是看过了,可是我们真的看到发生了什么吗?”张警督问。他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梅西埃的身后,才请他从威尔金森先生和妓女从电梯里走出来那一刻开始播放。
“我们可以看到威尔金森和他的客人八点三十分到达,”张警督说,“这时他还活得好好的。”
他看着威尔金森和女人进了房间后说:“她一个小时后离开。请跳到那里,梅西埃先生。”
梅西埃敲了一个键,录像开始快进,到九点三十分前恢复正常播放,正好看到露露小姐从房间里出来。
“现在,威尔金森先生订了他的三明治和咖啡,所以我们知道这时候他仍然活得好好的。”
“那是谁杀了他?”博古伊斯小姐问,“假如那个女人离开了房间,又没有人在服务员之前进去,谁刺死了他?”
“问得好,女士。”张警督说。
“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在于要明白,谁没有进入这个房间才是重要的。”
“你这话根本说不通。”经理不悦地反驳道。
“恕难同意。”张警督说,“完全说得通,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本人在《银焰的冒险》中所说的,狗没有叫才是值得注意的。”
“饭店里不允许有狗。”梅西埃说,“这里没有任何种类的宠物。”
李警佐微笑着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来,而张警督只是叹了口气:“我只是用这个故事作为例子,说明有时候什么东西不在才是最值得注意的。这个例子取自《银焰的冒险》。要是我没记错,那是乔治警督问福尔摩斯,是否这个案子上有东西需要引起警察注意的。福尔摩斯说,那条狗在夜里的表现。警督感到不解,他告诉福尔摩斯狗在夜间啥也没干。对此福尔摩斯回答说:‘那是件奇怪的事。现在明白了吗,女士?”
经理不耐烦地摇摇头:“不明白。”
“那么女士,请允许我示范一下。”张警督说。他把一只手放在梅西埃肩上,“梅西埃先生,请快进到周先生推着手推车到达那里。”
梅西埃说:“我们已经看过了。”
“请迁就我一下。”张警督说。
梅西埃照办了。录像慢了下来,他们看着服务员用房卡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这时周先生发现了尸体,给前台打了电话。”一直等看到服务员周先生出现在门口,张警督开始在走廊里踱步。“就像你们看到的,在饭店工作人员到达前,没人进入房间。”屏幕上,博古伊斯小姐带着属下出现了,都急忙走进房间里。“这个时候你报了警。”张警督回头对博古伊斯小姐说。经理点了点头。张警督拍拍梅西埃的肩头,“请快进到我到达的时候,我要大家注意到,直到我和李警佐到達前没人再进入房间。”
客房的门一直关着。二十分钟后,张警督和李警佐走出了电梯。
“请正常播放,梅西埃先生,谢谢。”
梅西埃敲了一个键,录像恢复了正常。只见张警督走到门前去敲门。门开了,张警督带着李警佐走了进去,门又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现在,我们在房间里,同你们说话,判断着眼前的情况。然后我进了卧室,博古伊斯小姐。我查看了尸体,同你交谈。我回到起居室,然后同梅西埃先生走了出去。”屏幕上,张警督同梅西埃从房间里出来,向电梯走去。
“请停在这里,梅西埃先生。”张警督说。
屏幕显示张警督同梅西埃正向电梯走去。
“这里有个大问题,梅西埃先生,”张警督说,“现在你从房间里出来了,可是,你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呢?”
梅西埃没吭声。
“你没有同博古伊斯小姐一同到达。”
“我们到达时他已经在房间里了。”经理说。她倒吸了口凉气,用手捂住嘴,“天哪!他一直就在那里。”
“显然如此。”张警督说。
梅西埃站起来,试图冲出门去,可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
“现在,梅西埃先生,基于我认为发生的事,我要做两个预测。”张警督说着指了指梅西埃的外套。“我确信你带着杀人凶器,你没机会处理掉它,所以一定在你身上。因为我不相信你预谋杀死威尔金森,我相信凶器事实上是件无害的东西,也许是一支笔。”他看着梅西埃脸上惊讶的表情,“没错,一支笔。不过,我还认为你有个照相机,甚至是摄影机,我说得对吗?”
梅西埃没有回答,慢慢地从内口袋里掏出一支黑色的勃朗峰笔,笔尖上还有血迹。李警佐走上前,打开一个物证袋,梅西埃把笔丢了进去。他又把手伸进左边的裤子口袋,掏出一部比香烟还小的袖珍摄影机。
张警督接过摄影机:“露露小姐是你的同谋吗?”
梅西埃看着别处,没有回答。
“当然,她没牵涉到杀人案。她不知道威尔金森被杀了,因为她离开时他还活着。”
梅西埃点点头:“她不知道。”
“因为你根本没想杀威尔金森先生,对吗?”张警督问。
梅西埃搓着手,摇了摇头。
“你本来打算敲诈威尔金森先生?”
“敲诈?”博古伊斯小姐问。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张警督说,“威尔金森带着露露小姐到达时他正好躲在房间里,我猜他想录下他们,以便敲诈他。毕竟他是个已婚男人,在美国,离婚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唯一的问题是,露露小姐是不是敲诈的一部分。”
梅西埃点点头:“这是她的主意。”
“你是她的客户?”
“有时是。然后她说有个有钱的客户,对她很不好,她想报复他,并从他那里搞到钱。她说要把钱分给我。”
“所以她建议你躲在衣柜里,录下他们在一起的行为?”
“她在回饭店时给我打了电话,他们到达时我已经藏好了。她保证,他绝不会看到我。可是,本指望她让他去洗澡时以便我溜出去,他却没有去。他说他的妻子约好要打电话,于是他把她赶出了房间。然后他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所以我没法儿再出去。然后他妻子打来了电话,他接电话时我被困在了那里。”他用手擦着脸,汗水正从他脸上往下滴,“接下来一切都乱套了。”
“他打开了壁橱,发现了你?”
梅西埃点点头:“他没必要打开的。他所有的衣物都在行李箱里,浴袍在浴室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开壁橱,可是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看到了我。”
“所以你杀了他?”
梅西埃摇摇头:“那是个意外。”
“你用你的笔刺进了他的喉咙。”张警督说。
“他攻击我。”梅西埃说,“他打开壁橱的门,看到了我并攻击我,我们纠缠在一起,我必须制止他。”
“用你的笔刺进他的喉咙?”
梅西埃看着地板。
“我认为不是。”张警督说,“要是你在壁橱里刺伤了他,壁橱里会留下血迹。可是只有床上有血,因此你是在床上刺的他。”
“我们扭打在一起,我推倒了他。”
“然后你刺了他?”
“我的笔在上衣口袋里。扭打中他抓住了笔,想刺我的眼睛。我把笔推开,而它……”他停住口,不想或不能完成他的话。
“你刺进了他的喉咙?”张警督追问道。
梅西埃点点头。
“然后你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又躲进了壁橱里?”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我知道他要了客房服务,不能冒在走廊里被人看到的风险。”
“所以你一直等到服务员发现了尸体,并趁他给前台打电话的当口儿从壁橱里溜了出来?”
梅西埃点点头:“我想溜到别的房间里,可是走廊里有人,我出不去,只能假装刚刚到达。这是个意外,张警督,我发誓。”
“这要留给法官去考虑。”张警督说,“我还想要你提供另一件证据,梅西埃先生,你的手帕。”
“我的手帕?”
“我注意到你和你的同事们不一样,你的口袋里有块手帕。”警督说,“因此我猜测你在杀了威尔金森先生后,用它擦去了你手上的血。”
梅西埃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沾满鲜血的手帕,李警佐拿出另一个物证袋,梅西埃把手帕丢了进去。
张警督朝两名穿制服的警察点点头:“请把他带走。”
两名警察铐上梅西埃,把他带出房间。张警督朝李警佐手上的两个装着笔和手帕的证物袋点点头。“可以送给你在技术部门的朋友了。”他说。
“好的。”她说。
“我想这证明了一件事。”张警督说,狡黠地笑着。
“证明了什么,警督?”李警佐问。
“笔的确比剑更有威力。”他说,“这句话不用记下来,李警佐。”
责任编辑/张小紅
绘图/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