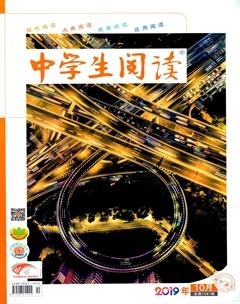古代园林里的琴境
李金宇
宋倪思曾说琴声是至清之音,明徐上瀛说听琴声有人深山邃谷之想,清张潮也有“凡声皆宜远听,唯听琴则远近皆宜”之语。可见,琴声渲染的氛围,与园林一样,都是营造出一个脱俗的、重自然的、幽雅闲适的出世境界。这使得琴境与园林之境在审美体验上完全一致,二者的结合,无疑是既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
琴在园林中的独特作用,中国古代造园者早有注意,所以置琴的建筑在很多园林里都有。苏州怡园有坡仙琴馆,杭州刘庄有蕉石鸣琴,成都罨画池公园有琴鹤堂,等等。
琴与园林的联系,不仅有物为证,而且有诗文为证。唐王维在他辋川别业的世界里,就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之句。清蒋恭棐在《逸园纪略》中写道:“每春秋佳日,主人鸣琴其中,清风自生,翠烟自留,曲有奥趣。”唐白居易在洛阳故居自谓“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而他的庐山草堂可谓简之又简,却依然少不了琴的身影。“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古人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后一句似乎也可以说成“不可居无琴”。仿佛有了琴,久在樊笼里的人们就可从尘世烦琐中解脱出来。琴声起到了涤烦消虑、忘忧解乏的功效,诚如陶渊明所言:“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南朝江淹直言晚年的生活追求是,在园林中弹琴吟诗:“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闲,忽忘老之将至。”
琴在园林中,可以解忧,更可以助景娱情。明徐有贞在《先春堂记》中言:“田园足以自养,琴书足以自娱,有安闲之适,无忧虞之事,于是乎逍遥徜徉乎山水之间,以穷天下之乐事,其幸多矣。”在琴声里,园林中的文人士子充分体会到了“中隐”之乐。在雍家园里,人们听琴声而仿佛进入神仙妙境:“我来踞石弄琴瑟,唯恐日暮登归轩。尘纷剥落耳目异,只疑梦人仙家村。”在园林的琴声里。人们体会到了忘怀息心的审美之境,体会到明文震亨《长物志》中所说的“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琴声如此,这使得园林中一切人耳之音,古人都好以琴声比拟了。如扬州休园,清方象瑛《重葺休园记》中说,“屋后修竹万竿,有轩日‘琴啸”,以竹声喻琴;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说,“(净香园)‘涵虚阁之北,树木幽邃,声如清瑟凉琴”,以树木声喻琴;扬州平山堂御苑的“听石山房”,古人云,“山风刚劲,风擦壁如琴”,山房前是黄石假山,后是湖石假山,山风盛时,自成妙响。此处风吹山石之音,亦以琴声作喻。最多的还是以水声喻琴。如苏州拙政园的小沧浪水阁,原有联云“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而北京颐和园中的“清琴峡”,则更是以听溪水潺声如琴闻名……保定的古莲花池,表达最为直接,涧水流觞之音在听者耳中就是琴声。围绕四周的建筑群分别叫响琴榭、响琴桥等。
从上文看出,园林中谓琴之所,其意倒并不在真实的抚操,而是意在琴外,在耳,更在心。据《莲社高贤传》记载,陶渊明自称不通音律,却仍备有一张无弦之琴,不时抚弄一番,别人以为怪,他却怡然自得,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借琴怡情,借琴起兴,借琴衬景,琴之一字,在园林里收到了“意显、情移、境生”的艺术效果。意显,指借琴把景点出来;情移,指游人因琴产生联想;境生,指以此生成充满乐感的氛围。因此,园中设琴室,倒不是要有一人天天抚琴而操,若此,反而太实,限制了游人的想象。有一琴一室一名即可,至于抚者是妙龄女郎还是白发老翁,是潇洒公子还是窈窕小姐,则完全交由观者自己,依了他们的经验、兴致、喜好,在想象的异域里享受自由“再创造”的快乐。
琴,又谐音“情”,此琴彼情,是琴境撩人还是游人多情,抑或是游人因琴景而留情?一个“琴”字,勾连无数,多方想象,如此这般,园林中的琴,怎不助人游兴,涨人雅意?因此,扬州瘦西湖的琴室,室内有琴一张,室外是“一水回环杨柳外,画船来往藕花天”,按《宋书》云,其时文人士子,“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
似乎可以说,琴的韵味在园林里达到了它的极致,在园林的背景里,琴声、游人、山水丘壑方更容易互為知音、互为传情。这也难怪《儒林外史》里市井奇人之一的荆元弹琴要到园林,书上写他生意闲时,“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中国古人有琴中觅知音的假想,“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中国的园林仿佛也这样,一石一水,一花一树,一亭一阁,只待“有缘人”,在读懂它的味,看出它的美,欣赏出它的妙后,才会发出那会心的一笑。
(选自《文汇报》2019年8月4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