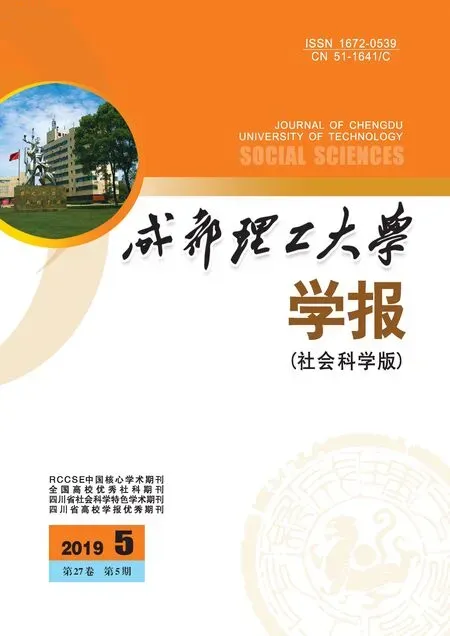诈骗犯罪结果并存形态定罪量刑研究
张晓丽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一、引言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诈骗刑事案件根据诈骗数额能否明确分为了目标数额明确的诈骗和目标数额难以查证的诈骗。
目标数额明确的诈骗,当一个犯罪既有“既遂数额”又有“未遂数额”时,该以哪一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学界和实务界对此至今未达成一致。笔者认为,诸论者对此情况下的两个数额称作“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是错误的。一个案件整体上的形态非既遂即未遂,不可能即既遂又未遂。在此情况下,既遂数额应当称作得手数额,未遂数额应当称作未得手数额,详见图1。理论和实务界对这两个数额名称的混称不仅导致理论上概念的混同,还会导致案件形态认定的混乱。

图1 诈骗数额的认定
目标数额难以查证的诈骗,当犯罪中既有得手数额又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当如何定罪量刑,理论中尚未有定论,司法中做法也不一。下面笔者将对这两种情形分别进行讨论。
二、目标数额明确的诈骗犯罪得手数额和未得手数额并存的量刑问题
(一)数额犯中得手与未得手并存时现存的四种处理方法
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等数额犯罪中,当既有得手数额,又有未得手数额时,到底以哪一个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实践中存在以下四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处理方法是,以犯罪既遂论处,根据已经实现的犯罪数额来定罪量刑,不考虑未实现的数额[1]。张明楷教授认为,盗窃罪中所规定的法定刑升格条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加重构成要件,只是量刑规则,因而不存在加重犯罪的未遂问题[2]。他认为,法定刑升格以超出前一档法定刑为前提,如果没有达到前一档法定刑的条件,就不可能符合法定刑升格的条件[3]。
第二种处理方法是,按照同种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处理[1]。对于此种处理方法,有论者认为,单次盗窃数额(特别)巨大财物的未遂与单次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既遂,并非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关系[4]。另有论者指出,如果一个行为既触犯了一般基本构成要件,又触犯了修正构成要件或派生构成要件,尽管是同一个罪名,但仍然符合想象竞合犯的特质[5]。
第三种处理方法是,以一罪论处,重刑吸收轻刑。即诈骗既有得手,又有未得手,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6]。
第四种处理方法是,将案件总体认定为犯罪未遂[7]。此种处理方法以目标数额选取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在该法定刑幅度内,以得手与未得手的数额比例调节适用具体刑罚,既遂额越多,处罚越重,反之,处罚越轻[8],即未遂的量刑应当在其法定刑幅度内随着图1中P点的移动而移动,P点越靠近B点处罚越重,越靠近A点处罚越轻。
本文支持第四种处理方法。
(二)在法理上对前三种处理方法的质疑及对第四种处理方法的证成
1.对前三种处理方法的质疑
第一种处理方法中张明楷教授将数额加重犯中的数额一概视为量刑规则,虽然有其“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类型”之类型化思维的根据,但是却存在不加分析地照搬德日学者观点而忽视我国与德日等国在立法方式上的重大差异之嫌[9]。在我国刑法既定性又定量还分档次的立法模式下,形式上同一行为类型所对应的,不仅有罪与非罪的区别,而且有基本犯和加重犯的区别,完全不同于德日等国的仅有行为类型的区别[9]。
第二种和第三种处理方法都将同一案件当中的得手数额和未得手数额分开认定,不论他们是用想象竞合的处理方法还是重刑吸收轻刑,二者皆将得手数额和未得手数额分开认定,将其称为既遂和未遂,这种对数额本身的性质认定就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诈骗是一个由多数的动作联合成的一个行为,这些动作可以看作诈骗的系列行为,即基于一个初始目标数额计划和实施之后的一系列行为。
2.对第四种处理方法的证成
首先,刑法上所称的行为,有单一的动作为一个行为的,也有多数的动作联合成一个行为的。比如行为人基于杀人目的实施行为,行为未遂只能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而不能将行为分割成故意伤害既遂和故意杀人未遂两部分。比如甲以杀人故意砍乙,致乙轻伤之后逃走,不能将甲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乙的既遂和故意杀乙的未遂,应将甲的伤害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即一个目标引领下的行为结果只能是此目标的实现与否,而非其他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与否。诈骗行为也是基于一个诈骗目标而实施的系列行为,诈骗目标统领和指导其接下来实施的所有诈骗行为,所有诈骗行为共同作用促成整个诈骗目标的实现,所以其既遂应该是整体诈骗目标的实现,而非实现其中一部分,如果只实现一部分,那就应该认定其整体诈骗目标未实现,即整体未遂,而不能分别认定其一部分既遂、另一部分未遂。以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案例62号为例,案中王新明的目标诈骗数额是100万,其接受定金和首付款的行为是这一系列行为中的一部分行为,既遂的30万元是他在这一系列行为当中将其犯罪意念转化成现实的部分。如果他的犯罪行为没有被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发现,也就是没有外在因素的强制干扰,他仍将继续实施诈骗行为来实现未得手的70万元,从而使其整体的诈骗目标作为一个整体行为加以实现。就行为结果而言,王新明的诈骗目标是100万元,其行为结果只存在诈骗100万元既遂和诈骗100万元未遂两种情况,认定他诈骗30万既遂,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其诈骗目标则为30万元,认定他诈骗70万元未遂,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其诈骗目标则为70万元,而这两个目标数额是与行为人犯罪目标数额不符的。
再者,诈骗行为对受害人财产的主观恶性从行为人犯意形成时就已经产生了,此时能够衡量其主观恶性的标准就是其诈骗的目标数额[10]。在上述第一种处理方法中只对得手数额进行处罚而不论未得手数额,只取了主观恶性的一部分与其对应的既遂数额,未能全面评价行为人的主观层面;第二种处理方法同样降低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将二者认定为两罪,实行想象竞合,生硬地将一个主观恶性大的犯罪分成了两个主观恶性小的犯罪;第三种处理方法虽然未将得手部分和未得手部分分为两个犯罪,重刑吸收轻刑,以一罪论处,但是这种处理方法也是将案件分为两部分进行评价,也会产生与第一二种处理方法同样的问题。以王新明案为例,根据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案件解释》的规定,将得手和未得手部分单独评价,分别认定既遂30万元、未遂70万元,而行为人的目的是诈骗100万元,不论是认定既遂30万元还是认定未遂70万元,都从数额要件上降低了其主观恶性。
(三)在量刑上对四种处理方法量刑结果的对比分析
在量刑时,这四种定罪量刑的方法会在相同的犯罪数额范围内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本文以北京市诈骗犯罪数额标准为例,将诈骗案件量刑时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定为“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50万元以上”,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分别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为了方便行文,将其分别称为第一刑档、第二刑档和第三刑档。另外,因第二种处理方法和第三种处理方法在量刑方面具有同一性,故为简化论述将二者合称为《诈骗案件解释》的处理方法(1)。
1.当得手数额未达到入罪标准时,未得手数额可能存在的三种情况
(1)未得手数额未达到入罪标准,整体未遂数额也未到达入罪标准。此时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占有数额较大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虽然实施了对受害人财物的诈骗行为,但是该财物的价值不在刑法保护的范围内,所以四种处理方法的量刑结果都是无罪。
(2)未得手数额未达到入罪标准,但是整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此时,按照第一种处理方法,只认定既遂,不追究未得手,此种情况下不入罪。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处理方法,既遂部分不入罪,未得手部分不入罪,最后结果也不入罪。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以目标数额定罪量刑。这里出现了入罪和不入罪的分歧。
(3)未得手数额达到入罪标准。按照第一种处理方法,只认定既遂,不追究未得手,此种情况下不入罪;按照《诈骗案件解释》处理方法,得手部分不入罪,未得手部分入罪,以未得手部分量刑;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以目标数额定罪量刑。
2.当得手既遂数额在5000元至10万元即数额较大范围内时,未得手数额可能有四种情况
(1)未得手数额没有达到入罪标准。按照第一种处理方法,仅以得手数额在数额较大范围内量刑,即在第一刑档,并且无论未遂数额如何变化,这个量刑结果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处理方法,先确定得手数额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一刑档,未得手数额不入罪,则采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认定整体未遂,采目标数额的法定刑幅度,但是因为一些临界值的存在,所以整体未遂的法定刑幅度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①得手数额加未得手数额得到的目标数额依然在5000元至10万元范围内,其法定刑幅度是第一刑档;②得手数额加未得手数额得到的目标数额范围超过了10万元,比如行为人得手97000元,未得手4000元,目标数额就是101000元,数额范围就跃升到了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此时的目标数额的法定刑幅度就升格到了第二刑档,至少是3年有期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当目标数额跃升到数额巨大的范围内就会发生法定刑的升格,得出比《诈骗案件解释》更重的判决结果。
(2)未得手数额在5000元至10万元范围内。第一种处理方法得到的量刑结果还是在第一刑档;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处理方法,得手数额与未得手数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都是第一刑档,所以采得手数额的法定刑幅度;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采目标数额的法定刑幅度,此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①目标数额依然在5000元至10万元范围内,其法定刑幅度是第一刑档;②目标数额跃升到了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比如行为人得手9万元,未得手9万元,目标数额18万元,其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所以当目标数额跃升到数额巨大的范围内时,就会发生法定刑的升格,从而出现相比于第一种处理方法和《诈骗案件解释》的处理方法更重的判决结果。
(3)未得手数额在1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处理方法,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一刑档,未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故按照未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量刑;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采目标数额的法定刑幅度,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①目标数额范围依然在1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此时其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②目标数额跃升到了50万元以上,比如行为人诈骗得手9万元,未得手49万元,目标数额58万元,其法定刑幅度就变成了第三刑档。所以当目标数额跃升到数额巨大的范围内时,因法定刑的升格导致判决结果更重。
(4)未得手数额在50万元以上范围内。按照第一种处理方法得出量刑结果是在第一刑档;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观点,得手数额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一刑档,未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三刑档,大于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所以在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目标数额必定大于50万元,所以其法定刑幅度必然是第三刑档。此情况中,第一种处理方法和另外两种处理方法得出的判决结果不同,而后两种处理方法得出相同的量刑结果。
3.当得手数额在1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时,未得手数额可能有四种情况
(1)未得手数额没有达到入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第一种处理方法得出的量刑结果是恒定的,即一直在第二刑档;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观点,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未得手部分不入罪,所以取得手部分定罪量刑;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目标数额必定也在1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所以其法定刑幅度也是第二刑档。此时三种处理方法得出的判决结果相同。
(2)未得手数额在5000元至10万元范围内。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观点,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未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一刑档,得手部分大于未遂部分,所以取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目标数额范围必定在10万元至50万元,所以其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此时三者量刑结果相同。
(3)未得手数额在1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观点,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未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也是如此,所以取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目标数额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①目标数额依然在1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此时目标数额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②得手加未得手数额得到的目标数额范围跃升到了50万元以上,比如行为人诈骗得手15万元,未得手45万元,整体未遂数额60万元,此时其法定刑幅度就是第三刑档。而第四种处理方法的判决结果就会重于第一种处理方法和《诈骗案件解释》得出的判决结果。
(4)未得手数额在50万元以上范围内。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观点,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二刑档,未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是第三刑档,故取未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按照本文的观点,整体未遂数额必定是50万元以上,所以其法定刑幅度必然是第三刑档。而此时第一种处理方法量刑是在第一刑档,所以量刑轻于后两者。
4.当得手数额在50万元以上时
此时得手数额的法定刑幅度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第一种处理方法得到的量刑结果是在第三刑档;按照《诈骗案件解释》的观点,无论未得手数额范围如何,都取得手部分的法定刑幅度,即第三刑档。按照第四种处理方法,采目标数额的法定刑幅度,得出与前两者相同的判决结果。
以上分析便是得手数额与未得手数额在不同的组合下按照四种不同观点所列举出的所有可能的量刑结果。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得手数额与未得手数额存在一些临界值时,二者相加得到的目标数额会跃升到另一个量刑档次内,由此发生法定刑的升格。刑事古典学派认为, 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 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 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 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1]。行为人主观恶性随着犯罪数额的增加而加重[10],量刑随着犯罪数额的增加而加重,这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因此,法定刑升格的发生,不仅会从量刑上改变案件性质,同时也侧面反映了行为人对公共利益危害的加强,因此应当用更加严厉的刑罚来对抗。
本文采用第四种处理方法,将目标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认定案件整体诈骗罪未遂,一般比照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轻或者减轻标准的确定,本文认为可以用得手数额来衡量,得手越多说明行为人对受害人法益的侵害越大,反之越小,反映在图1中即P点的移动代表了得手数额在目标数额中所占比例的变化,P点越接近B点,说明得手数额所占目标数额比例越大,以A、B的中点为界可以判定对行为人应当从轻还是减轻处罚。法官可以根据这一比例变化来决定对未遂的处罚幅度,量刑将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加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当诈骗目标难以查证时,既有得手数额又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量刑冲突问题
(一)得手数额和“其他严重情节”并存时现存的三种处理方法
2016年颁布的《意见》规定:行为人诈骗目标不明确时,“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骗得财物的,以诈骗罪(既遂)定罪处罚”。其中对“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作出了界定。“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是发送诈骗短信五千条以上、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或者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的”,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具有上述情形,数量达到相应标准十倍以上的”被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行为人既有得手数额,又有《意见》中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时该如何量刑?实务中存在以下三种做法。
第一种处理方法是,只存在“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不存在得手数额时(2),此种情形完全符合《意见》中所规定的情形,所以可以直接适用,即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二种处理方法是,得手数额较小(满足“数额较大”),但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根据《意见》规定按诈骗罪(未遂)来处罚。对于得手数额,有的法院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来处理(3),有的法院则在重刑吸收轻刑之后便不再考虑(4)。
第三种处理方法是,案件中既有较大的得手数额(量刑幅度远超“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量刑幅度),又有“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时,一般只根据得手数额来定罪量刑,不再对“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进行评价(5)。
本文认为应当采用想象竞合,重罪吸收轻罪,以重罪认定犯罪形态,同时将得手数额作为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加以考量。
(二)在法理上对本文观点的证成
当行为人既在数额上成立诈骗罪,又在情节上成立诈骗罪,这就相当于成立了两个诈骗罪,而数额的成立是由情节中的行为导致的,行为人以一个主观故意实施一种犯罪行为,导致两个犯罪的成立,按照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此处按照法定刑幅度的大小判断罪行的大小[12])。如果数额重于情节,则认定犯罪既遂,如果情节重于数额,则根据《意见》的规定认定犯罪未遂,这是在定罪上的处理。在量刑上,考虑到数额和情节都是这一案件的组成部分,故在定罪之后还应对比二者的法定刑幅度跨度的大小,再决定从轻或者从重处罚。
(三)本文观点在实务中的具体操作
当数额和情节同时存在时,先分别确定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对应的法定刑,重罪吸收轻罪,再比较二者刑罚档次的跨度,具体操作如下:
如果刑罚档次跨度大(比如数额量刑在一档,情节量刑在三档),则在重刑的基础上从轻刑罚;如果刑罚跨度小(比如两个量刑档次相邻或在同一量刑档次内),则在重刑的基础上从重处罚。例如,行为人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量超过五万次,诈骗得手五千元钱,依照北京的诈骗罪入罪数额标准,则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内量刑;而情节符合“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该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内量刑。先重刑吸收轻刑,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量刑;再对比二者的量刑档次,数额的量刑在一档,情节的量刑在三档,中间跨越了一个刑档,因此在“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量刑的基础上从轻处罚。又由于《意见》规定对“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对于情节的从轻处罚即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范围内从轻处罚,比如降低一个量刑档次。
四、结语
在诈骗目标明确时,数额犯中既有得手数额,又有未得手数额时,以目标数额作为犯罪数额来定罪量刑不仅能在犯罪构成论中站得住脚,而且更加符合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精神;诈骗目标不明确时,既有得手数额,又有严重情节,采用想象竞合的方式,不仅能正确认定犯罪形态,而且在量刑上将刑罚档次跨度的大小作为从轻或者从重情节加以考量,能够实现量刑的更加客观、公正。
注释:
(1)第二种处理方法和第三种处理方法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第二种处理方法将得手和未得手并存的犯罪区分为数罪,适用想象竞合的方法择一重罪论处,而第三种处理方法是将该情况视为一罪,将既遂部分和未得手部分分开量刑,重刑吸收轻刑。第二种处理方法要首先区分重罪和轻罪,而国际上重罪、轻罪具体的划分标准主要有4种:法定刑的刑期、刑种、犯罪类型、刑事诉讼活动(例如起诉、逮捕)方式,其中以自由刑的长短区别重罪与轻罪是最常见的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在第二种处理方法中,如果将得手部分和未得手部分区分为数罪,那么也应该是同种数罪,同种数罪必然通过对比自由刑的长短来区别,即在对未得手部分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得出其量刑,再与既遂部分的量刑相比较,取重刑作为最后的量刑结果,其本质也是重刑吸收轻刑,所以与第三种处理方法在量刑时是同一的。
(2)参见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陕05刑终116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837号。
(3)参见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豫16刑终723号。
(4)参见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余刑二终字第13号。
(5)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津刑终1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粤刑终27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通中刑二终字第00138号;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冀08刑终3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