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引入AI得到的启示
编译 乔琦
深度思维(DeepMind)创始人丹米斯·哈撒比斯(Demis Hassabis)曾经指出,对于构建智能水平与人类相当的人工智能(AI)来说,人类大脑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灵感来源。持这种观点的不止他一个。深度学习的成功向人们展示了如何把来自神经科学的启迪(记忆、学习、决策、视觉)转换成各类算法,并以此把我们人类强大认知能力赋予人工智能的硅大脑。
不过,人工智能又会对神经科学的发展有何启示呢?2019年8月,《自然》杂志策划了一系列文章,凸显了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共生关系。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交叉与相互促进由来已久。根本来说,它们致力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智能,只不过研究角度不同,抽象化的程度也不同。在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们希望通过机器语言从数学角度解开有效、高效学习之谜;而在神经科学领域,我们仔细剖析了两耳间这三磅脂肪团的里里外外,希望通过研究这绝无仅有的实例来理解智能问题。没错,我们就是证明人工智能可行的活证据。
在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主攻大脑信号控制机械肢体方向的塞詹·潘德瑞纳斯(Chethan Pandarinath)博士看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之间的联系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
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技术。凭借处理海量信息并从中发现相关模式的能力,人工智能融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管理和探究大脑活动方面的)中去的现象已经愈发常见了。第二个方面或许更令人激动。随着算法不断演化出与大脑类似的输出,它们已经成为测试神经科学纷繁复杂的基础概念的绝好实验田。在某些案例中,人工智能会抽象出大脑在做什么的高级概念,哪怕这些算法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与我们的大脑活动有极大的差别。
以下讨论了AI和神经科学相互促进的三种宝贵方式。
1 整理数据
虽然从神经科学诞生的时候起,数学方程就融于其中了,但一直以来,这个领域为破解大脑之谜而采取的实验手法始终都要依赖那些可以观察的生物学部件,比如感受器、神经递质和信号分子。然后,大数据时代来了。
神经科学家突然就拥有了可以在基因层面描绘单个神经元,或是运用数字手段重建海量神经连接的工具,而不用再挨个研究蛋白质和大脑区域了。例如,生物化学中各类“组学”的兴起,也就是在一定生物学层面上的全脑研究,其中包括基因组学、表观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以及我们很快就会归类出来的各种组学。就映射神经连接这项工作来说,细致入微地说明神经元物理连接的方式在人工智能出现后已经迅速变成了过时的方法。现在大家常用的方法是进一步把大脑图谱和其他功能图谱联系起来,比如,在逐渐变长的时间跨度内考察全脑基因表达模式。现在,解析神经信号事宜——并且把特定的激活模式同感官、运动乃至特定记忆联系起来——至少是在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这样的规模上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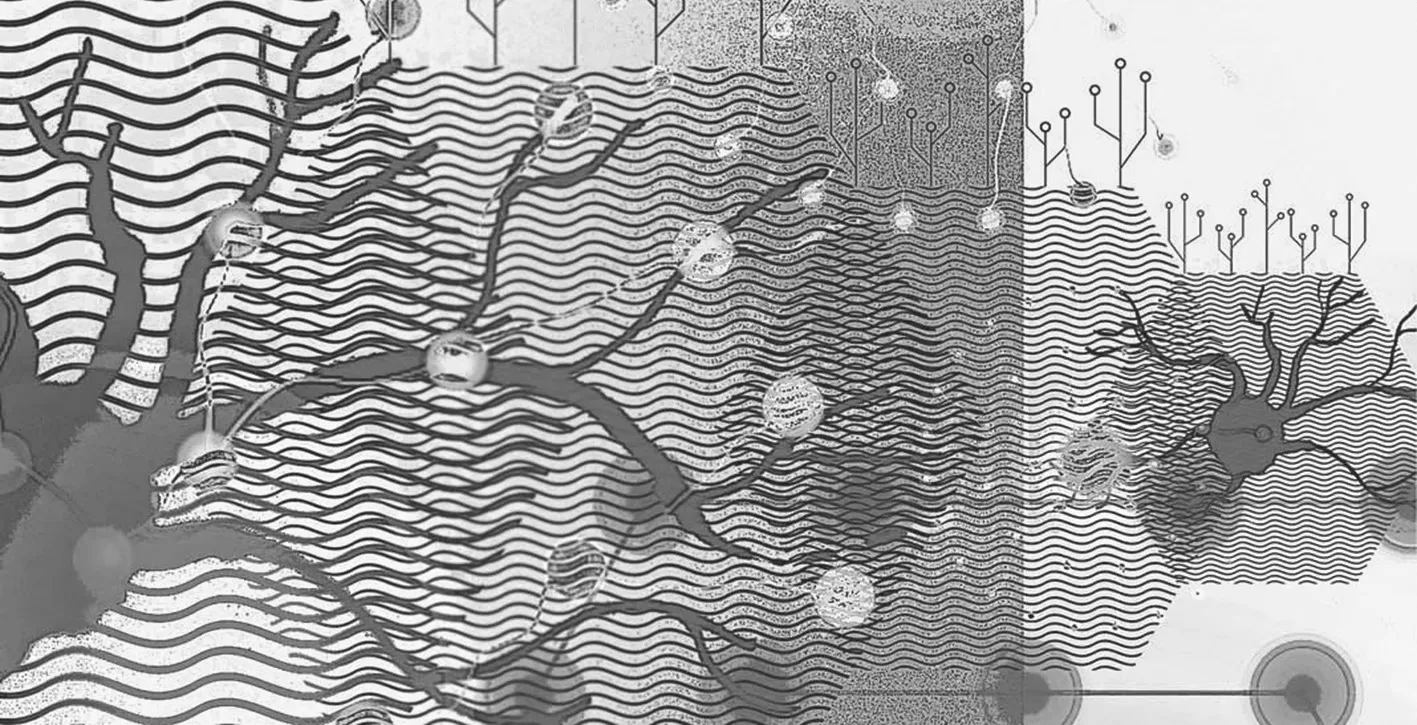
我们还会用大脑的活动模式控制机械手臂。例如,潘德瑞纳斯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在控制手臂运动的1千万至1亿个神经元中,一次性研究其中大约200个神经元发出的信号。而这就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相关算法可以帮助识别数据中的底层结构——哪怕它们深埋在噪声之中——从而提取出与特定细微行为相关的电子指纹。计算机还可以挖掘出这些激活模式随时间改变的方式,编写控制机械手臂所需的高精细度操作手册。
类似地,人工智能还大大加速了大脑映射项目和脑功能成像技术方面的研究,它可以轻松处理这类研究中需要处理、重构、注解的海量图像文件。计算机视觉甚至可以帮助分析那些负责检测神经死亡或蛋白质浓度水平的小规模大信息量图像。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研究人员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上——也就是解决根本问题——并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神经科学领域积攒的大部分数据集都以非标准的专有形式埋藏在本地硬盘中。随着神经数据无国界(NWB)——脑机接口先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洛伦·弗兰克(Loren Frank)博士就是其创始人之一——这类项目的驱动,将建立标准化数据结构,越来越多的数据会上传到云端,并且带着可供机器学习的标签。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人工智能对大脑的洞见。
2 解决感官和运动问题
现代深度学习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对视觉通路的研究。因此,神经科学家现在使用人工智能重新检验有关大脑加工感官和运动信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玛格丽特·利文斯顿(Margaret Livingstone)博士领衔的一支哈佛团队设计了一种名叫“XDREAM”的生物学算法,以此来研究一种神秘视觉细胞的“视觉字母表”。这个算法最终生成了大量图像。这些图像运用光栅和抽象形状把脸部糅合成了一种此前不为人知的细胞语言,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供进一步测试的基本观点。另一项近期开展且运用了卷积神经网络的研究发现,人类视觉系统会自动植入情感方面的信息,这和人们的普遍观念大相径庭。
这些研究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究明人类大脑处理感官和运动信息的方式对制造更逼真、受大脑控制程度更高的假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利文斯顿博士类似,斯坦福大学的丹尼尔·雅明斯(Daniel Yamins)博士同样致力于视觉方面的工作,但他的目标是究明目标识别过程中的神经网络活动。雅明斯根据我们现在对视觉系统架构的理解建立并训练了一张深度神经网络,并且发现这个网络中的神经活动与在猴子执行类似目标辨别任务时记录到的活动吻合。几年后,他又以听觉皮层为对象,开展了相同的研究。
仿真视觉或听觉的算法激发了科学家从新的角度认识大脑处理此类任务所采取的方式。“如果你训练神经网络做这些事,”谷歌大脑(Google Brain)的计算神经科学家大卫·苏西洛(David Sussillo)博士说,“那么你或许就能理解这种网络的运作方式,进而利用这点理解相关的生物数据。”
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模型可以起到模拟大脑的作用,指导理论和实践。它可以扮演体现大脑活动表征的过渡替身角色,科学家就不用在提出假设之后,直接拿到动物身上检验了。这类模拟允许“干跑”(dry-runs)扰动神经活动并且观察随后的结果,而不用把电极连到人身上。这个想法——虽然还刚刚起步——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开始了商业化运作。
这些结果在智能假肢与大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就是由大脑控制的机械假肢或外骨骼,以及可以绕过眼睛和耳朵直接激活相关大脑区域的视觉、听觉假体。近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Facebook的资金支持下,发布了一款通过阅读脑电波精确解码语音的系统。
3 破解神经密码
上述这些解决感官和运动问题的策略也有助于我们破解更多抽象的大脑功能,当然具体实施起来要复杂得多。例如,在计算机芯片中模拟负责记忆功能的神经回路未来有可能会把记忆或其他更高级的认知过程卸载到“记忆补丁”上,待到记忆所有人年迈或遭遇严重脑损伤之后再从这些补丁上把记忆加载回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已经在开展此类实验了。其他实验中的大脑假体包括一些智能植入物,它们可以检测神经活动,重点寻找是否有即将发生癫痫或抑郁的迹象,并且在发病前及时做出反应来抵消这些症状。
在这两个例子中,人工智能集中在帮助神经科学家破解所谓的神经密码——形成思维或行为的各个神经元组的激活模式。大脑植入物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最近人工智能的注入使其内部过程(比如识别神经活动的脉冲峰)变得高效多了。
最后,还有一种稍有争议的方法,它把重点放在了驱动人工智能类人工作的数学理念上,并且提出问题:这些数学理念是否也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长久以来,认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贝叶斯定理(一种把证据纳入现有理念的数学方法)是否也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做出决策的方式。科学家发现,受贝叶斯定理启发而设计的人工智能有时可以仿真人类认知过程,这重新点燃了正反两方的辩论热情。
当然,人工智能的输出与大脑的真实输出颇为相似,仅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大脑就是像人工智能那样工作的。与机器智能不同,我们的大脑是进化压力下的产物。我们大脑掌握的那些高效学习方式很可能和生存本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人工智能模型可能无法捕捉到的信息。
相比直接给出三磅宇宙之谜的答案,人工智能更有可能给出一个或更多可供神经科学家通过实验验证的解决方案。无论如何,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神经科学生态圈,并且这种影响未来只会有增无减。
“我希望能成为这场伟大变革的一部分。”苏西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