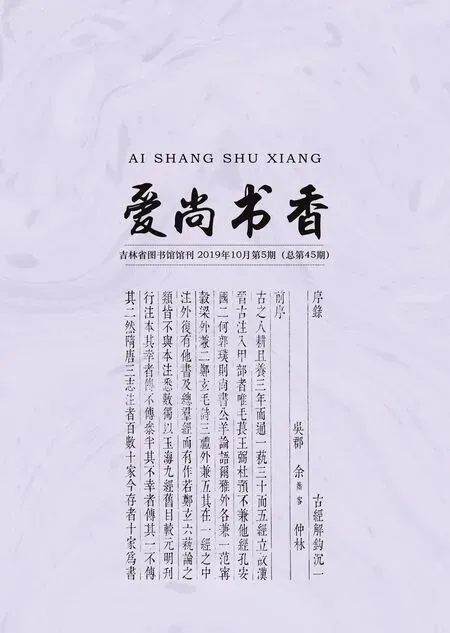译书的苦与甜
石观海
二十年前翻译《〈万叶集〉与中国文学》的时候,窗外正值暮春时节,珞珈山上牵动三镇的樱花已经飘落如雨。每当我走在樱花大道上时,便油然忆起是书的作者——辰巳正明教授。记得一个同样的暮春时节,辰巳先生陪我在东京观赏了灿烂得令人心醉、飘零得令人心碎的樱花。
我与辰巳正明先生神交已久,我第一次东渡时就通过其师弟东茂美先生和他有了书信往来,那时彼此正年轻。但真正有了接触却是我在东京都一所大学客座研究时。辰巳先生当时执教于大东文化大学,专治《万叶集》与中日比较诗学,研究颇有功底,成绩亦甚斐然。他给人的印象朴实敦厚,大智若愚,绝无某些知名学者常有的桀骜不驯和盛气凌人。有这样一位异国学者作为师友,私心很以为荣幸。
正如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经》一样,《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它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和歌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文学史上个人文学意识的觉醒和抒情文学的形成,引起了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学者们以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积极探讨它的价值。在争相问世的有关《万叶集》的研究著作中,辰巳先生的《〈万叶集〉与中国文学》《〈万叶集〉与中国文学Ⅱ》是两部不容忽视的力作,表现了他独特不群的目光。他突破了传统的实证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着重从主题建构的角度探讨了《万叶集》与中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他立足于《万叶集》中作品的本体剖析,研究和歌这一日本固有的文学样式对中国六朝文学影响的中和与变容。尤其值得注目的是,他把《万叶集》的研究置于汉字文化圈诸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中,从而使其研究具备了开放性和国际性。
在日本,研究《万叶集》的论著汗牛充栋,但译介到中国的却十分罕见。有感中国学界的这种状况,我觉得出版一部辰巳正明先生大作的中译本,似乎不无意义。古人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斯之谓也。一次,我邀请辰巳正明教授来校讲学,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他当然赞同我的提议,但是,原著两大本含13篇88章,共计1600余页,是名副其实的巨著。倘若全文译出,不仅费以时日,而且还会碰到出版方面的障碍。彼此协商再三,由辰巳先生择定了章节,并且另撰序言,书名一仍如旧。出这样的中译本,委实是权宜之计。其实,因篇幅所限而未择入的其他篇章也都颇值一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日本笠间书院出版的原版(日文版)。当然,借一斑而窥全豹,中译本正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翻译辰巳正明教授的大作,我作为一个非日语专业毕业的外行,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所幸有辰巳先生鼎助,碰到疑难问题便径直请教他。每次难以断定是非的疑惑,都得到他详细的解说,或者赐寄相关资料。因此,是书的完成确实是辰巳先生的“御隂様で”。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书中的和歌的汉译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曾有过一场争论。对于短歌,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李芒先生主张“似应从原歌的内容和句法出发,采取相应译法,而不宜在形式上强求统一”,友人罗兴典教授则主张按照原歌格调译成“五七五七七型”。后来我的友人早稻田大学的松浦友久教授在探讨了和歌的节奏后,认为与短歌的音数律最为对应的汉译形式应为“三四三四四型”(《中国诗歌原论》),国人王勇教授则主张译为“三七七型”(《中日关系史考》)。此外,尚有主张译作“诗经句型”的(钱稻孙《汉译万叶集选》),或译作“五言绝句型”的(杨烈译《万叶集》)。
而我认为翻译日本和歌,面对的是中国读者,而且主要是不大懂日语的中国读者,因此,和歌的汉译形式最好既能大致照顾到原歌的音数律,又能大体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所谓原歌的音数律,这里是指和歌的外部格式(字数、句数、句式等)。音数律当然还包括和歌的内部韵律(节奏、对仗、音步等),但对于既非研究者又不大懂日语的中国读者而言,他们只要大体把握诉诸视觉的外部格式特征就已足矣,而和歌诉诸听觉的内部韵律特征不妨留给专家学者们去研究。所以,把短歌按假名数译成“五七五七七型”(长歌则按句数类推),似乎是一种易于直观把握和歌外部格式的形式。而且,五言七言是中国古典诗歌两种基本的句型,译成由这两种句型构成的形式,较之于“三四三四四型”或“三七七型”,更易为中国人传统的审美心理所接受。
基于这种考虑,我把这本书中所引的万叶和歌都做了这样的处理,也就是把五音、七音译作五言、七言。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记纪”歌谣也采取了万叶和歌的汉译形式,而未顾及其中的“字あまり”“字足らず”等破格现象。
本书所引的和歌,依据的是辰巳正明教授的恩师、日本研究《万叶集》的权威中西进教授的《〈万叶集〉全译注》(日本讲谈社,1983年版)。古人说“诗无达诂”,更不用说翻译外国诗歌了。
回首此书的出版,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辰巳正明教授已经成为日本古典文学及比较文学学界著名的权威。先前在岛城执教时还不时收到他的新作。只是我使用电脑后,懒于拾笔,而他又不惯电脑,渐渐地彼此疏于联络。但我从网上还可以看到他仍然活跃于学坛,衷心祝愿这位老朋友永葆学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