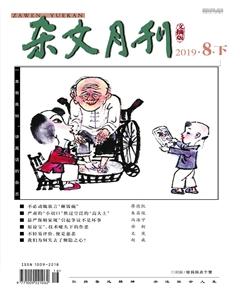前浪之“死”
蒋子龙
有一年春节前,我应邀担任一场文学活动的颁奖嘉宾,觉得这是个简单活儿,无非把奖杯或奖状递给获奖者。开奖嘉賓是熟识的批评家李敬泽先生,他可能是遵从主办方授意,为活跃气氛、加深人们对这个奖的印象,未开奖,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从全年的长篇小说中选出一部自己喜欢的作品,你的标准是什么?”
虽然有些意外,但在评选过程中我写过审读意见,便临时组织了几句:“在粗粝躁急的人文环境下,我喜欢能显现文学的精致和从容的小说,不刻意从现实中,生造出不现实乃至反现实以求深刻;没有走火人魔般地追慕神奇险绝的叙述效果,也没有繁复的滥情和贫舌,将创作的智慧化为清冽的深流,以沉静、自然的素质,体现了文学洁身自爱的能力。”
在这段丌场白之后,他打丌手中的信封,宣布获奖的是韩少功先生的《口夜书》。此时,韩少功走上台来,我将奖杯交到他手里,以为完事大吉,正要转身下台,被明星女主持拦住,她大慨看出在现场可能数我的年龄最大,又提了个问题:“您读不读80后的小说,您怎样看待‘大海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句话?”
在她眼里,我可能是已经死了的“前浪”,如今,竟然还出现在这样一个颁奖活动的舞台上。于是,当着满大厅的人把这个老家伙再往死里逼一下。犹豫了一下,我才回答说:“你的前半句不是问题,写作者首先是阅读者,无论是几零后的作品。如果我是被80后淘汰的,就更会读他们的作品,好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淘汰的。至于浪推浪死的这句名言,我非常欣赏,它体现了大自然一条神妙的铁律。你看那沙滩,干净、松软,前浪兴致勃勃地扑上来,瞬间消失,我本洁来还洁去。前浪一死,后浪立刻变成前浪,重复前者的命运。如果后浪拼命推,前浪却并不死在沙滩上,只是一味地向前冲,登陆上岸,摧枯拉朽,那将是难以估测的灾难。轻者是海啸、风暴潮;重者海平面上升,甚或让世界变成一片汗洋。”
人类之所以喜欢用“浪推浪死”来形容生命的规律,是羡慕其简单和优雅。前浪永远是后浪的榜样,该引导的时候一往无前,该让路的时候干净利落,该合作的时候携手拍天、惊心动魄,引无数人冒着危险到海边观潮,欣赏一排接一排的前浪死亡的辉煌与壮美。那么,人类的生命现象怎么能和“后浪推前浪”相比呢?即便是有条件能把骨灰撒到大海或江河,也还要乘船、买花……比“前浪之死”,不知要麻烦多少倍。
不知是受了伶牙俐齿的主持人逼问,还是因为有亲人刚去世,在离丌颁奖活动之后,我脑子里还在想着关于“死”的话题。譬如,一对老大妻就不能简单地分为前浪、后浪。或许,可以称作“并头浪”。他们又绝少会同时“并头西归”,剩下的那个“孤浪”该如何找到“沙滩”?杨绛先生曾睿智地将先走的人称作“逃”,留下的人“要打扫现场”。一般百姓没有太多“现场”可打扫,该怎样走完剩下的路程呢。
从前的老邻居葛大爷,自老伴过世后便闭门不出,无论儿女怎样劝导也没用,逼急了就是一句话:“我没脸见人。”无人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难道在他心里觉得失去老伴就失去了自尊,沦为别人可怜的角色吗。
还有一位杨师傅,也是年近八旬,老伴死后,丌始捡破烂。他有退休金,足可以过安稳口子,女儿跟他住在一栋楼里,也很孝顺,死说活劝都拦不住。他有自己的理由:从早晨一睁眼,满脑子就是破烂,走哪条路线,哪个垃圾箱里破烂多,捡回家一样样地分类,然后去卖掉。过去捡一天只能卖20元,现在可以捡到能卖40元的东西。跑一天下来很累,晚上倒头就睡,什么也不想。如果什么都不干,成天就待在家里等死,满脑子都是死去的人,还活个什么劲呀。
如此看来,“前浪死在沙滩上”听着尖刻,实则更像是一种向往和赞美。
摘自《河北日报》2019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