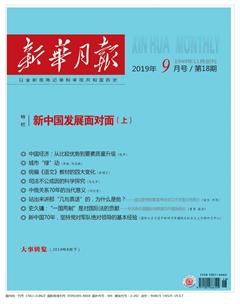史久镛:“一国两制”是对国际法的贡献
崔隽 敬宜
脱去庄重的法袍,史久镛是一位普通的老先生。
见到记者时,史久镛起身招呼记者坐下喝水。话题从北京的天气和交通展开,有一种闲话家常的亲切感。
不过,国际法官的素养和习惯在史久镛身上仍然有迹可循。为了表示对来访者的尊重,即使在家里,他也要穿着熨帖的夹克和衬衫,再配一双光亮的皮鞋,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哪年哪月哪案的记忆仍然清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英文法律词汇常常脱口而出。
93岁,史久镛的年岁比联合国国际法院(以下简称“国际法院”)的历史还要长。从外交部法律顾问到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再到国际法院法官、院长,他说自己的人生经历,恰恰也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
放大镜和录音笔不离手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那天,史久镛没有到现场领取改革先锋奖章。家人说,已经年逾九旬的史久镛,到现场参会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了。
那枚奖章现在就摆在客厅的陈列柜里。“我没想到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做梦也没想到。”坐在记者面前的史久镛重复了几遍“没想到”。
最近这些年,从国际法院退休的史久镛常常为外交部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上了年纪,腿脚不如从前麻利,他常用口述录音的方式将咨询意见送给有关部门参考。放大镜和录音笔成为他不离手的工具。
2013年,菲律宾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单方面将中菲南海有关争议提起国际仲裁。2016年7月12日,临时仲裁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妄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部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整个过程,中方态度鲜明:对于仲裁,不参与,不接受;对于有关裁决,不接受,不承认。

当时,史久镛认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中菲南海有关争议没有管辖权,这是原则性、根本性的一点。当“裁决结果”公布时,中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声明称,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对于当前的国际形势,史久镛也很关心。谈到中美贸易争端,史久镛用了“艰巨”来形容。“贸易争端涉及了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美国依据‘301调查对华采取的单边贸易报复制裁并不具有国际法依据,有违WTO(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中的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原则,完全违反了free trade(自由贸易)的精神,也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體制相悖。”
中美贸易争端拼的是实力,但打的也是规则。“这次我们的态度很鲜明,外交部不是说了吗,我们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这些年中国正在利用国际法与国际规则处理国际争端,规制其他国家的违法行为,来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正是因为中国,我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史久镛家的陈列柜里,有一个刻有铭文和法官签名的纪念银盘,签名特意按照当时在职法官的资历排序。这是2010年史久镛卸任国际法院法官时收到的告别礼物。“对我来说,它代表着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十分珍贵。”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此后,一批国际法学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活跃的身影被视为中国在国际法学界受到重视的标志。
1993年,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同一时期,王铁崖、邵天任、端木正和李浩培当选为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赵理海成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
国际法院要就国家间争端行使诉讼管辖权,以及就联合国有关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行使咨询管辖权。被提交至国际法院的案子,均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和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因此法官的工作非常繁重。
“双方的起诉词、辩词摞在一起有一米多高。”史久镛张开手臂比划了一下。那时他每天从法院回家,吃饭之前要在床上躺20分钟休息调整。
开庭那一天是最忙碌的。随着礼宾官一声“La Cour(开庭)”,15位大法官身着法袍,依次从侧门进入大厅落座,法院正式开庭。上午法官们要听取双方律师的辩护,下午庭审辩词会以复印文本的形式送达到法官桌上,法官要在下午进行阅读分析。
2003年,77岁的史久镛高票当选国际法院院长,成为首位担任院长的中国籍法官。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向史久镛发了贺电:“您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您卓越学识和公正品格的肯定。这是您个人的荣誉,是中国法学界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誉。”
担任院长期间,史久镛参与审理了16宗案件,创迄今国际法院院长审理案件数量之最。“国际法院的法官是各国法律精英,他们都有‘我是天下第一的自信姿态。如何形成判决,当院长的就得仔细听,要考虑怎么引导大家,最起码要形成一个多数意见。”
采访中,史久镛提到他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美国继续增兵中东地区,伊朗宣布突破浓缩铀上限,波斯湾上空弥漫着紧张的空气。在国际法院工作时,史久镛对美伊之间的复杂关系深有体会。2003年,他还负责审理了伊朗诉美国石油平台案。
此外,以色列隔离墙案也是史久镛审理的经典案例。自2002年6月起,以色列沿以巴边界线及占领区修建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安全隔离墙,摧毁了140栋房屋,影响到87.5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来自400个家庭的2300多人流离失所。
经过5个月的法庭审议,2004年7月9日,史久镛在国际法院司法大厅宣布咨询意见: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应终止修建,同时拆除已修建的隔离墙。
“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影响之大,直到现在,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一见到我就说,在你手下作出的隔离墙的咨询意见公正合理,现在阿拉伯人民还把你看成英雄。”史久镛说。
在国际法院的答疑手册上有一句话: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一旦当选,就不再代表他们各自的政府,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保证绝对公正。“我在国际法院的唯一身份就是法官,我的法律信仰就是按照现行的国际法从事审判。任职那么多年,中国政府从来没干预影响过我,没问过我对某个案子怎么看。”史久镛说。
但是,在国际场合不讲不利于祖国的话,是史久镛一直坚持的立场。有一次,史久镛参加一位英國法官的家宴,一位荷兰少数党人问史久镛:“我看了您的履历,1954年您回到中国,我不理解,您当时难道不知道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吗?”这是一句别有意味的发问。
“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我留在美国,你觉得我现在能坐在这里,以国际法院院长的身份和你交流吗?我甚至连法官都当不上。正是因为中国,我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史久镛说。
力主香港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总协定内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史久镛在现场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外交急需具有国际法背景的专门人才。1980年,史久镛调入外交部条法司担任法律顾问。两年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此后,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问题开始了共22轮的漫长谈判。
史久镛是谈判工作组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法律顾问,参与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3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的起草工作。
回归后香港是否要继续留在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中?这是史久镛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香港借用英国是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的身份已经在总协定内。香港经济依赖进出口贸易,关贸总协定对其有重要影响。
史久镛力主香港先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总协定内。经过讨论,英方对此没有异议。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当时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申请“复关”表示支持,中国“复关”谈判前景光明,不出一年甚至半年就能谈成,那个时候香港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加入。
史久镛认为这是盲目乐观。“西方国家对我们‘复关的支持只是口头的,真刀真枪谈判的时候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的,没有10年谈不下来。何况当时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才刚开始,我们最终能改革开放到什么地步,外界是‘心中无底的。”
然而,这些观点被一些人视为“卖国”,甚至有人当面讥讽他说:“你要知道,李鸿章的外交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您是怎么回应的?”
“我理都不理他。”史久镛摆了摆手,笑了起来。
不久,他被派往日内瓦关贸总协定总部了解情况,回来后撰写万字长文《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最终,中央拍板决定香港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关贸总协定内。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问题不解决,那么在我们入世谈判时,香港的特殊身份很可能会被对方当成筹码,使我们的谈判更加艰难。” 史久镛说。
在联合声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归,也考验着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英方提议,声明中使用英方“放弃”香港的表述。但这样一来,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就被粉饰成了英国曾在香港行使所谓“主权”的历史,实质是将英国非法取得的权利合法化,中方不能接受。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最后的声明使用了中方主张的“交还”的表述方式。“‘交还意味着香港是英国非法军事占领的,现在要还回来,意味着香港从来不属于英国,中国对香港历来拥有主权。”史久镛说。
与英方代表通宵达旦地谈判、磨合、试探、拉锯,是史久镛的工作常态。在一场关于香港民航的谈判中,史久镛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与英国交通运输部的一位司长直接交锋。谈判整整持续了一夜。最后,这位英国司长握住史久镛的手说:“尽管我们的分歧很大,但这是一次友好的谈判,没有拍桌子,与你谈判很过瘾。”
再次回忆参与谈判的这段岁月,史久镛认为最大的亮点是“一国两制”被写入联合声明,这是中国对国际法的一大贡献。
“小平同志当时一直强调,中国政府愿意让香港保留资本主义,高度自治,实行‘一国两制。我们把这个意志也写进了声明,这使香港人民能放心,也得到了香港人民的信任。几十年后的今天,香港的前途命运仍与此紧密相连。”
学国际法,不想再看到国家山河破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史久镛在《纽约时报》看到了这则消息后急忙给家里拨越洋电话,询问家人是否安好。挂上电话,他心情激动,难以平复。
当时23岁的他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公法系深造。“我记得《联合国宪章》公布时,里面有一句: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成长在战争年代,学国际法就是不想再看到国家山河破碎,想推动国与国的关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丧权辱国,是史久镛最深刻的少年记忆。上中学时,史久镛一家居住在上海英租界。那时行人经过岗哨林立的外白渡桥时需向日本宪兵鞠躬行礼方可通过。“这是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屈辱感。”史久镛向记者回忆。
1950年11月28日,以伍修权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九人中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针对“美国侵略台湾案”,伍修权在安理会控诉美国的侵略行径,掷地有声。这是年仅一岁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史久镛坐在电视前见证了这一幕。他看着伍修权指着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痛斥,仿佛将中国人民100 多年的怒气倾泻而出,他只能用“震撼”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此后,新中国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1953年,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从此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视为中国在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1954年,史久镛等不及修完博士学位,直接踏上了回程。如今,隔着近70年的时光回望,史久镛仍然能回忆起那时急切的心情——迫不及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当时愿望很朴素,就是为国家做些事、出些力。”这个念头,直到现在也没有变。
每一个外交问题背后都是法律问题
记者:国际法是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法律,您觉得法律在外交中起到什么作用?
史久鏞:一个硬币的两面。国际法与外交是分不开的,每一个外交问题背后都是法律问题。要维持国家间彼此的正常关系,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就要求国家遵循一定的规则。
在外交方面,国际法的一系列规则对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解决争端。国与国之间寻求合作可以通过双边合作条约、多边合作条约来实现。国际法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也有推动作用。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您认为中国如何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久镛:中国已经渐渐成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国际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在我经历的几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选举中,中国每次选举都得到高票。我记得有一次,日本大使问中国大使,中国究竟送了多少钱,得票那么高?中国大使一听就笑了,说我们从来不贿赂,完全靠国家威望得到支持。
就国际法而言,国际司法机构应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席位。我们还要让自己的国际法观点和惯例在世界范围得到承认,增强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记者:70年里,中国在国际法方面都有哪些发展?
史久镛:前30年,中国的国际法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发展得比较快。1980年,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开始在大学里讲授,国际法学科体系逐步建立。
现在是国际法发展的好时机。这些年我们在条约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英文版《中国国际法论刊》发展得很好,在国际上的声望甚至高于《美国国际法季刊》。
中国还成立了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专门培训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学者。我记得有一次,海牙国际法学院秘书长来见我,向我开玩笑说:“你们厦门国际法学院要代替我们了。”
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过去中国是被动跟随,这些年已经开始积极参与,提出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丰富了国际法治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我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逐步转化为国际法规则。
(摘自《环球人物》2019年第14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