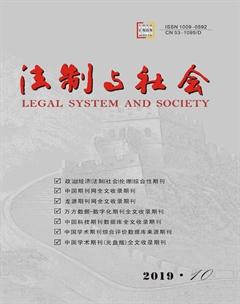另起犯意及犯意转化在司法实践中的思考
摘 要 在司法实践中,另起犯意与犯意转化之间关于行为人的犯意个数、犯罪终止形态以及罪数等问题都有极大的争议性。在个别实际案例中,认定行为人犯意以及行为的个数将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量刑情况。如何对该类案件进行准确定性,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不尽相同。本文试通过分析在犯罪不同的阶段以及侵害同质与不同质的法益试图来解决实践中遇见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 另起犯意 犯意转化 转化犯 法律拟制
作者简介:谢禛,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獻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0.104
一、司法实践中认定犯意转化的情形
犯意转化在不同的犯罪阶段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一)在犯罪预备阶段的犯意转化
犯罪预备阶段的此犯意在实行阶段转化为彼犯意,即行为人以此犯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却以彼犯意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行为构成实质的一罪,通常以实行阶段实施的犯罪论处。
例如:如甲事先准备了砍刀,准备杀死自己的仇人乙,但在去乙家的路上,改变犯意,认为将其打伤就可以了;或者相反,甲本意想打伤乙,但是在去乙家里的路上,改变犯意,意图将乙杀死。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笔者将行为人犯意转化之前的犯罪行为称为“前罪”,将犯意转化之后的犯罪行为称为“后罪”。对于以上两种情况,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应当以后罪的完成形态吸收前罪的犯罪预备形态,最终以实行阶段实施的犯罪既遂定罪处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重罪吸收轻罪,在上述的两个案例中,无论哪种情况都应当以故意杀人行为吸收故意伤害行为,按照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或者中止进行处罚。第三种观点,应当按照前罪的犯罪预备与后罪的犯罪既遂进行数罪并罚。
笔者认为,在上述的两个案例中,应当采用实行阶段行为吸收预备阶段行为的方法,如上述的第一个案例,就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第二个案例则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原因在于:前行为仅在预备阶段还未进行实行阶段,因客观情况或者行为人主观心态转化之后,在犯罪实行阶段仅实行了一个行为。行为人转化后犯意支配下的行为也是无缝接续了先前的预备行为。故应当按照后罪的既遂做一罪处理。
(二)在犯罪实行过程中的犯意转化
行为人在犯罪着手之后,改变了犯罪预备的犯意。对于该情形,原则上遵循这样的思路:犯意升高者,从新犯意(即以变更后的犯意为准);犯意降低者,从旧犯意(即以变更前的犯意为准)。例如:案例一,甲男在大街上看见乙女,原先的主观心态是想让乙女给自己口交,但在实施猥亵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犯意,继而实施了一个强奸的行为;案例二,甲男在大街上看见乙女,本意实施强奸行为,但是在准备实施的时候,乙谎称自己患有艾滋病。后甲男便让乙女给自己口交,在口交行为结束后,乙女离开案发现场。案例三,甲男在大街上看见乙女,本意实施强奸行为,但是在准备实施的时候,乙谎称自己正在经期期间。后甲男便让乙女给自己口交,在口交行为结束后,乙女离开案发现场。笔者为论述方便,认为强制猥亵行为是系低犯意,强奸行为系高犯意。
在上述的案例一中,甲在犯罪实行过程中由强制猥亵的故意转化为强奸的故意,属于犯意升高者,从新犯意——即以强奸罪既遂论处;而对于案例二,甲在犯罪实行过程中由强奸的故意转化为强制猥亵的故意,属于犯意降低者,从旧犯意——即以强奸罪(未遂)论处。在案例三中,甲也在实行犯罪过程中由强奸故意转化为强制猥亵的故意,仍属于犯意降低者,从旧犯意——但应以强奸罪(中止)论处。虽然案例二与案例三均属于犯意降低者,从旧意。但是区别在于:案例二中,甲男在知道乙女患有艾滋病后,按照一般认知,甲男从主观上已经不可能和其发生性关系,所以甲男的行为属于欲达目的而不能,因而是犯罪未遂;案例三中,乙女虽然称自己处于经期期间,但是经期并不妨碍双方性关系的发生,因而是甲男主动放弃了实施强奸行为,故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
需要注意的是,犯意降低者从旧意这一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难度较大,原因在于:认定行为人犯意降低必须要嫌疑人承认自己之前具有高犯意或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作为依托,而在司法实践中证据很难达到这一程度。例如:在认定故意杀人的案件中,行为人一般不会承认自己在之前就有故意杀人的主观心态。因此将很难认定其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的形态为中止,在无其他的情况下,只能根据行为人的陈述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罪。
综上分析,在行为人犯意转化的情况下,因转化的时间点不一致,如犯意是在预备阶段转化,则行为人仅构成实行行为一罪的既遂。而犯意是在实行阶段转化,则行为人构成重罪的既遂、未遂或中止的形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犯意的转化时间点不一致,处理原则也会存在有不同情况。在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前行为没有完成形态的情况下,针对同一犯罪对象,侵害同种法益的前提下,仅存在犯意转化的情况,不存在另起犯意的情节。
二、司法实践中认定另起犯意的情形
另起犯意在不同的犯罪阶段存在两种情形:
(一)在犯罪预备阶段的另起犯意
在犯罪预备阶段,针对不同质法益实施的犯罪行为。例如:甲男事先准备了抢劫银行的工具,准备实施抢劫银行的行为,但是在去银行的路上,看见乙女花容月貌,遂起歹意,产生了强奸的想法,在强奸行为实施完成后,逃离了现场,之后也没有实施抢劫的行为。在上述的案例中,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抢劫罪的犯罪预备与强奸罪既遂数罪并罚。
上述案例不能按照预备阶段犯意转化中的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处理。原因在于:行为人在预备阶段的准备工具的行为是为了实施了抢劫行为。该行为与之后的强奸行为不属于同质法益,无法被实行阶段的后罪吸收,因此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
(二)在实行犯罪过程中的另起犯意
在犯罪的实行阶段,针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的不同种类的犯罪行为属于另起犯意的行为。例如:案例一,甲事先准备了工具,准备在半夜大街上拦路实施抢劫行为。后甲在对路人乙进行抢劫的时候,发现乙花容月貌,遂起歹意,产生了强奸的想法,在強奸行为实施完成后,逃离了现场。案例二,甲深夜埋伏在路边意图强奸路过的妇女乙,待乙骑车路过时,甲以强奸的犯罪故意使用暴力制服了乙,准备实施强奸时发现乙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甲失望之际便另起犯意对乙实施了抢劫行为。
在上述的两个案例中,均属于在犯罪着手之后,针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的不同质的犯罪行为。属于另起犯意的行为,甲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以及强奸罪,应当按照数罪并罚处理。原因在于:甲的抢劫行为已经进入到了实行的阶段,不属于预备阶段,因而不能被实行行为所吸收。对抢劫的行为应当进行评价,而后甲又实施了一个不属于同种罪名的强奸行为,由于甲的抢劫故意与抢劫行为是在强奸行为中止之后产生的,也应当对该行为进行评价。行为人实施了两个不同种行为,分别侵害了两种不同的法益,故应当按照行为人触犯的两罪进行并罚。
另外,在犯罪实行阶段,针对不同对象实施的侵犯同种行为也应当认定为另起犯意,做数罪并罚处理。
例如:甲因故与乙发生矛盾,事先准备了一把菜刀,后在将乙砍了三四刀的时候,看见了自己的另一个仇人丙,后甲扔了菜刀,拳打脚踢把丙打成了重伤。乙在甲殴打丙的途中,逃离了案发现场。在该案当中,甲的行为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并且应当数罪并罚。该情形属于针对不同犯罪对象实施的同一犯罪类型并且是在前行为未有完成形态下的行为,对象不一样有且只有成立另起犯意。
三、论抢劫罪法律拟制的理论合理性
笔者认为在上述关于犯意转化及另起犯意的理论支撑下,行为人在实施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行为时,只要是在当场的情况下,就应当按照抢劫罪进行处罚。理由如下: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其中一点在于是否使对财物持有人使用了暴力。但是根据犯罪形态的完结情况会存在不同的处理。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中或实施完毕后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情形,盗窃行为实施完毕后,行为人出于灭口、报复等其他动机伤害、杀害被害人。第二种情形,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中,由于他人发现或误以为盗窃行为被发现等意志以外的因素出现,行为人为排除障碍而当场使用暴力。第三种情形,在盗窃行为实施完毕后并且取得被害人财物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针对第一种情形,由于盗窃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犯罪心态已经终结。而后另起一个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犯意。即在两个犯意支配下实施的两个行为,应以盗窃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也应当构成抢劫罪。该情况仍不在法律拟制的情况下探讨,仅从法学理论上进行分析,对于行为人而言,其在实施盗窃过程中被他人发现,属于意志以外的因素,盗窃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状态,而后行为人为了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转而对其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从而达到强行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当属于犯意转化,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典型的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成立抢劫罪。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当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笔者探讨该行为不在法律拟制中的转化抢劫前提下进行研究。分析如下:从实施盗窃的整个犯罪阶段来看,行为人在取得财物之后,是在逃跑的过程中使用暴力。笔者认为仍然属于“当场”的范畴,此时被害人并未丧失对物的占有,如果是在屋内取得财物后对被害人使用暴力,此时的被盗(被抢)物品仍然在屋内,被害人并未失去财物。因此盗窃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状态。行为人随后实际上使用的是抢劫的手段,使被害人脱离了对财物的占有。同样,如果行为人盗窃了财物之后离开了被害人居住的房屋,而后被害人一直有追赶行为人的行为。而后行为人在该过程中,具有殴打被害人的行为。笔者认为在该种情况下,即使被盗财物离开了封闭场所,因被害人一直追逐行为人,从主观上并未放弃对物的占有。这种情况应当属于“观念上的占有”,此时,应当是行为人和被害人共同占有被盗物品。而后也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行为,使被害人对被盗物品脱离了占有,本质上与第二种情况相同,也应当属于犯意转化,是由一个盗窃的犯意向抢劫的犯意的转化,因而属于低犯意向高犯意转化。行为人误以为自己取得了物的占有,但是实际上被害人在观念上仍然占有被盗物品。因而也应当按照犯意转化的原则。犯意升高者从新意的原则,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