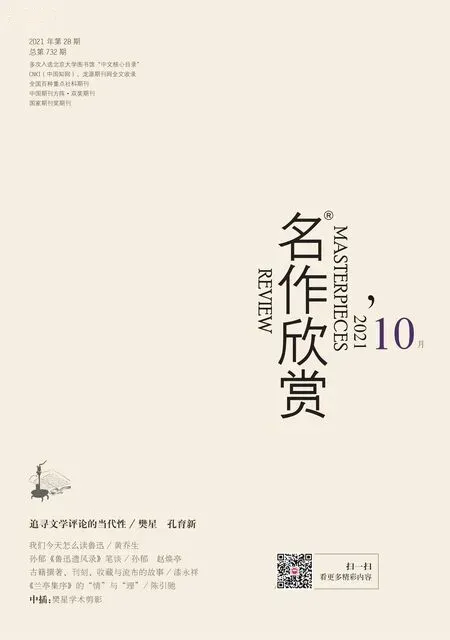雄深雅健与清丽芊绵——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与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比较探析
安徽 吴振华
文学史上某种文学传统线性系列中,前后出现的大家,后者往往自觉接受前者的影响,像李白推崇屈原、黄庭坚崇拜杜甫、辛弃疾学习苏轼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在古代散文发展历程中,“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对后代散文家的影响可谓深远,其中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等人的影响已经广为人知;而他对李清照的影响却鲜见论述,乍看起来,韩愈在诗歌散文方面造诣很深,而李清照则精于词的创作,仿佛他们没有任何关联,其实不然。李清照既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词人,也是散文大家,尽管她现存的散文并不多,但以《金石录后序》为代表,可以看出她的散文艺术造诣很深,其艺术特色继承了韩愈散文的一些笔法,尽管议论方面略微逊色,而体物言情细致精微,堪称宋文中的极品,很有研究价值。今就韩、李二文做一比较研究,以就教于通家。
以相同的文体记载惊天动地的历史
两文都属于文序中的“后序”,所谓“后”,一指一本书之后,一指一篇文章之后。韩愈的“后叙”,是在读李翰所写的《张巡传》之后,感到有很多缺失,而且详密的传文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既有重申的必要,还有一些轶事需要补充;李清照的“后序”,则是为了记录她和丈夫积毕生的心血收藏、鉴别、整理金石书画以及这些珍贵文物在靖康之变后流失遭毁弃的辛酸历程,由此保存一份既对丈夫也对文物的珍贵记忆。从文体类别来看,两文虽有相似性,也有一些区别。相似之处就是都属于序体,不同之处在于一者为单篇文章的读后杂记,一者为一部著作的相关情况叙录。由于两篇文章记录的历史事实具有独特的意义,因而两篇文章分别可以作为唐代与宋代的史传来对待。
韩愈文章所记的是唐代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张巡与许远联军进行著名的“睢阳保卫战”,这是一场关系唐王朝生死命运的战役,睢阳扼守江淮要冲,当时叛军以十三万人马围攻仅有一万士卒的睢阳孤城,尽管睢阳附近皆有重兵环绕驻扎,但是由于守将们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竟然没有一兵一卒前来增援,经历了大小四百余战,阻遏叛军前锋使之不能长驱江淮,坚守孤城十个月之后,终因弹尽粮绝,睢阳被攻破,张巡、许远等战死。然而,五十年后,历史的血迹未干,但是对历史的记忆却已经开始模糊。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然制造无耻的谰言来攻击当年誓死抗击叛军的英雄们,他们先是抛出“不该死守睢阳”论和“城破许远有责”论,引起张、许两家子弟对簿公堂,最终上诉朝廷。在当时藩镇割据的严峻形势下,既有为睢阳保卫战辩诬的必要,更有为以身殉国的英雄辩诬的必要,在坚持“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原则的基础上,韩愈浩气凛然、义正词严地驳斥这些无耻谣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维护英烈的崇高形象,对那些混淆视听“自比于逆乱,设淫词而助之攻”的小人予以辛辣的批判,揭露他们的险恶用心,然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自己搜集或友人提供的一些关于当年英雄们的轶事遗闻补充原有传记的缺失,使当年的英雄栩栩如生地再现于人们面前,具有了信史的价值。
李清照的文章以自己家庭遭遇为内容,以金石书画的收藏与毁弃为线索,记录他们夫妇搜集购买、鉴赏品评、精心保存文物并自娱自乐于其中的情景,以及历史巨变之后这些文物在兵戈动荡的岁月里或流失或遭抢劫、偷窃的遭遇,并围绕金石书画叙述了家庭变迁及家庭人物的命运,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靖康之变前后数十年的历史景象,成为一部纪实性的家史。如果再联系那个天荒地变的特殊时期,壮丽辉煌的北宋都城汴京被金人占领后,徽宗钦宗及其皇室成员被俘北上,皇宫及其皇城的多少历史文物或被掠夺或被毁坏,又有多少家庭遭遇到李清照一样的命运,像《金石录》这样的日积月累于清明时代的一部著作,其命运遭际也是一部当时的信史。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么靖康之难就是两宋历史与文化由强转弱的转折点。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国家遭到空前的浩劫,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战乱造成的时代伤痛必然会反映到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中来,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成为一代史诗,正是因为他在诗中融入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民的苦痛哀怨。当然,在表现历史的时候,作家都会采取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并做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合乎逻辑的判断,因而作品还必须具备史识。像杜甫“三吏”“三别”那样的新乐府诗既写出了当时战事的严酷,表现了在灾难面前统治者是怎样的昏庸无能,又是怎样的不惜民力,将战争的灾难转嫁到人民头上;同时又站在时代的高度,含着热泪鼓舞人民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参加平叛战争,保家卫国。严肃的现实批判精神与高昂的爱国精神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常常是舍小我存大我,因此杜诗给人的印象厚重而深邃。韩愈继承了杜甫的文学精神,他不仅在诗歌里发扬杜甫的新乐府精神,而且在他大量的散文里积极地宣扬儒家道统思想,想通过重建士人的文化品格来改变中唐时期庸俗卑劣的士风,从而改变由于藩镇割据而造成的衰败颓靡的世风,企图通过恢复中央号令四方的崇高威信,重新回到开元盛世,实现唐王朝的中兴。《张中丞传后叙》就是表现韩愈高瞻远瞩见识的重要作品,在安史之乱过去已经半个世纪的时候,围绕睢阳保卫战,从朝廷到民间都有一种糊涂认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舆论为藩镇张目,企图混淆视听,指责张巡和许远当时不及时逃走保存实力,以致造成睢阳城毁人亡的重大损失,并将城破的责任推给负责镇守西南城墙的太守许远,却没有人去指责那些拥强兵坐而相环,竟然为了保存实力而见死不救的军阀,这真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对睢阳战役的诋毁和对张巡、许远的污蔑,充分暴露了他们为藩镇割据张目的险恶用心。这时,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成为最重要的史识。睢阳战略地位重要,既是江淮的屏障,又是东部战场争夺的焦点,双方展开了长达十个月的拉锯战,投入兵力达到十几万。睢阳战役一方面牵制了大量的叛军,减轻了两京地区西线战场的压力,为收复两京争取了时间,同时作为屏障,有力地捍卫了唐王朝主要的财富来源地——江南地区——没有遭到破坏,为平叛战争源源不断提供财力物力。正是因为这场力量悬殊的搏斗,所以韩愈厉声诘问道:“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韩文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把握了时代脉搏的新动向。
李清照尽管没有像韩愈那样写出深刻的历史见解,但是她娓娓动人的细腻描述,将历史的面貌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在文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北宋时期(实际上是北宋末期)文化繁荣的局面,以一个官宦之家竟然能够集藏文物如许之多,足见当时文物的兴盛,由此也可以推想皇家藏品的丰富,随着当时修史的兴盛而带来金石学的繁荣。赵明诚和李清照尽毕生之力搜集的金石文物“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这是一笔不菲的文化遗产,由此可以透视北宋文化的兴盛。李清照以自己一家人的血泪,照见了历史的沧桑,也表现了对远去王朝的甜美追忆和无限眷恋。后人对李清照的同情,实际上也是对不幸遭到毁灭的北宋繁荣昌盛文化的深深悲惋。宇文所安先生认为“失去的东西却保存在记忆里”是记忆的本质,并认为李清照“这篇文字中的告诫的力量来自一种认识,认识到她自己的爱而不舍为她留下的伤疤,认识到推动那些狂热的爱而不舍的人们去做他们非做不可的事的那种共有的冲动,在她身上也发挥过作用。她也被回忆的引诱力所攫取,被缠卷在回忆的快感和她无法忘怀的伤痛之中”。宇文先生指出了李清照撰写这篇后序的心理动力,见解深刻,给人以启迪。其实,珍藏于记忆深处的东西往往因其价值的大小而决定其被记忆的程度深浅,沧桑历史巨变的当事人往往对所经历的盛世光景尤其萦怀,从《诗经》中的周大夫悲叹“黍离”,到庾信的“哀江南”赋,从杜甫追念开元盛世的《忆昔》,到李清照的后序,再到其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及张岱《陶庵梦忆》等笔记著作,都是抱着存一代之史的目的,表现对已经消失的盛世背影的追慕,借以表达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兴亡之感。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看,韩愈与李清照的散文内在气息相通,都表现出历史的悲凉厚重,呈现出一种苍茫浑灏的气象。
雄深雅健与清丽芊绵:韩、李散文各擅其胜
韩愈在评价柳宗元的文章时,指出柳文具有司马迁“雄深雅健”的特点。其实,这也是韩愈散文的主要特点。韩愈是破体派作家,主张诗文相通,提倡“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要求打通各种文体之间的壁垒,诗文相互借境生色,为文体的发展不断拓展新境。李清照也是一个学识丰赡的作家,独特的家学渊源与她聪颖的才华相结合,加上她潇洒透脱的处世态度,使她的诗词散文各具风采。而她与柳宗元一样都是尊体派文人,柳宗元主张诗歌与散文各有特性,提出“文有二道”之说,李清照则主张诗词各有独自的体性,提倡词“别是一家”之说,维护词体本色,严守诗词之别。如果说她存世不多的诗歌主要表现出她阳刚雄健格调,她的词主要表现她缠绵婉转的女性阴柔秀美特质的话,那么她的散文则呈现出偏向词体一样的清丽芊绵面貌,当然其中也不缺乏魏晋风度的潇洒。由此看来,李清照与韩愈看似没有多少相通之处,其实不然,他们在继承司马迁《史记》刻画人物、叙述历史事件的艺术技巧方面,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这一点在两篇文章中有所体现。
(一)刻画人物,象形生动
刻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人物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心理状态的描写,传达出人物的精神气韵。像《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著作,刻画人物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到司马迁写《史记》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如描写项羽巨鹿之战、东城快战、乌江自刎,写蔺相如完璧归赵,写荆轲刺秦王等,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在紧张激烈或剑拔弩张的环境气氛下,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似乎能够跳出发黄的书页,跃然于读者眼前。韩愈的散文继承了司马迁刻画人物的优长,并吸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世说新语》《搜神记》为代表的小说及唐代传奇的一些笔法,加以变化,使他散文中的人物描写达到形神兼备的高度。如文章这样描写张巡部将南霁云: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言,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之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是韩愈搜集的张巡部将的轶事。描写得虎虎有生气,南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而贺兰既无出兵意愿,又反而想乘机挖墙脚,这就激起了南霁云的义愤。他慷慨言辞,义不独食,又拔刀断指,用鲜血来示意,出城时再抽矢射塔,发誓破贼后志灭贺兰。短短一百多字,人物言行举止历历如画,且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将南霁云义薄云天、刚勇英烈、威猛豪荡的神采风貌表现出来了。又如写张巡轶事,通过当年部下于嵩的转述,突出张巡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和为文章神速异常,还有张巡发怒时“须髯辄张”的情态、就义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的视死如归情状等,尽管琐碎,却立体浮雕般将英雄的形象表现得丰满厚实、神采飞扬。由此可见韩愈将史家笔法与文学想象巧妙结合的艺术腕力。
李清照没有韩愈那样著史的经历,但对史书非常熟悉,又钦慕魏晋风度,所以她的散文既具有史传笔法,又兼备女性特有的从容细腻。如她叙述早年与丈夫在经济窘迫情况下购买金石书画文物的情景: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他们当年为了购买文物节衣缩食,若偶尔碰上名人书画或一代奇器,甚至质衣换钱、脱衣市易文物。最让人动容的是将徐熙的《牡丹图》带回家耽玩两夜,最终因无法凑足二十万钱而物归原主,夫妇怅然若失的心情,与先前一边吃着水果一边赏玩碑文的乐而忘忧情态相互映衬,活脱脱地勾勒出这对志趣相投的夫妻对金石文物的浓烈兴趣,及其“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的宏伟志愿。又如,李清照这样描述屏居乡里十年期间生活: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这是最具有李清照文章个性风采的描述,可以说将上文提到的“葛天氏之民”的悠闲自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共同校勘古书,共同赏玩书画彝鼎,指责瑕疵。更让人神往的是夫妇烹茶竞猜某言某事在某书某页,以中否角胜负的细节描写非常传神,甚至有时举杯大笑,连茶水也倾覆怀中,这种身处忧患却乐而忘忧的雅洁韵致,足见他们伉俪情深。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北宋晚期尽管全局上危机四伏,但在乡间文人雅士的家中还是洋溢着宁静悠闲的气氛,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深层辐射,他们沉浸在古代文化的海洋中,让生命与文物一起绽放光华。这一细节也充分体现出易安居士生平所具的魏晋风度。
还有,像描写赵明诚赴召离别时的形象“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也是精彩绝伦。当时形势严峻,北人纷纷南渡,南宋朝廷根基未稳,到处兵荒马乱,而李清照既要逃难还要照顾从青州精选的舟车运输而来的十五车文物,其艰辛窘迫之状可以想象,她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因而询问夫君:“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赵明诚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可见这位金石学家视文物为生命。每读这段文字,清照当年的情状仿佛总是历历在目,不得不钦佩李清照叙述复杂场景的高超驾驭能力。
(二)文气贯注,情感充沛
古人认为“文以气为主”,重视文章字里行间的气势,因为这“气”是一种生命所独具的生气,就像人无气就成死人一样,文章没有“气”也就没有神采缺少气象。韩愈提倡“气盛言宜”,认为只要站到道义的高度居高临下,深厚学养贮蓄于中,加上精神状态亢奋激昂,这样作者表达时就会“声之高下与言之长短皆宜”。文章气盛的重要基础还是一个“理”字。像韩愈的这篇文章,一股雄杰悲壮之气始终贯注全篇,在为睢阳战役与英雄辩诬时,气势凌厉,势如破竹,解剖刀一样的笔触直刺小人卑污的心脏。在描述南霁云乞师贺兰时,忽然变得慷慨激昂,而描述张巡与南霁云等人就义时则变为悲壮哀婉,结尾叙述张巡和许远的一些轶事,文气变得舒缓晃漾,期间也插叙张、许二家子弟的愚顽令人扼腕叹息,最后叙述于嵩死于猖獗恣肆的武人却无人为其申冤报仇则又令人陷入沉思哀伤。总之,韩愈这篇散文以表彰英雄为中心,时而抨击奸佞,时而悲叹世情,形成一曲气势豪迈宏壮悲惋的浩歌。方苞评曰:“截然五段,不用勾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又曰:“退之叙事文不学《史记》,而生气奋动处,不觉与之相近。”方苞论文强调义法,他所说的“神气流注”指的是韩文的气势充沛,而他说韩愈不学《史记》则是不当的,其实韩文深得司马迁的笔意。至于刘大櫆喜爱这篇文章“锋芒透露”,张裕钊赞美说“屈盘遒劲,雄岸自喜”等,都道出了韩文所具有的阳刚劲健之美。
相比之下,李清照的这篇散文尽管没有韩愈散文那样滔滔洪流一般的气势,但是其文如一股幽泉细流,穿行于幽谷涧石之间:时而缓缓流淌,淙淙有声;时而冲击岩石,喷射出晶莹的浪花;时而又静静地流入回潭,轻卷涟漪;时而也飞泻断崖,奇丽飘逸。从全篇文章来看,深情的追忆中夹着凄厉的悲惋是其主旋律,尽管开头的疑惑与结尾的告诫相互呼应,但本文的主意却并不在于此,或者说这样的告诫本身也是无尽的哀婉。悲伤为主的文气统帅下,以“靖康之难”为分界线,既有夫妇节衣缩食收购文物共同鉴赏的欢乐情景,犹如小溪欢快流淌时发出清脆悦耳的乐音;也有南奔逃难时四顾茫然的悲壮画面,犹如溪水跌落悬崖断壁时发出悲壮的呼号;还有遭遇抢劫、偷窃时的凄凉无奈,犹如溪水困于涧石深潭发出忧伤的悲鸣;至于未能购得名画的怅然与得到奇字的惊喜以及把玩残篇的慰藉,等等,犹如点缀溪流两岸偶然开放的灿然野花,饶有情趣。总之,李清照的这篇散文具有跌宕起伏、婉丽精曲的阴柔美。与韩文相同的是文中都贯注了作者充沛的感情,体现了作者独具的个性风采。
(三)叙述婉曲,剪裁得当
作为史传类文章,叙事的技巧都是非常讲究的,文章结构的安排往往颇费经营。韩愈这篇散文更是难度大,因为已有《张巡传》在,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是颇费周折的。韩愈不愧为文章大家,他总能够别出心裁,给人巧妙新颖之感。对于这篇文章的结构,林纾有精彩分析,特抄录如下:
后传之序,补遗也。凡传必有论赞,李翰之《传》,亦必有论,退之再加以论,直成蛇足,故变其称,曰《传后叙》。在体例,应补叙巡之遗事,然巡、远,共命之人也,势不能尊巡而黜远。李翰通人,视二公宜并为一。然为二公辩诬矣,乃不为远立传,此缺典也。故退之因补遗之际,先为许远表明心迹,斥小人之好议论。其下再将李翰之论一伸,痛快极矣。……文加叙加议,先议而后叙,议处斩钉截铁,具有真实力量,叙处风发电剽,字字生棱,读之令人气王。(《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二)
林纾认为前三段是根据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也就是李翰《张巡传》所提供的事实进行辩论;后两段根据韩愈在汴、徐二府所得的材料以及张籍所提供的材料,补叙遗事。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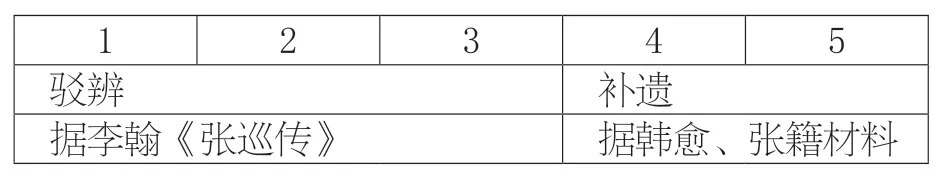
这篇文章材料比较琐碎,搜集起来颇为不易,最难的是如何将后面两段叙述与前面三段议论糅合成一个相互照应的整体,韩愈挥洒自如,前面的议论为后面的叙事展开了广阔的背景,既渲染了气氛,又提供了评价两位历史人物牺牲的价值尺度,有了这样一个宏伟的坐标,后面的叙事就可以对前面的议论进行有力的补充了。像南霁云的故事一方面回击了前面议论中小人们淫词的可笑,用铁的事实印证了在张巡许远血战时候“拥强兵坐而相环者”的无耻,另一方面以部将的刚烈正好陪衬主将的忠勇;又如写张巡读书记忆力惊人,写文章从不打草稿,似乎与睢阳战役无关,但它让我们看到这位精通军事英勇善战的将军,并不是一介武夫,而是胸怀韬略腹有诗书的儒者,特别是他在围城中跟士卒“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的”细节,更突出了他时刻关怀士卒冷暖的仁爱胸怀,这就使张巡的形象更加丰满,带有传奇色彩,也更能引起人们对英雄人格的敬仰;再如于嵩故事,一方面是张巡读书记忆力的见证者,另一方面突出张巡对部属的影响,再一方面通过于嵩的悲剧表明盘踞各地的武人还是非常猖獗的,最后这位参加睢阳战役的仅存者对张、许的蒙冤受屈也是一个照应,暗示了铲除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是多么刻不容缓!这样全部材料就都簇拥在主题的周围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成为一个严密的艺术整体了。
李清照的文章共分十段,前后两段互相照应抒发感慨,中间八段按照时间的自然顺序娓娓道来,期间不时穿插一些细节描写,其结构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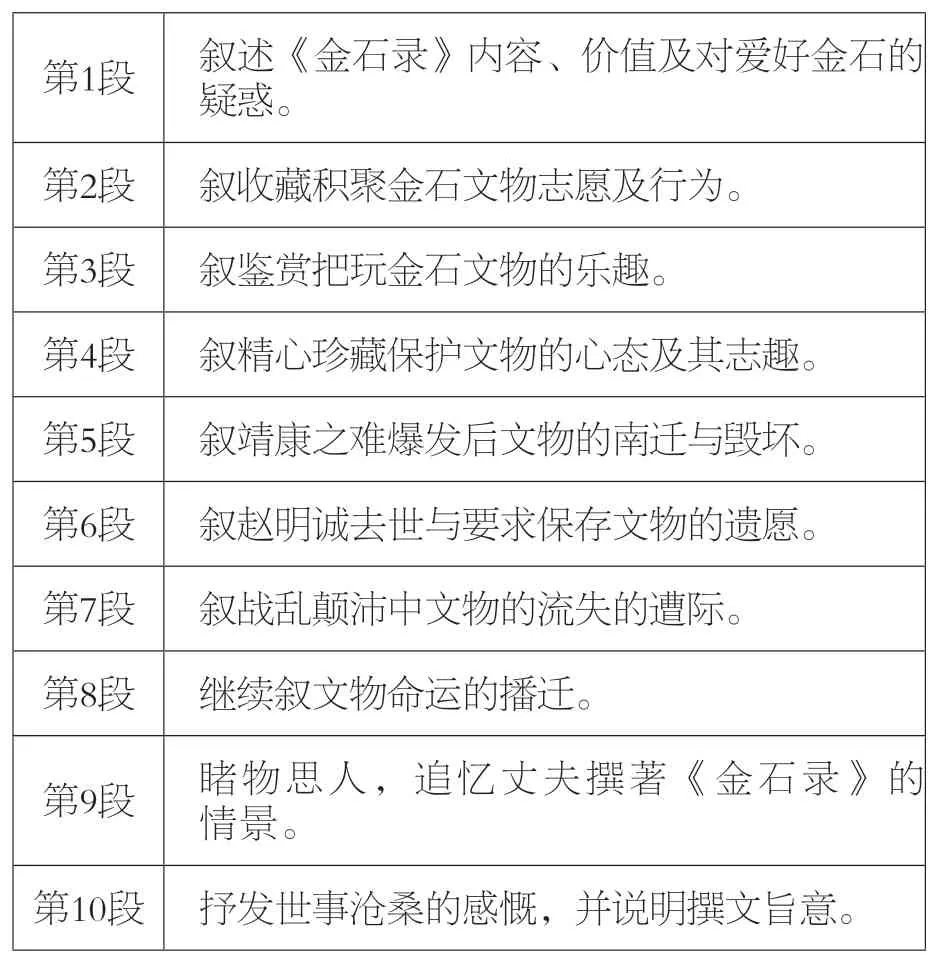
从上表可以看到李清照在剪裁布置的时候,紧紧围绕金石书画文物这一中心,然后由此生发出相关的人物故事,而这些故事又跟靖康之难的背景发生联系,文物和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变迁是息息相关的,文物的收购、保藏、转移、毁弃,系于主人公的命运播迁,而主人公的命运又受时代变迁的摆布。围绕着时代悲剧而产生的家庭悲剧和收藏历史文物事业被毁坏的悲剧融合在一起,由李清照情感的抑扬起伏贯穿全文,强烈的命运意识及无法与命运抗争的无奈,形成文章的暗线,从而使整篇文章成为一个详略得当的艺术整体。
如果说韩文靠浩瀚的气势取胜的话,那么李文则凭真挚的情感使人心灵得到滋润。
(四)用典设喻,凝练精确
韩愈与李清照都是学识渊博的作家,韩愈读书上自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书撰著,下至诗词歌赋、野史笔记、当代人的著作,乃是无书不读,且读书总是含英咀华、钩玄提要,作文也是融贯百家自成一己之长,他提炼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创造了很多表现力强、含义丰富且凝练简洁的语汇,其中擅长比喻是他最突出的地方。如韩愈在反驳小人们诬蔑的“城坏许远有责论”时,就是连引两个比喻“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来类比在当时叛军围攻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城池的被攻占只是时间问题,具有必然性,而什么地方首先被突破则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而不能对力战而败的许远横加指责。另外,韩文运用动词非常富有表现力,如“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其中“守”“捍”“战”“蔽遮”“沮遏”等词可谓力透纸背,将睢阳保卫战的重要意义揭示出来了,而且句式整散结合,长短交杂,夸张反问并举,气势磅礴,力量万钧。又如“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句中“擅”“坐”“观”“相环”等动词将那些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的军阀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此外,韩愈这篇散文句式变幻莫测,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精妙境地。
李清照家学渊源深厚,加上常年寄居家中,完全靠读书创作消磨时光,她读书范围也很广,而且有些书终身随其左右,文中说:“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馀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她南渡携带的书籍应该非常丰富,其中李杜韩柳的集子和南唐时代的写本书籍是她终身阅读把玩的珍品,因此,她的文章运用典故轻盈自如。本文就运用了大量典故,如:
自王播(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
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这些典故的运用说明李清照精熟经典、史传、笔记、诗词歌赋之类的著作,而且信手拈来如轻云卷舒,与文章流畅自然的韵致融合无间,既含义丰富婉曲,又感慨深沉。
韩愈、李清照是两位个性风貌截然不同的作家,他们各自精诣的艺术领域也完全不同,但由于李清照精熟韩文,所以在她的散文中也常有韩愈的影子,本文尝试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从中可以看到艺术作品除了情感的真挚是其灵魂之外,我们也会发现艺术风格迥异的作家之间也有某种灵犀一线相通。
①〔美〕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12 月版,第112 页。
②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73 页。
③孙琮云:此篇纯学《史记》。前幅是许远传,中幅是南霁云传,后幅是张巡传。妙在前幅俱用宽缓之笔,将许愿心事一一表白。中、后幅俱用古劲之笔,将南霁云、张巡事迹一一写生,比之史迁,何多让焉!读南霁云一段,《游侠转》逊其激烈。(《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韩昌黎集卷四》)〔按〕此论非常切当,既指出了韩文的艺术渊源,又道出了韩文新的创造。
④刘、张评语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