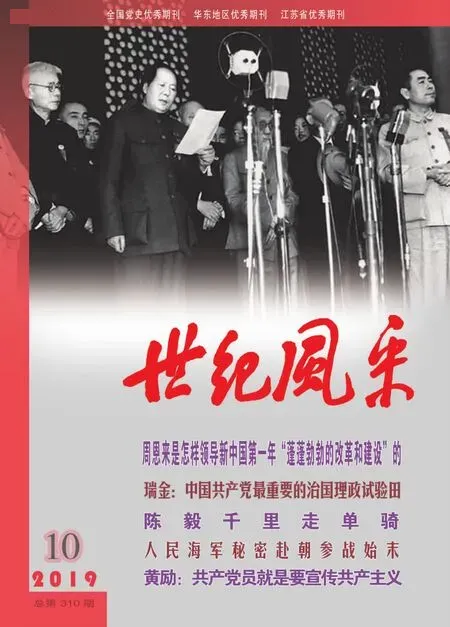鲁迅病逝及葬礼纪实
吴雪晴

安葬鲁迅时,上海各界为鲁迅送灵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鲁迅的逝世,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上海也为他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而肃穆庄严的葬礼。
病情加重立遗嘱
鲁迅的身体本来就不好,1935年的下半年,病情开始恶化。鲁迅病情恶化的原因,主要是过重刺激和长期劳累所致。1935年3月,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鲁迅多方设法营救,原准备发起公开营救的抗议运动,但未能实现。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悲痛不已,身体受到打击。他为了纪念战友,仍扶病编辑亡友的译文,出版了两册《海上述林》。1935年8月,著名共产党人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在牺牲前,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的文稿《可爱的中国》等托人辗转送到鲁迅手中,希望鲁迅通过关系将它转交中共中央。虽然鲁迅不认识方志敏,但他从这些文稿中看到方志敏对革命事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想方设法将烈士的文稿转交给了中共地下组织。得知方志敏牺牲的消息后,鲁迅义愤填膺,这更加损伤了他的身体。
为了鲁迅的健康,他的许多亲友劝他住院治疗,或转地疗养,或到国外治疗。他的朋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还转达了苏联的邀请:请鲁迅到苏联游历并疗养。鲁迅为了留在国内更好地同敌人战斗,一一加以婉拒。他对前来劝说的茅盾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1936年初,在严寒的气候中,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气喘,发烧。鲁迅的亲属和几个好友瞒着他由史沫特莱请了一位美国医生进行检查。医生对鲁迅病情严重的程度十分吃惊。他惊讶地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了。鲁迅对医生的这一“判决”十分从容,他认为医生再高明,也一定没学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处方,所以也没有请美国医生继续治疗。
对于死亡的即将来临,鲁迅十分镇定,他要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抓紧工作。同时,对身后之事也做了一些考虑。在病中,他写下了随笔《死》一文,刊于《中天》杂志1936年第2期。在文中,鲁迅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还为自己拟了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以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不和他接近。
巨星陨落神州惊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的病情突然加重。这天上午,他在住所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邨9号寓内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以纪念刚去世不久的章太炎。午后,他独自外出拜访日本友人,天黑时才回家。晚上,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来,两人谈至夜11时,其中商谈了鲁迅搬家一事。
周建人走后,鲁迅即上床就寝。大约是由于白天过分劳累和外出受风寒的缘故,他心情烦躁,久久不能入眠。10月18日凌晨三时半,鲁迅气喘加剧,继而咳嗽,他弯曲着身体,双手抱脚而坐,十分痛苦。晨6时30左右,鲁迅支撑着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一短信,通知他“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请他速请医生。信送出不一会儿,内山完造和日本医生须藤赶来,帮其注射服药。但鲁迅病情仍未有好转。
在18日的一整天里,虽然有医生全力抢救,但鲁迅的病情仍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说话也困难。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仍挣扎地戴上眼镜,将报上《译文》的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触文字。之后,鲁迅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19日凌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突然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经注射两剂强心针后,仍然无效。至5时25分,死神终于夺走了年仅55岁的一代文豪。

鲁迅
鲁迅去世后,悲痛欲绝的许广平与周建人等即商议葬事安排。许广平派内山书店的一位店员去通知胡风。胡风赶到鲁迅寓所后,许广平要胡风做记录,记下送讣告的地名、人名。不一会儿,得到噩耗的冯雪峰、宋庆龄等人赶来吊唁。冯雪峰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万国殡仪馆承办,并提出鲁迅是一代文化伟人,在殡仪馆只是让群众吊唁,瞻仰遗容,不要西式、宗教的仪式。他们还拟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关于这个名单,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有四个版本。第一个,1936年10月19日上海《大晚报》发表的《鲁迅先生讣告》中13人: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曹靖华、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1936年10月20日,上海各报(包括《大美报》)刊登《讣告》中为8人:马相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史沫特莱、萧参(萧三);同一天,日本报纸《日日新闻》刊登的是8人: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斯梅达列夫人(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萧参(萧三);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冯雪峰用铅笔拟的名单为9人: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参(萧三)。现在看来,10月19日《大美报》的13人名单肯定是错的,它竟然包括了与鲁迅素有嫌隙的二弟周作人,明显是《大美报》想当然。其他几个版本一是8人一是9人,核心问题是是否有毛泽东,究竟哪个名单是真实的,还需史学家们进一步研究。
鲁迅逝世的消息在上海文化界迅速传开,沈钧儒、夏丐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柯灵、黄源、萧军等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到鲁迅寓所吊唁。当时国际上流行为名人遗容做石膏模型的传统,受家属之邀,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赶来,用一块软体石膏,为鲁迅做面部石膏模型。下午2时,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王士珍(摄影师)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卧室镜头。此后,明星公司又拍摄了万国殡仪馆吊唁和万国公墓安葬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下午3时,由内山完造联系安排,万国殡仪馆的“克里斯”黑色柩车开入大陆新邨,用白布裹好鲁迅遗体,放入灵车中的铜棺运回殡仪馆。
鲁迅的逝世,不仅在上海,在全中国,甚至在外国文学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日当晚,上海《大晚报》就刊出讣告。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各界人士纷纷发来唁函、唁电。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连续发出三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对鲁迅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一份发给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一份《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共中央表示:“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指出鲁迅“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各界人士的悼念
10月20日、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是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鲁迅遗容时间。
19日晚,胡风、黄源、雨田、萧军、周文等5人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遗体守夜。悲痛的萧军一直跪在鲁迅的灵前,直到夜深人静也不肯起来。20日上午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在殡仪馆的门前拱门上方挂着“鲁迅先生丧仪”的白色横幅,门首设签到处。灵堂四壁悬挂各界人士所送挽联、挽词。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为:“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远在日本不能归国的郭沫若送来的挽词为:“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蔡元培的挽联为:“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茅盾当时正在家乡桐乡乌镇,接到鲁迅逝世的电报后立即出发去上海,但因痔疮发作,疼痛不能行走,只得请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前去吊唁。郁达夫时在福州,10月19日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连夜致电许广平表示哀悼。翌日乘海船赴上海,在船上作《对于鲁迅死的感想》,表示:“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在。”终于在22日赶上了瞻仰鲁迅遗容,参加了葬礼。曹聚仁的挽联为:“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春。”
鲁迅的灵柩原停放在殡仪馆二楼的二号房间内,因吊唁的人太多,房间狭小,20日上午10时许移至一楼的礼堂内。灵堂正中挂着鲁迅遗像,四周堆满花篮,中间安放着蔡元培、何香凝等各界人士献的花圈。灵桌上另置一张鲁迅的小照片,为沙飞所摄鲁迅在木刻展上与青年木刻家交谈抽烟的情景。遗像两边供着两瓶鲜花,上面插着两张纸条,写着:“鲁迅老师千古,十二个青年敬献。”下面放着一张由木刻家力群所作的木刻《鲁迅像》,这是鲁迅生前最满意的一张作品。灵桌上放着鲁迅生前用的一本稿纸,一个笔架,一瓶墨水和一支钢笔等文具用品。礼堂门框上挂着由草明等16位青年作家合献的中间有五角星的轭形鲜花拱门。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以世界语文字及拉丁字书就的两幅巨大布额悬挂两侧;法电工人读书班所献的松柏牌坊,上书“失我良师”四个大字。灵堂里窗户都垂着绒帘,灯光黝暗,气氛肃穆。
灵桌前横置着鲁迅的遗体,与灵桌稍有距离,以供瞻仰遗容者绕遗体而过。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盖深色绵绸被,止及胸际。他两颊廋削,朴素庄严之至,就像劳累了一天后正在沉睡。许广平手书的挽辞《鲁迅夫子》放在灵床前。
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以及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均亲来吊唁。来得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他们大多读过鲁迅的作品,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据统计,20日一天前来吊唁者有团体102个,其中学校团体就有50多个,吊客5298人。21日,前来吊唁的人更多,团体增加到80多个。吊唁的人们在鲁迅的遗容前站着,垂下了头,眼眶里溢出了热泪……
21日下午3时至4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大殓时,在场者有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及女儿、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郑振铎、池田幸子以及治丧职员共30多人。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许广平悲极伏地痛哭失声,其他人也为之落泪。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鲁迅身着白纺绸衬衫裤,咖啡色薄棉袍,白袜、白底黑鞋,外裹咖啡色棉衾,上覆绯色面子湖色夹里之彩绣锦缎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深红色楠木棺椁,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首部,供人瞻仰。22日上午,前来与鲁迅做最后告别的群众更多,殡仪馆内挤满了人,门外的马路上更是人山人海。

宋庆龄、许广平和海婴在鲁迅葬礼上
在吊唁期间,治丧委员会每日收到国内外大量的唁电、唁函,其中来自国外的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日本改造社、大阪《每日新闻》社、朝鲜京城大学,以及一些国际文学界知名人士。
沉痛、肃穆的葬礼
鲁迅的墓地,选在上海西郊的万国公墓。1936年10月22日下午13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启灵祭”。家属、亲友和治丧委员会成员等30多人肃立致哀,向灵柩三鞠躬,殡仪馆工作人员将外层棺盖封严。接着,由黄源、萧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巴金、张天翼等人扶灵柩出礼堂,移置柩车内,执绋者随柩而行。
14时30分,送殡队伍开始出发,原定的路线是经过上海的繁华地段,但由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反对,只好改为沿胶州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到虹桥路。走在最前面的,是由一批作家签名的白布横幅,额题“鲁迅先生殡仪”六个大字为张天翼手书,由作家蒋牧良、欧阳山执掌。后为乐队,几十名乐手吹奏哀乐。然后为一长列人,手持各界人士送的花圈、挽联。紧接着的是歌咏队,唱着由冼星海、麦新等创作的悼念鲁迅的歌曲。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鲁迅的遗像,它是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其形象刚毅、坚定、栩栩如生。画像后为鲁迅的两位侄女(周建人的女儿)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分乘四辆汽车紧随其后。女作家草明和雨田陪伴着悲伤的许广平。由于海婴年幼,不谙世事,一如往日那样天真活泼,但有人问起他时,他回答说:“爸爸睡了,他在休息。”在场的草明事后回忆说,这个稚嫩的孩童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鲁迅先生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心里!
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巡捕和警察对送葬队伍进行监视。但是,沿途仍有数不清的民众加入送葬队伍,使队伍从出发时的6000余人很快扩大到几万人。他们代表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愿,来送别自己的导师、战士,向黑暗统治进行示威。一路上,不断有人散发纪念鲁迅的传单,高呼“继承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16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主持礼仪,沈钧儒致悼词,介绍鲁迅的生平及成就。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政府迫害鲁迅。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将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民族魂”三字为沈钧儒手书),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盖上石板、土。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无数人的痛哭声和断断续续的《安息歌》的歌声。
对于鲁迅的逝世,最伤心的当数许广平女士。在鲁迅安葬后,上海报纸上刊登的许广平所写的哀词,就表达了她对鲁迅的深厚感情。许广平写道:“悲哀的雾团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总是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关于丧事的几个问题
鲁迅丧事筹办过程中,有几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鲁迅逝世后,各界人士送来大量的挽联、花圈,这其中绝大多数是鲁迅的好友与战友,但也有少数鲁迅生前曾经批判过的人,有的甚至是敌人。鲁迅逝世前曾撰文痛批过徐懋庸。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徐异常悲痛,他认为他始终把鲁迅视为革命的朋友,是鲁迅误会了他,鲁迅总有一天会谅解他的。现在鲁迅逝世,这个机会再也不会有了,于是自撰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他本想将挽联亲自送到殡仪馆,但有朋友担心他去了会遭到吊唁群众怒视,他便托曹聚仁的夫人将挽联带到殡仪馆。最后,徐懋庸鼓足勇气,还是去了殡仪馆,在鲁迅的遗体前默哀了一分钟。曾和鲁迅进行过论战的周扬、夏衍等人,获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也感到十分悲痛。因鲁迅的家和殡仪馆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他们不能亲去吊唁,故派沙汀、艾芜代表他们去向鲁迅的遗体致哀。
对于鲁迅的逝世,国民党要人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送了花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也给鲁迅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第二,丧事活动中的重大问题,都由冯雪峰代表中共党组织与治丧委员会、许广平等人协商,治丧办事处由胡风负责。胡风是鲁迅生前最信任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在葬礼中决定丧事程序,如群众瞻仰遗体的时间安排、灵前守灵人的名单等。萧军实际上做了葬礼活动的“总指挥”,黄源、雨田、周文、孟十还为“灵前司事”。鲁迅生前的最后几年在上海没有固定工作,一直靠稿酬度日。虽然鲁迅稿酬不薄,但开销也大,没有多少积蓄。再加上根据遗嘱又不收礼,故殡仪馆费用、购买墓地等经费,原由沈钧儒表示由救国会负担。据胡风回忆,救国会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出钱。丧葬所需经费二三千元(其中鲁迅墓穴价格为580元)全由许广平负担,其来源是鲁迅生前被蔡元培聘请到中央研究院任职的薪水(鲁迅并未就职,但蔡元培薪水照发,以此方式资助鲁迅),这笔钱鲁迅一分未动,全部存起来了。这次被许广平用在了鲁迅的丧事上。鲁迅的棺木是宋庆龄、孔德沚、王蕴如(周建人的夫人)陪同许广平去挑选的,跑了几家棺木店后由许广平选中一款900元的西洋式棺木,此款为宋庆龄所出,因此鲁迅棺木实际上为宋庆龄所赠。鲁迅的墓地由沈钧儒联系,他对公墓负责人说,死者是了不起的伟人,故不讲迷信求风水,墓地四周要留有空地,以便千秋后代举行悼念活动。
鲁迅的墓碑简陋:坟墓只是个小小土堆,后面树一块梯型水泥墓碑,高71.2厘米,顶宽31.5厘米,底宽58厘米。碑的上部镶着高38厘米、宽25厘米的瓷制鲁迅像,下部刻着横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字样,字体幼稚而工整,乃是当时仅7岁的周海婴所写。为这事,冯雪峰曾安慰许广平:将来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国葬。1947年9月,鲁迅的墓地进行了扩建,面积达到64平方米,用花岗石围成正方形,墓椁后是野山式圆顶墓碑。碑面嵌有高66厘米、宽60厘米的黑石块,上面镶着椭圆形的瓷质鲁迅像,像下横写着“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下面还有两行小字:“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绍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卒于上海”,均为阴文金字。此碑文为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书写。1956年,有关方面举行隆重仪式,将鲁迅灵柩从万国公墓迁葬上海虹口公园,并在墓前塑高2.1米鲁迅铜像。他左手执书,右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面容坚毅而亲切,目光深邃,炯炯有神,体现了鲁迅的精神风貌。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被刻在一块高1米、宽0.8米的花岗石上,远远望去,雄健有力,金光闪烁。

鲁迅出殡,巴金、胡风等16人抬棺
第三,关于鲁迅逝世的病因,当时一直认为是死于肺结核。1984年2月22日,上海鲁迅纪念馆邀集部分我国著名的肺科、放射科专家,对鲁迅生前所摄的最后一张X光片(1936年6月15日拍),以及鲁迅的病历,进行了研究。最后专家一致认为,鲁迅的肺结核病属中等程度,这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泡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死亡。这个结论公布后,国内曾有人怀疑鲁迅的日本医生须藤故意误诊和处置不当,甚至有可能暗害鲁迅,引发了一场风波。但绝大多数鲁迅研究专家和鲁迅之子周海婴表示,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和须藤医生的医疗经验来看,须藤医生的治疗没有大的问题,尚无证据证明须藤暗害鲁迅,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