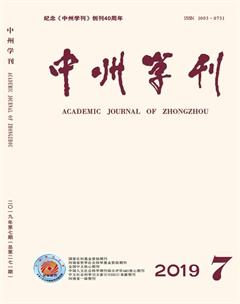从《小鲍庄》的批评位移看媒介对经典的重塑
李军辉
摘要:每个时代文学经典价值的发现与阐释,都要经过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媒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传媒影响下,文学批评不仅指认经典,而且会改写经典的生成方式,推动文学作品放弃旧观念,走向文学经典的核心位置。《小鲍庄》发表后,传统文学批评把它纳入“反思文学”范畴,但在“寻根文学”兴起后,文学批评的重点转向小说的传统文化,将其纳入“寻根文学”批评领域,重塑了作家的认同。以媒介为中心,多种合力使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从而居于“寻根文学”的中心。
关键词:媒介;《小鲍庄》;批评位移;文化反思;寻根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7-0146-06
20世纪80年代是以文学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文学报刊不仅向我们呈现出多元、丰富的文学世界,更能呈现出脉络化的文学批评踪迹。文学批评背后蕴藏着媒体效应的巨大推力。在传媒影响下,文学批评不仅能指认经典,而且会改写经典的生成方式,对经典进行重塑。在文学批评领域,我们也应该对媒介效应保持警惕,对文学媒介的传播力进行剥离式的分析,回到文学发生现场,进一步揭示文学媒介怎样改变文学批评的重心,怎样改变我们想象与体验文学作品的方式,怎样对经典进行重塑。
一、媒介批评对作品文学史价值的确认
王安忆的《小鲍庄》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在今天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它和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一起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其经典性被诠释为“表达作家对儒家文化的‘仁义精神与对这一精神崩溃的理解”①。然而,《小鲍庄》在发表之初,并未旗帜鲜明地打着“寻根文学”的旗号,它后来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是媒介批评的功劳。
事实上,紧随《小鲍庄》发表之后的评论文章虽然赞赏作品的独特之处,但未将其与“寻根文学”联系起来。在1985年最早的几篇批评文章里,对小说较之作者此前作品体现出来的“思想转变”“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的革命话语批评之类的文化反思仍被作为评价《小鲍庄》的重要参照。后来批评界在对这一创作现象进行归纳时,“批评家基于理论阐释对文本搜寻的必要”②,因其在文学取材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成分的书写,显示作者在创作上的探索和突破,而将其列入“寻根”目下。
《小鲍庄》发表后不久的1985年3月,文学评论家李洁非、张陵敏锐地发现其与王安忆之前的创作不同,很快在《文学自由谈》第1期发表《“小鲍庄”与我们的“理论”》进行剖析,这也是公开发表关于《小鲍庄》的第一篇评论。该文认为,《小鲍庄》的出现“使整个上海文学界为之一振”,是“这个城市的小说创作开始摆脱‘小家子气的征兆”③。二人把王安忆小说中书写场域由淮北平原到上海的转换视为由“旧我”向“新我”的转变,这种转变“背叛她在艺术上的初始状态,渐近于她的艺术理想”④。这种理想的实现是“她对我们的‘理论的背叛”,“愈让我们悟察到以往用来处理生活素材的艺术‘典型化原则是如此虚伪、矫揉造作和荒诞”⑤,而这种“‘典型化原则曾经是上个时代的文艺实践的成功概括”⑥。李洁非、张陵在为《小鲍庄》以“朝气蓬勃的创作实践”对“典型化原则”进行抛弃感到欣喜之余,不禁感叹自己的“职业自尊心受到了伤害”⑦,因为“对现有‘理论的批判或突破”⑧本该由自己这样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完成。显然,李洁非们更加注意的是作品对革命文学中“典型化原则”抛弃后的文体价值。当然,此文的撰写不排除与1985年前后文学思潮迭起,文学批评史和创作史都对文学转型要求迫切的主流话语调整适应的生存之策有关。但文中一再重审《小鲍庄》对“典型化原则”的抛弃,从中读出其對旧文学经典的颠覆,对新文学经典的再建这一审美上的创作实践,还是道出了《小鲍庄》对西方“现代派”影响下创作手法的改变给文坛带来的新鲜气息,以及这种创作方法在新形势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该文并没有提及《小鲍庄》在“寻根文学”方面的创作意图和方法结论。
紧随其后,《当代作家评论》在1986年第1期重磅推出4篇对《小鲍庄》的评价之作,分别是洁泯的《〈小鲍庄〉散论》、畅广元的《〈小鲍庄〉心理谈》、陈思和的《双重迭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和李劼的《是临摹,也是开拓——〈你别无选择〉和〈小鲍庄〉之我见》。洁泯之文论述了《小鲍庄》对国民性和人性的挖掘及反思,认为“文学的反思,已经从单一的政治和社会题旨的变易,延伸到人性摹写的深化”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开掘民族文化素质中的负量”⑩的努力以及“改造民族的灵魂”的追求。畅广元之文从群体性意识角度来分析“在这种仁义的伦理规范下,人们作为群体的一员的自觉性极强”的心理形成机制,并认为作者运用“心理距离”的创作实践来“自觉地调整其审美心理结构,重新组织自己审美创造的心理力”,以此对小鲍庄“人们心理上对群体意志的绝对遵从性和对偏离群体的恐惧感”进行深层剖析。陈思和之文运用“神话模式”来解释小说叙述的表层文本小鲍庄的生存世界和文体背后隐含的“要读者的体验与领悟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的另一个世界。他运用完整、系统、全面的理论分析来说明《小鲍庄》“宗教的神话模式的运用,不但使这部小说增添了现实的讽刺意义,而且超越了一般农村题材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容量,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人类苦难等一系列永恒主题的作品”。李劼之文肯定《小鲍庄》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认为小说是对《百年孤独》的一种描摹,同时又“显示出了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个性”。文中将《小鲍庄》和刘索拉具有现代派创作特点的《你别无选择》放在一起探讨,显然是为了凸显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综合以上几篇评论文章,《小鲍庄》在发表之初,的确在评论界引起了关注,但评论的焦点集中在思想领域的反思、心理距离的创作手法、“神话模式”的表本象征以及现代派创作特点,这些评论基本上还是把作品框定在“反思文学”范畴,并没有以“寻根文学”待之。即使是1985年“寻根文学”发起者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阿城等人自信满满地发起“寻根文学”宣言之后,评论界对《小鲍庄》的批评仍然围绕“反思文学”的创作手法、创作观念及取材等问题进行论述。
这些批评家虽然没有明确将《小鲍庄》归属于“寻根文学”作品,但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是注意到《小鲍庄》和《百年孤独》创作手法的相似性;第二是关注《小鲍庄》对民族心理、传统文化的挖掘。这些批评与“寻根文学”注重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有相通之处,被后来带有“寻根文学”归纳倾向的批评文章积极引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评所写的《面对新的文学现象——〈小说评论〉、〈延河〉召开部分小说讨论会记略》一文中明确提到,评论界在总结1985年的小说创作时,已经开始把王安忆的《小鲍庄》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等寻根派作品放在一起,明显用寻根意识来概括其文化深意;文学批评的重点由“反思文学”向“寻根文学”转移,“寻根文学”具有三种创作倾向:一是“写原始自然的封闭状态所产生的奇闻异事,揭示传统文化中阻碍现代化进程的落后保守的意识”,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从当代生活出发去写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代人意识的影响,写当代人的观念在传统中的蜕变过程”,三是“写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
伴随着“寻根”主张的提出,《文艺报》等国内多家重要报刊顺应潮流地组织起关于文学“寻根”的讨论,很快将“寻根”文学创作和讨论推向高潮。《小鲍庄》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仁”的独特书写,被批评界归到“寻根文学”旗下。上述结论成为后来文学史写作中对《小鲍庄》的基本表述与定位,《小鲍庄》成为“寻根文学”的经典代表作品。《小鲍庄》在成为“寻根文学”经典作品之前的这段批评隐含的文学史价值不可忽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鲍庄》是在媒介批评话语中从文化反思走向寻根。
二、媒介力量对作家创作趋向的改变
《小鲍庄》发表之初被批评界冠以“文化反思”的标签,后又在文学思潮涌起的过程中以“文化寻根”的面目呈现,被纳入“寻根文学”知识话语系统,这与文学传媒的发声重点有关。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不断更新的时代,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大量涌入,文学媒介的话语中心不断更迭,更趋向于西方新的文学理论。这种时代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对王安忆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安忆在《小鲍庄》创作前后的文学活动和话语言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创作。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这次出门远行对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她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友,审美趣味和创作手法因此发生重要的变化。时空上的跨度激活了她对中国本土的记忆,西方文化思想进一步扩展了她的文学视野,使她萌生了在本土传统文化的森林里提升书写经验的意愿。归国后熟悉的一切又让她“觉出了生活的陌生,和以往的似有点两样”,东西方许多方面的差异让她在写作时“有些不知所措,下不了笔”,虽然“再不甘心在自己的经验中看待生活”,但她还是非常庆幸能够“拉开了一段距离来看这生活”。美国之行让她对本土经验的书写,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书写多了一些思考。《小鲍庄》就是她从美国归来后创作的一篇重要作品。
批评界热衷于将《小鲍庄》和《百年孤独》对比,并认为美国之行是王安忆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但王安忆本人一开始并不认同。陈村在给王安忆的信中提到她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但王安忆在回信中并未直接回应,而是在写给陈村的信中有意凸显其创作《小鲍庄》的来源是中国的乡村。在这场对话中,王安忆一再强调自己去过那个村庄,似乎不太愿意把《小鲍庄》的创作和《百年孤独》联系起来,而是更愿意把这种创作与当时的“寻根文学”热潮联系起来。
1987年,复旦大学曾以《小鲍庄》为主题专门举办一场王安忆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王安憶一再声明,“《小鲍庄》里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原型是我在一次采访中获得的”,并“清楚地叙述了小说写作的‘缘起、‘人物原型和‘故事原生态”,一再强调她创作的独立性。她那详细清楚的叙述除了想让读者相信其作品创作是来自于自己熟知的生活之外,更多的是想远离批评家给《小鲍庄》安排的西方视野和概念桎梏。当中文系学生刘福和向她提问“您的《小鲍庄》是不是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时,她愣了一下(没有想到在自己对小说创作的缘由和人物原型解释的这么清楚之后,还有人这样问她),回答道:“我很喜欢《百年孤独》,但《小鲍庄》没有直接受它的影响。《小鲍庄》写的环境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些事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当另一个学生韩建新问及美国之行对她有没有影响时,她倒坦然承认:“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
从这次对话来看,王安忆对自己创作的认识印证了《小鲍庄》发表后不久批评家洁泯等对其国民性和人性的挖掘及反思的判断。《小鲍庄》的创作起点,是在当时历史条件观照下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在作品的设计方面,作者的美国之行使其从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对贫穷落后的农村文化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恰好印证了新的文学成规中对革命文学叙事的“典型化”的反驳,顺应了当时文学创作回到普通人的日常叙事上的创作实践。
程光炜认为,这两名复旦学生的提问值得特别注意。虽然作家创作的个人性经验是作品形成的基础,但接受过专业训练、科班出身的复旦学子俨然承担了批评家的角色,他们犀利的提问代表了文学批评者眼中的《小鲍庄》。他们认为《小鲍庄》和《百年孤独》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王安忆创作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作品的审美意蕴和寻根派文学同根同源,他们以自己的批评眼光为《小鲍庄》归类站队。他们认为美国之行对于《小鲍庄》的创作意义非凡,虽然作者也承认美国之行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有影响,但远非批评家眼中的“决定性”因素,只是让作者有了另一种审视中国文化的眼光。这是作家自述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作品创作。
“批评早已管制和转移了作者希望暗示的东西”,在批评的强大势力之下,“作家本人想强调或作品本已存在的另一些叙述层面则被压瘪、被忘却因而可能会逐渐消失”。《小鲍庄》创作的动机被王安忆解释为想写一个乡下的故事;文学批评则敏锐地把作品和“寻根派”之间建立联系。
当我们把眼光转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现场,重新梳理《小鲍庄》创作的前因后果、批评历史时发展,除却小说在批评视野中不断被讨论、被归类的批评系统构建之外,作家最初的创作意图也会在批评潮流的裹挟下发生变化。“批评家的这种‘自卑和惭愧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一种始终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作家作品之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促进他们对文学作品进行定论。这也提醒研究者,今天文学史中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给出的定性结论,需要将其放到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
三、叙述主体的价值体现:小鲍庄的“仁义”故事
从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思潮与现代派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尽管批评力量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文学都或隐或显地与现实批评话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批评机制下,虽然题材和视野有所不同,但对民族文化的严肃思考成为批评家在归纳寻根文学创作时的共同追求。《小鲍庄》就这样在文学媒介主导的文学潮流中被归入“寻根文学”创作,强大的媒介批评塑造机制改变了文学创作的“原始性”,作家的创作初衷也不得不与批评机制趋同,其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有意味的形式”在当下文学批评中渐渐被淡化。因此,重新梳理《小鲍庄》的创作思路变得异常重要。
正如《小鲍庄》发表后评论家所指出的,小说“既突出着共同的儒学文化氛围和不同人物各自的价值观念前提,又显示出这一切文化价值因素的孤立、呆滞和可怜”。从文本的表层叙事来看,作家着力凸显小鲍庄的“仁义”故事。在小鲍庄人的印象中,“仁义”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似乎与生俱来。但现实中生活在小鲍庄的每个人,却都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作者在叙述中没有超越“故事”的高度,小鲍庄人表面看来还是很“仁义”的,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但读者发现,这“仁义”的背后却有着让人吃惊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故事性的存在来突出文化寻根的意义看起来已经是无效的,但文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却显而易见。经过作家对故事情节的艺术加工,小说主题向文化反思拓展,故事情节具有了双重意味。正如陈思和所说,“在这个世界的背后,隐藏了另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它似乎不出现于文学表象之中,需要读者的体验与领悟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小鲍庄的“仁义”故事耐人寻味,其中的人物形象成为展现故事丰富性的必要途径。“在文字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世界,它包含了作家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严肃思考。”王安忆通过对小鲍庄“仁义”故事的书写,实现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
从文本的表层叙事看,《小鲍庄》在讲述一个“仁义”之村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下了七天七夜的雨,致使山洪暴发,小鲍庄的祖上是做官的,因治水不力被黜了官,因此带着赎罪的心情来到水坝最低处安家落户,这是小鲍庄的第一个“仁义”故事。小鲍庄的“仁义”一直传到现世,村里人把“仁义”作为行为准则,成为远近有名的“仁义”之村。老绝户鲍五爷、流浪女小翠、鲍秉德的疯妻都是小鲍庄“仁义”关照的对象,但随着作家笔锋一转,我们发现大水来临之际,说好照顾鲍五爷的村民都没有想起来他不能动,更没法逃走;鲍彦山家收留小翠是为了给大儿子建设子作童养媳;鲍秉德不忍心和疯妻离婚的背后是毒打这样的事实。这些让读者不由得发问,小鲍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义”之村吗?这种对小鲍庄人集体无意识的群体“仁义”行为的描写,实则是一种文化上的反思。作家本人在《王安忆说》中谈到小鲍庄“仁义堕落”的文化主题,对仁义村种种不仁义行为的描述,恰好反映了她对“仁义堕落”主题的深化。表面看来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成分“仁义”的书写,但通过作者的反观,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显而易见。王安忆曾说:“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
撈渣是作者在小鲍庄表层叙事中安排的一个对传统文化深层挖掘的对象,是一个形象化了的符号。从出生开始,他就颇具仁义品质,还未开口说话便陪伴鲍五爷,从不嫌弃鲍五爷对他的不满和怨恨。他性格谦和,为人仁义,长大后更是从精神到物质层面对鲍五爷关怀备至。最后,他为救鲍五爷牺牲,世人感念他的英勇仁义行为,将他评为少年英雄、为他立碑。他的行为举止的确是仁义的代表,作者却偏偏把故事内容加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人之初,性本善”,捞渣的仁义形象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审美载体,被赋予了传达作者对传统文化观念反思的使命,极具渗透力和感染力。捞渣的仁义形象不仅蕴含着小鲍庄仁义的文化密码,而且蕴含着作家对文化反思的情感密码,是一种独特的文本话语表达方式。如果要给捞渣短短的一生冠以什么名号的话,大抵只有“仁义”二字。作为故事的主要人物,作者并没有从多角度去塑造他,致使他只以扁形人物出现,他只是一个“仁义”的符号。
为了进一步凸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另一个人物形象——“文疯子”鲍仁文。在整个小鲍庄,只有他与“仁义”之村的氛围格格不入,被小鲍庄人视为不仁义的代表。他田里长了荒草也不顾,读了几天书天天要写文章,为了写文章整天缠着转业军人鲍彦荣采访,到处投稿却一无所获,被村里人视为“异类”。捞渣牺牲后,他借此机会将这个仁义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捞渣的仁义故事竟然被这个村里认为和“仁义”距离最远的鲍仁文所成就,真是一种讽刺,更加深了对文化反思的力度。
四、“外来者”形象的意义
“外来者”的形象书写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叙事模式之一。在许多“反思文学”作品中,“外来者”或“归来者”的形象不但有利于承载作者反思过去、憧憬未来的诉求,更有利于借“外来者”的世界来反观现有世界的各种观念和行为,从而达到反思的目的。在鲁迅著名的“铁屋子”寓言中,“外来者”又被赋予启蒙的意义。当“外来者”进入铁屋子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从外部打破这个封闭稳定的文化空间,从而起到警醒的作用。
作者除了对小鲍庄土生土长的人进行书写外,还安插了“外来者”的形象。他们代表着小鲍庄“仁义”系统以外的象征意义,体现着两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对立,更是两种文化体系的碰撞。这些外来人代表了小鲍庄群体意识的另类,作者以他们在“仁义”村的经历来反观小鲍庄的虚假“仁义”,从而实现对群体意识的反思。
陈思和提出人物形象是“受社会环境的多种制约的”,认为王安忆的写作倾向将“背景淡化”并“有意把读者的眼光集中在人自身之上”。对此,王安忆回应说:“我的经历、个性、素质,决定了写外部社会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题,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她对小鲍庄“仁义”文化系统的来历进行详细的叙述,渲染作为小说外部社会的“小鲍庄”的特征。同时,她又刻意而不露痕迹地写了几个小鲍庄外来人的故事,在外来人身上展开“外来者”与小鲍庄固有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差异,向读者展现小鲍庄秩序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作家在小说中设置一些来自他乡的“外来者”形象,借助他们的故事揭示小鲍庄“仁义”的虚伪性,直接或间接地达到作者对传统文化反思的目的。
第一个“外来者”是拾来。拾来出身不明,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他来自鲍山附近的小冯庄,但事实上他是大姑从别处捡来的。他和大姑的关系有一定的暧昧性,对于他俩的关系,小冯庄人感觉蹊跷,处处试探未得结果。拾来十八岁那年,置了一副货郎挑子自食其力,在小鲍庄认识了四十多岁的寡妇二婶。他从对大姑的“恋母情节”转移出来,爱上了二婶。但小鲍庄不能容忍外姓人,村民殴打拾来,二婶也受大家歧视。虽然两人结了婚,可小鲍庄人仍不接纳他们,二人在人前始终抬不起头来。这种对待拾来的态度和行为显然和小鲍庄的仁义道德符码不一致。直到在洪水来临时,拾来下水捞出捞渣的尸体,受到大家的尊重,他才在小鲍庄立住脚。捞渣仁义的故事不但成为“文疯子”被小鲍庄话语系统接受的关键,而且成为拾来被小鲍庄话语系统接受的关键。后来拾来又成为捞渣仁义故事的诉说者,他似乎还在小鲍庄整体之外徘徊而无法进入,只能凭借诉说和拥有小鲍庄的故事而存在。
第二个“外来者”是要饭的小丫头小翠。她聪明伶俐,从小被鲍彦山家收养。鲍家收留小翠似乎是“仁义”之举,但在“仁义”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功利目的,是为了把她作为建设子的童养媳。鲍家在看到小翠并不愿意做童养媳时,就开始使唤她。但在小鲍庄村民眼里,“比起别庄上的童养媳,小翠可说是享福了,不挨打,给吃饱。小鲍庄的童养媳是最好做的了,方圆几百里都知晓,这庄的人最仁义”,这显然是小鲍庄文化伦理的固定思维。后来小翠在情窦初开之际抗拒圆房而逃离鲍家,这是对小鲍庄文化秩序的一种挑战和反叛。
第三个“外来者”是鲍秉德的疯女人。她做姑娘时如花似玉,是十里铺的一枝花,但嫁到小鲍庄之后,多次生下死胎,最终成了一个疯子。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被社会扭曲的“疯子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文本中意指不同,但对社会扭曲性的表达是一定的。“疯子的产生就是对社会的否定,疯子的反常行为、思想、言论就是个人在对强大社会的对抗,这种对抗最终以个人被社会所吞噬所放逐而结束,但往往这种反叛或对抗却是一种人性的回归”。鲍秉德的疯女人就是在小鲍庄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她接连生下死胎,被村里人说三道四,体现了小鲍庄人“仁义”的虚假性和病态性。而丈夫鲍秉德,由当初被人劝离婚时的一口回绝,到后来因为“文疯子”的广播稿而无法离婚时的“恨”,说明他和小鲍庄的话语系统完全一致。疯女人是对小鲍庄“仁义”道德系统的讽刺和否定,她的最终死亡反衬着小鲍庄话语系统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最初创作动机的驱使下,作者通过“外来者”形象的塑造,逐步挖掘,揭开一幅小鲍庄“仁义”符码背后的另一画面。在小鲍庄“仁义者”群体性话语的背后,是一群被抗拒的特殊社会群落。小说通过这种视角的描绘,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以此凸显其丰富深刻的话语叙事系统。
五、结语
每个时代,文学经典价值的发现与阐释都要经过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媒介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文学作品放弃旧观念,走向文学经典的核心位置。事实上,许多作品在文學史中的定位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文学媒介的影响下,批评家会随着文学主流思潮的变动,有意识地提取作品与文学主流批评相契合的特征,以其敏锐的批评意识悄然改变文本最初的写作体验。作者在这种批评话语主导下,也会逐步改变原有的观念和认同,合力把作品推向某一文学思潮的框架内,文本书写和批评的重心也会随之转移。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学批评如果囿于某一观念框架或已有文学史的定位,而无法摆脱批评历史和知识的束缚,文本的丰富性就会大打折扣,原本鲜活的问题也会变得抽象和狭窄。
注释
①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0、322页。③④⑤⑥⑦⑧李洁非、张陵:《“小鲍庄”与我们的“理论”》,《文学自由谈》1985年第1期。⑨⑩洁泯:《〈小鲍庄〉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畅广元:《〈小鲍庄〉心理谈》,《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陈思和:《双重迭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李劼:《是临摹,也是开拓——〈你别无选择〉和〈小鲍庄〉之我见》,《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一评:《面对新的文学现象——《〈小说评论〉、〈延河〉召开部分小说讨论会记略》,《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王安忆:《归去来兮》,《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王安忆、陈村:《关于〈小鲍庄〉的对话》,《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程光炜:《批评的力量——从两篇评论、一场对话看批评家与王安忆〈小鲍庄〉的关系》,《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小鲍庄〉·文学虚构·都市风格——青年作家王安忆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对话》,《语文导报》1987年第4期。邓婕、毕文君:《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看文学史如何定义〈小鲍庄〉与“文化寻根”》,《红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郭银星:《〈棋王〉和〈小鲍庄〉》,《文艺评论》1986年第4期。陈思和:《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谈〈小鲍庄〉》,《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1页。王安忆:《我写小鲍庄》,《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陈思和、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范虹:《新时期中国电影里的“疯子形象”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责任编辑: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