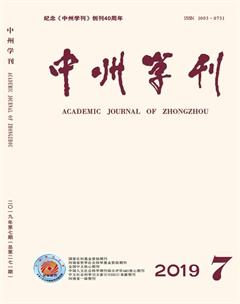民法典如何对待物权法的结构原则
一、物权法的四项结构原则
依据学界通说,物权法存在四项结构原则:与物权的类型有关,存在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的客体有关,存在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与物权的变动有关,存在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与物权的效力有关,存在物权效力优先原则。无论是2007年3月16日审议通过、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其中对物权客体与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物权效力与物权效力优先原则并未以具体法律条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物权客体与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为什么没有以具体条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对此,目前未见学界有更多的讨论。但对于物权效力与物权效力优先原则不以具体条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曾展开过讨论。2006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曾用半天的时间组织专题研讨会,讨论要不要在物权法第一章就物权效力优先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据笔者了解,当时尽管存在激烈的争论,但立法机关采纳的意见是不支持在物权法第一章规定物权效力优先原则。对此,比较有力的理由是:物权效力优先原则与通常意义上的法律原则是不一样的,物权效力优先原则只是对物权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的物权与物权之间、物权与债权之间关系所涉及的调整规则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该原则本身没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取向,因而不能成为裁判者处理纠纷的裁断依据。在法律就特定纠纷未设明文规定的时候,裁判者不能依据物权效力优先原则创制对相关纠纷进行处理的具体裁判规则,也无法就现行法上特定法律条文的复数解释结论,依据物权效力优先原则进行筛选。因此,《物权法》也就没有规定物权效力优先原则。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物权法》《民法总则》《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中,有两项物权法的结构原则被保留了下来。这两项原则即: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物权法定原则。民法典该如何对待这两项原则?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二、民法典如何对待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体现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第4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从内容上看,该条基本上是重申了《物权法》第6条的规定。
事实上,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主要是就民法典物权编的总则部分、所有权部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部分中调整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法律规则而作出的理论抽象和概括。也就是说,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主要是把这些散见于民法典物权编各部分、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法律规则给出了一个理论上统一的名称,即称其为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必须认识到,在遇到实定法上未设明文规定的情形,或者遇到实定法上相关法律条文出现复数解释结论的情形,《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第4条所确认的物权变动公示原则并不能发挥补充民事法律依据或者对复数的法律解释结论进行筛选的功能。而且,《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第4条围绕物权变动公示原则而设置的规则,即使作为对分散在民法典物权编之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部分的相关规则根据其家族相似性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这样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不够周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仍有必要在民法典物权编中保留物权变动公示原则这一物权法的结构原则,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更何况,与物权变动有关的结构原则是公示公信原则,目前只见公示、不見公信,似乎也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理想的安排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应当作为对纯粹民法学问题的讨论结论,停留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步入民法典物权编中。
三、民法典如何对待物权法定原则
尽管《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未对物权法定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但由于《民法总则》第116条把现行《物权法》第5条有关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予以重申,而《民法总则》是要作为民法典总则部分进入民法典的,所以民法典事实上还是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那么,物权法定原则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立法者对此应当秉持何种立场和态度?这是民法典物权编编纂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这就对当事人围绕物权客体进行利益安排的自由起到了限制作用。
若要对《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中的法律规则作一个梳理,自然可以按照目前的篇章结构进行,将之分为“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这是一种常见的立法技术方案。当然,也可以对《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所确认的法律规则通过其他方法进行规则的梳理。
例如,根据物权的客体是否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相应的记载,可以把物权的客体分为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和不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并以此为据,安排物权编的法律规则。这也是一种可行的立法技术方案。不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典型的像一支铅笔这样的普通的动产;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首先是不动产,另外还有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价值相对较高的动产,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财产性权利如基金份额、股权、知识产权等。对于不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大多数情形下都要通过交付或者占有进行权利的公示,将权利人对权利的客体享有何种类型的物权公之于众。但在实际操作中,就占有或者交付而言,在普通的动产上要想真正公示权利人享有何种权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对于一个人佩戴的手表,虽然看起来其采取了占有的公示方法,但其实并没有办法公示此人对手表究竟享有何种具体类型的权利。因为对手表的占有,可以是通过租赁、借用或者承揽等方式获得,亦有可能是对手表享有所有权或动产质权等方式而获得。在此意义上,对于不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而言,所谓物权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所起的对交易自由和利益安排的限制作用是有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只能通过占有或者交付予以公示,而占有或者交付的公示方法,其公示功能本身就是有限的。
事实上,物权法定原则着重限制的是当事人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进行利益安排的自由。对于此类财产,物权法定原则所产生的限制作用主要体现为:当事人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所作的某些利益关系的安排,可以申请登记机构为其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从而在物权法定原则之下,登记机构可以根据该原则,同意当事人的某些申请而拒绝某些申请。简言之,物权法定原则对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登记的财产起到的限制作用,主要表现为登记机构有权据此拒绝为当事人办理某些登记手续。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登记的标准问题,即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财产所作的利益安排,登记机构应当依照何种标准,决定为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或者拒绝申请人的登记申请。对于《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所确认的物权类型,如果其客体是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登记机构当然应当为申请人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但如果当事人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以及其他法律之外,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作出了一些利益安排,同时这些利益安排既无害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又无害于交往主体之外的特定第三人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则登记机构拒绝为其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的合理性與正当性就值得怀疑。这就构成了对民事主体交往自由的法律限制。但此时存在什么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限制民事主体的交往自由?当前,学界在证成对民事主体交往自由的限制的正当性上,在说理的充分性上,依然存在不少有待补充和完善的空间。
例如,当前各地兴建的不少工业园区里已经形成某种优势产业,同时围绕该优势产业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产业链,存在比较完整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之间的产业链条。很多企业在同一个工业园区中各自生产、相互配合,使产业优势得以扩大。那么,围绕当地的这一优势产业并为了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地方政府在出让工业园区内某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时候,能否对特定建设用地的出让作出限制,要求该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所进行的房屋建造和利用只能服务于该产业链中某一环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此种限制是否合理?如果当地政府作出的此类限制既不违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不损害公共利益和特定第三人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则能不能将此类限制物权化,即允许登记机构登记此类限制?如果地方政府只能提出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者订立一个合同,那就明显不足以充分实现和保障地方政府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目的。因为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可以继续对外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地方政府对这块土地所作的此种特定用途的合同限制,就无法对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后手的受让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由此将导致地方政府保持产业优势、维持产业链完整的发展规划落空。但是,如果此种限制能够成为得以在登记簿上进行记载的事项,其就具有可以向任何其他主体主张这种限制的法律效力。
同样,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如果民事主体就特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享有和使用作出了特定用途的限制,此种限制若能够进行登记,则对于实现物权人的意图而言,具有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原因就在于,民事主体围绕能够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所作的这些利益安排若不具有登记的能力,登记机构就不会为其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这一限制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值得商榷的。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物权法领域相当多的概念和知识是继受的产物。但我们所继受的知识不应当成为知识封闭的高墙,进而限制我们的法律想象力和进行规则设计的可能性。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最大不同,就是总会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充分的想象。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人类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一个不断展现想象力并不断把想象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法治的进步同样需要法律人展现自己的想象力,尤其是我国当前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行民法典编纂工作,必然面临许多无法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现成的法律文本中找到可供参考的答案、可供借鉴的经验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这就需要我们既关注必要的规则继受,更致力于必要的规则创新。
就对民事主体交往自由实施法律限制的正当性基础而言,物权法定原则这一严格的限定,其正当性基础值得探寻。物权法定原则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关于地役权的规则设计中有所缓和,正如苏永钦教授多次提到的,地役权有可能对物权法定造成松动。因为地役权的设立是通过合同完成的,而合同究竟可以约定什么类型的地役权,属于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范畴。然而,这也仅限于对相邻不动产设定地役权的情形。权利人自己的不动产虽然是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但地役权所提供的对物权法定原则的松动对此是无法适用的。
有鉴于此,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是否可以设置一项规则,即法律虽然不能放任当事人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随意设置权利进而要求登记机构办理登记(因为有时当事人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所作的利益安排违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第三人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但可以考虑设置一个法院确认程序,要求当事人创设现行法上没有认可的物权类型并要求登记机构办理登记手续时,应当以在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作为前置条件,然后法院审查当事人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所作的利益安排是否违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损害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第三人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并作出裁判,当事人再以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为依据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登记手续。这一规则可为民事主体围绕适合在登记簿上记载的财产设置符合其需求的权利并使这些权利具有对世效力,提供可能的渠道和途径。
以上意见,供立法机关参考,供学界师友批评。
作者简介:王轶,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