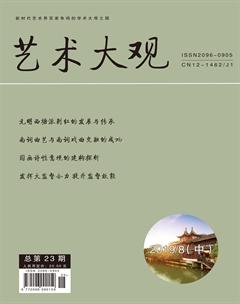用小说叙述历史的可能
桑姝凡
摘要: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长篇小说《汴京残梦》以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为主要线索,借主人公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爱情悲剧传奇再现了靖康之难的大历史,呈现出历史、艺术介入小说创作后的重大创新。历史介入小说是黄仁宇的专业使然,黄仁宇启用《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关于历史脉络梳理的抽丝剥茧法介入小说叙事,历史写作的专业性与小说的虚构性得以同步呈现。在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爱情悲剧中,黄仁宇在借鉴《桃花扇》关于“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辩证叙述外,更注重抒发具备“人的自觉”与人性发展的启示。从文化史角度看,《汴京残梦》触及北宋社会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脉搏,文学、文化与生活全面艺术化是北宋的时代风潮,《清明上河图》就是生活艺术化的典范。《汴京残梦》以历史介入小说叙事而不轻易放过对人性的深刻批判,达到了再现时代与人性批判的高度平衡。
关键词:《汴京残梦》;历史叙事;《清明上河图》;爱情悲剧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
相国寺内品图博鱼
金明池畔填词吟诗
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这是北宋汴京城繁华物语的缩略与写照,只是靖康之难让这一切瞬间化为灰烬,繁华倏忽间灰飞烟灭总引起后来者的凭吊与哀痛。近世以来以宋明为代表的汉文化与文明的折戟沉沙作为痛点引起诸多文人的反思与凭吊,近数十年来流行的论调“宋亡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华”就强化了宋明灭亡给予后世文人的灾痛感。在这个意义上,黄仁宇的《汴京残梦》以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的过程作为切入北宋末年社会的一把钥匙,叙写了由杭城入汴京的三位年轻士子徐承茵、李功敏、陆澹园在北宋末年汴梁城的载沉载浮,夹以对自北宋中叶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制度文化、繁荣的经济与娱乐消费文化、外交与军事对策等方面的专论,涉笔北宋末年的童蔡弄权、徽宗禅位、农民起义、汴梁保卫战、靖康之难等大事与活字印刷、宫廷文化、汴梁消费、妓馆娱乐、造船运输等时代创造及文人风尚。其中尤以徐承茵与天子帝姬邂逅而言情说爱之传奇为主线,生动地还原了北宋末年的绝代风华及由重大社会危机、少数民族辽金入侵而引发的汴梁城由繁华至残缺入梦的动态过程。《汴京残梦》的创造在于黄仁宇以历史学家身份基于史实发挥小说的寓言与虚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般历史书写之简略与冰冷之不足,以真正带情感温度的历史叙事创新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
一、历史深处的肌理
黄仁宇作为历史学家而选择历史题材以小说创作,非凡的专业素养较一般小说家尤凸显过人处。《汴京残梦》最富创造当在于其绵密细致又深入历史肌理的叙事与黄氏以其“大历史观”溯源北宋末年的种种社会历史事件并对之做出基于人性、合乎历史、兼顾道德良知的判断,尤其黄氏对北宋末年世俗生活与社会危机的抽丝剥茧而丝缕梳理之功就已炉火纯青。一方面,黄仁宇以《清明上河图》的绘制过程与所摹写对象为中心,全面再现了北宋末年皇都汴京的日常生活情状:“从晨雾在树,乡人进城,茶馆开门,垛房告别,樯桅折叠,虹桥惊扰,脚店输钱,太平车辆,河畔观鱼,驼队出城,门前说书,骑绅护眷,迄至僧道论衡。”[1]这些被呈现于《清明上河图》中的世俗生活内容被后来大部分艺术批评家认定为北宋社会繁华的证据,黄仁宇概莫能外。小说反复交代《清明上河图》的绘制动机在于宋徽宗圣裁的“叙盛世民情”“为当今天子与冢宰粉饰太平”。其实《清》图盛世繁华再现论并非向壁虚构,《汴京残梦》如是言:“天子朝献景灵宫,飨太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师太尉以下一律进爵加官,连东京士庶闲杂人等也全部喜气洋溢。因为大宋版图延展,户口钱粮增多,新政敷功,不仅‘丰享豫大的办法要加紧继续进行,而且见存人户尚可得到停刑减税的好处。”从《汴京残梦》对《清明上河图》的绘制过程所做出的技术性和物理性分析及想象中亦清晰地呈现出黄仁宇对《清》的“叙盛世民情”价值高度认同。另一方面,张择端承宋徽宗之命以危机重重中的北宋末年的回光返照为底本绘制《清明上河图》,至于北宋社会的整体危机与北宋末年的创痛实录则由黄仁宇以其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来补足。这构成了《汴京残梦》的叙述重心与特色。
黄仁宇以历史学家的专业素养在《汴京残梦》中对北宋末年社会危机的观察全面深刻,而《万历十五年》关于历史脉络梳理的抽丝剥茧法介入小说叙事往往给读者以惊奇。黄仁宇曾谈到作为历史研究规范的无法揣测之遗憾:“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猜度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2]这一“正面观察之不足”当在于历史研究必须倚重典籍文献等各种史料所录之史实,但据以新历史主义理论,历史研究本身并不能完全溯源实情实境,尤其大量现场细节无法还原导致历史书写必然走向叙事化且极有可能变成虚构艺术。黄仁宇的小说创作明显以历史叙事化为突破口克服历史研究“无法揣测之遗憾”,进而以历史小说的想象与虚构代替刻板拘谨的历史研究,使其历史小说《汴京残梦》能以微观观察法克服对一个时代和一个王朝的“正面观察之不足”之弊端。如《汴京残梦》谈及当时的宫廷风气:“当今天子虽不过四十多岁,却已御宇二十五年,他实在已倦于国政。他之自命为道君,筑青城,称无为而治,都有此类趋向。”北宋宫廷多出艺术精品,数位皇帝沉湎于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世界里自娱自乐且多有创获,在这类沉溺于艺术创造和道家之清静无为境界的熏染中,身为皇帝他们进一步将道家的无为推衍为一般的不作为:“童贯在外已不领制而独自草诏。梁师成尚且令手下数员书吏专仿圣上的笔记,他们所作‘御批,虽朝中人莫辨真伪。只是各事假手于人,当中细节也只好由他们做主。”“今日由南调北的兵马已不入东京,只从距京十里处上陆转道北去。一说南兵不守纪律,买物不给时价,恐怕进得城来有碍观瞻;一说太尉童贯虚报兵马人数,不愿在都城人士之前露出实况。”结合黄仁宇的观察与宋亡实际,宋之亡说先应归咎于顶端制度设计,然后恶性循环延及军队。及至靖康元年的汴京保卫战尤其触目惊心,北宋在战与和之间一直摇摆不定,京城保卫战的中流砥柱李纲则被贬官流放,占上风的主和派则一再妥协进而投降,甚而频频闹出历史笑话:“太宰李邦彦仍对金人和使说及,南朝主站的只有姚平仲和李纲两人,姚已在逃,朝中也即将罢斥李,以谢金人。并且大宋兵马奉旨不得在金人撤退时追击。”如此迂腐而贻误战机,若有一丝胜利真属天理难容。此既是大笑话也是屈辱史,更是投降史,北宋亡可谓自作自受。小说借由李纲之口道出:“我们一个主将,要受几十个文臣监督指摘,他们的一个行军元帅就是一个小皇帝,这样子我们又如何敌得过他们!试问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功业又如何施仁义!”黄仁宇将宋亡之因由一般军事失利很负责任地循迹至北宋开国以来以文抑武之制度,并对这一制度的恶果给予了直观恰切的分析。这一制度设计命定了宋亡之必然性。小说对李纲及其汴京保卫战事迹的细节叙述,补足了长期以来关于李纲及其英雄事迹在一般普及读物中的匮乏。至于汴京城破前后的细节梳理,则以触目惊心论而不为过,处处是主和派的投降以及城破后金兵如玩弄滑落至手掌里的小鸟般最终一网打尽北宋末二帝及所有皇室成员连同宫廷艺人、内外名臣、出色妓女及宫廷法器图文等一应掳掠北上。诸如此类细节钩沉梳理多不胜数。细节的力量是惊人的,历史资料只有冰冷刻板简化的记载。《汴京残梦》作为历史小说,对北宋亡国过程的叙事首先基于大量史实进而启用小说之想象与虚构功能以生动还原,历史细节与想象虚构同指北宋灭亡遭遇文化和人性上的重创。“残梦”抒写就此获得了普遍意义。
宋亡八百多年后黄仁宇通过《汴京残梦》追寻旧梦,然旧梦已不可为。只是这样一个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在瞬间灰飞烟灭,寻梦其实早已开始:“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园,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3]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在北宋亡后二十年间成书,即以无比艳羡哀痛的寻梦之笔对繁华的汴京城的陨落发出追悔之声,成为那个时代汉文人无比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各种哀婉忧思频频流布于字里行间。相形之下,《汴京残梦》没有停留在想象古都风物人情和盛世荣耀,究竟多了一层内蕴。拥有如此繁华之都的北宋王朝的遽尔坍塌,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黄仁宇在历经细致绵密的梳理与推断之后,他讲述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罪与罚”故事。《清明上河图》作为北宋社会的缩影,在盛世荣耀繁华无比的背后是大宋从躯体上已罹患重疾的严峻实际。这一切都来自北宋自开国以来的制度设计而形成的历次改革运动的好大喜功及北宋政府欠缺务实理念所致。黄仁宇以历史学家身份在极其冷静又充满智慧的叙述中,让《汴京残梦》穿越近千年替北宋王朝弹奏出一曲挽歌与悲歌。
至于《清明上河图》是否仅仅呈现了北宋末年汴京的繁华,这又牵连出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余辉的著作《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结合有关北宋中晚期社会、经济、军事、商贸、消费、娱乐等文献史料,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画卷细析之后,确认了《清明上河图》全面囊括北宋后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诸如“惊马闯市、船桥险情、文武争道、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商贾囤粮、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贫富差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4]黄仁宇则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汴京残梦》对北宋社会危机的分析并未呈现于《清明上河图》的相关分析上,实则未察觉到该画本身所内隐的社会危机。此或可言其为术业有专攻,毕竟不能强求一位历史学家化身为一名解画高手。
二、“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清初著名戏剧家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与黄仁宇的小说《汴京残梦》有不少相似处。首先,从叙写对象来说,北宋与南明王朝多有相似。尽管从“陈桥兵变”至“靖康之难”北宋已历166年,而南明王朝仅存在一年时间,但两个王朝的灭亡过程出奇的相似。同样面对少数民族入侵时迅速溃败;同样都发生权奸误国之灾,北宋宣和之际名臣童贯、蔡京之流已留万年恶名,马士英、阮大铖等权奸亦不逊色。他们治世无能、作奸弄权、打压排斥主战派将领,如主战派将领李纲被罢官、扬州刺史史可法孤军力战而亡。即以军事而言,北宋与南明于灭亡之际,都保存着相当的军事实力,北宋汴京保卫战参战人数就比金兵多,南明只左良玉一部即有70万之众。历史地看,南明朝的腐败速度令人瞠目,相比北宋,更丧失巴蜀一带作为粮仓与兵源的保障;尤令两位作者感慨由之在于两个王朝都有着富丽无比且寄寓着汉文人情怀与梦想的繁华古都。其次,从作家的创作心态来看,戏剧《桃花扇》和小说《汴京残梦》的“兴亡”叙事均建立在对汉文化与文明遭遇重大创痛与封建王朝已显重大危机的考察上。孔尚任在《桃花扇》一剧中反复铺陈南明时期金陵城的文人交游、复社风雅、秦淮风月、女性风华等晚明风月情怀,这些美丽风雅连同金陵这座繁华的巨大都城包括已然发育精致的汉文化与汉文明都在这场王朝更替中灰飞烟灭了。作为孔子的六十四代世孙,孔尚任的文化选择从应和清廷积极入仕转向了迷恋以与明遗民话桑麻为标识的汉文化与人文精神。所以,《桃花扇》对南明王朝一系列自作孽以实录,推演出灭亡的必然性,而孔尚任以孔子后代身份与明遗民的密切又持久的交往强化了他的汉文化与文明代言人的立场,以此为起点对整个汉文化与汉文明发出深刻忏悔之声。黄仁宇的《汴京残梦》则直接将《清明上河图》所考录的北宋末年汴京空前繁华置于北宋末期积聚日久的巨大社会危机中以全面考察,繁华历历在目而巨大的社会危机则触目惊心,北宋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危机重重中演化出畸形的丰润风雅。汴京繁华的陷落留给了本已多罹中国现代以来战祸离乱之苦的黄仁宇以无法了却的“残梦”,美丽风雅灰飞烟灭后的忏悔与追悔基调力透纸背。这些叙事都无一例外地借力于爱情悲剧等美的丧失。可以说,《桃花扇》与《汴京残梦》艺术构思与探索明显趋同:“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不仅是《桃花扇》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与主题,同为《汴京残梦》在“残梦”意识主导下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与核心主题。与《桃花扇》对侯方域、李香君为代表的宋元以来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写法不同,《汴京残梦》关于封建时代沉于下僚的落魄读书人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爱情故事则近乎旷世传奇。黄仁宇无疑以近乎完美的道德人格力量强化并刷新了因“离合之情”而引起的“兴亡之感”。这要从小说对徐承茵的形象塑造说起。徐承茵由杭城入汴京只为改变已不可遏抑的走向颓败的家族运势,适逢宋末取士标准由诗词歌赋变为书画医数,意外入画局参与绘制《清明上河图》,徐承茵尽心竭力只为“使自己的前途事业也有一番着落”“有益于日后升迁……替自己打开出路”,在与“正途”阴差阳错的时运不济中,他跟随张择端作为主要参与人协助绘制《清明上河图》,上述诸种突围努力仍不外乎功名利禄:“如此看来仍只有希望《清明上河图》及早成功,皇上嘉纳,则不怕再不加薪晋级了。”徐承茵全盘心思于种种上位之法以成全一己之功名利禄。意外的是,在《清明上河图》的绘制过程中,因当朝皇帝以所宠溺的柔福帝姬作为画中人物的安排和本由皇帝钦定、张择端坚持的《清明上河图》之写实宗旨不符,徐承茵抓住机会以北宋时期流行的力谏获名之意图谋求觐见皇上以期引起重视而快速上位,小说对徐承茵以有限的见识来推敲自己的迎合术之叙写尤显生动:
他将衣冠再四检点,确信了无差错。至于行礼,则自杭州府保送应举之日本来就经过一段教习。最重要的是目不旁视,心中沉着,步履要有节奏。像戏臺上的稳重步伐即算“趋”。不到适中的地点不考虑慌忙下跪。以后的动作视情形而定。总而言之一举一动都要干脆利落。如果不潦草马虎遮盖掩饰,即算行做得没有全按程序,也仍算有分寸。否则纵是按部就班如仪,行走之中若夹带着任何扭捏,也仍可能被检举或受斥责。
这次觐见成为徐承茵人生的重大转折。本来复杂而紧蹙的迎合帝王术之准备变成一场美丽的邂逅,柔福帝姬由幕后轻跃至前台。黄仁宇笔下的赵柔福具备世间小女子的所有雅姿:“头上戴有毛褐以避风尘,面上则特别的红润”“柔福则脱下毛褐,只见头上一片乌云,无假髻长梳”“似乎比所说尤尚年轻,脸上一派烂漫不受拘束状态”“露出脸上酒窝”“她真是十六七岁的小娘子,也确是玲珑利落”“他知道她面庞横宽,颊上有酒窝,并非出奇的艳丽,只是光彩夺目,这时候风趣横生,更显得玲珑娇小”“面如凝脂,满体芬馥”“淘气的小妮子”“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明快利落的双眼”“令人心怀荡漾的颊上酒窝和柔嫩的小手”。及至徐承茵将其形象绘入画中:“笔下之帝姬,注视有神,唇吻微长,面颊浑圆,双手柔软。柔福虽不是国色天姿,只是一团利落明快,惹人注视引人爱慕的形象已跃然出现纸上。”以一般创作主体经验而言,黄仁宇如此不惜笔墨一意夸赞赵柔福之美,实则见出黄仁宇之钟爱青春女性美之心态与相应喜爱之甚。徐承茵与赵柔福一生三次相遇而如梦似幻,这种身份不对等的交往因柔情蜜意成就传奇。此番恋爱改变了徐承茵的人生轨迹,此前他一心谋求功名利禄为名利而活、为家族而活、为别人而活,此后他仍谋求建树重大功勋,而背后的动力与终极目的无疑在于以所获功勋作为迎娶皇家帝姬的资本,及至国破家亡之后,徐承茵置一己生死于不顾,一路冒雪北上河朔入金境寻觅赵柔福,至此徐承茵抛下了人生所有的功名利禄而为自己活着,是为小说倒叙手法目的在于凸显现代人生价值意义。倒叙在结构上无非为了引起新奇的叙事效果,而在传情映射层面尤其强化了徐承茵此番寻情经历的重大意义。徐承茵携一仆孤身而入金境已将一段美丽的邂逅演变成家国沦陷背景下个人对以爱情为代表的人生存在意义的追寻,进而以精致而合乎人性的悲剧叙事将一般意义上的“离合之情”推演至家国“兴亡之感”。而小说的“残梦”抒写特征则一再强调读者不要留恋于小说的“尾声”处所给予的一丝团圆可能。黄仁宇在“尾声”中给予徐承茵和赵柔福的爱情故事以及赵柔福个人命运以多种可能性,实现了对近代以来fiction代言小说之寓言和虚构艺术特征的应和。开放式的结局向来多被近现代小说家所喜爱,实质上预留了小说的抽象抒情功能与意义。而回到具体历史家国灾难与中国文人命运轨迹上,則后来者无论讲述的是现实中的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还是虚构艺术里的徐承茵,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此由个体“离合之情”的抒叙走向了后世文人对汉文化及汉文明代言的国家“兴亡之感”的天鹅绝唱与魂牵梦萦。
从人物形象的成长轨迹来看,由杭城入汴京之际的三位年轻士子陆澹园、李功敏、徐承茵各怀心思,在对比叙事中,徐承茵虽深怀封建时代读书人浓烈的求取功名心,但正直、仗义、忠厚和所彰显的一般人性良知及谨守普遍道义使其形象在一般求取功名的封建读书人之外逐渐变得圆润饱满起来,他对待感情由单纯、执着而至深情就与北宋时期一批沉于市井的文人如柳永之流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尤其迭经汴梁城破对爱情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徐承茵的形象就完成了由一介文弱书生到勇谋齐备的军中幕僚再到置生死度外的一位忠诚的爱情卫士的重大转变。徐承茵就此完全具备了欧洲中世纪骑士精神的“爱情、忠诚、冒险”特征,也合乎中国传统“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文学实践。徐承茵是一位成长型的读书人,他的性格丰富性要远超复社青年才俊侯方域的性格成长历程,而柔福帝姬出于皇室,较之于李香君虽少了淡定从容之江湖脂粉沧桑气,而多出了淘气、可爱与明秀之美,这点尤其难得。就此而言,孔尚任在《桃花扇》一剧中将侯、李之爱情悲剧符号化为“兴亡之感”的必由之路,黄仁宇则在《汴京残梦》中不仅顺延了《桃花扇》关于“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辩证叙述,进而通过在家国之难中演绎离合之情以生成极具现代价值与意义的“人的自觉”与人性的发展。此为优秀的现代小说家必然具备的现代意识。
三、艺术与文化背景的内在关联
李泽厚在其名著《美的历程》中提到了宋代在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文化上的发达程度:
宋代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室,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绘画艺术上,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追求是基本符合这个阶段在“太平盛世”中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的。但这不是从现实生活中而主要是从书面诗词中去寻求诗意,这是一种优雅而精细的趣味。[5]
就艺术论而言,李泽厚的判断自然出彩;而《汴京残梦》显然没有依循这一路径奢谈艺术之自足审美特质,而是以近似纪实的手法折射了北宋时期文化背景对文人命运及艺术发展的复杂影响:
将文学、文化与生活全面艺术化是北宋时期的时代风潮,以汴京城内各式风俗人情物理为原型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典范。《汴京残梦》揭示了《清明上河图》最艰难地行进在于如何平衡艺术与各个方面的是是非非。作为小说的主线之一,三任画学正绘制《清明上河图》涉及三个层面的以画论为代表的艺术与现实之关系思考,首任画学正刘凯堂强调“今日之所谓画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照着景物写生,探求人伦物理都从这些地方开始”。这一要求明确此幅描绘汴京繁华景象的画卷必然要遵循实录法绘制。若说局部特写尚有完成此类预想之可能,则全面呈现这一绘制主旨即使而今以人工画笔亦恐难完成,刘凯堂则将写实主义以教条法则毁之:“注重当中一笔一画之工细,最不为迁就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朦胧模糊”,明显忽视了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之特质。黄仁宇从读者接受层面指出了这类僵化方法的局限:“画之为画少不得供人赏玩,原来不离娱乐。像刘凯堂这样的遣派,真是为形影所奴役。即纵算画得逼真,也使画得人和看的人同样感到索然寡味了。”第二任画学正何叙先以一幅特别之肖像示人:“露出半秃的头顶,两眼眯眯地笑作一团,说时露出一嘴黄牙和右边牙床上的一个缺洞。”黄牙与缺洞大概由贪吃而损耗牙齿所致,又俗话说相由心生,其慵懒圆滑世故的面相已赫然在目,其所念大都是此类圆滑避世求自保之类的生存智慧:“道法自然”“不可强求”“虚心淡泊,静候机缘”“以静待动”“非曲非直,不柔不刚”“若要无为,必先无能”“富贵利禄强求无功,倒可因知音的见爱决于俄顷”。说白了就是近乎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及至于不作为与无所事事,其“浑然无是非曲直”而日日沉湎于自斟自酌之放浪形骸状,日后的命运亦可想而知了。及至张择端的出现才为《清明上河图》奠定了技巧与理论基础:“所选资料也只有混杂的代表性质,并不一定所画限于清明节那天的情事。”在随后的选择素材上,张择端带领两位画师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景物人情以成幅置画,且在具体绘制过程中,张择端以极具艺术功底的眼光选择了“三道屏风”法、视点移位法、山水画之点染法、文人画之写意法等技法以具体素材具体选择具体解决为标准,注重详略得当与主次分明,兼顾现实参照与艺术呈现。与其说,前两任画学正刘凯堂与何叙所顾虑与参考在于时代背景,而张择端之成功秘诀除了出色的技法而更在于对艺术之于人生的深刻认知:“这样看来,人世间之至理无从全部目睹,眼目之所及一般人以为实在,当中却还有虚浮的地方。此中蹊跷能不令人警惕。”此亦为《清》图作为杰作传世的最重要因素。当艺术具备了独立性进而成为人生体验的深刻写照之后,艺术杰作就会脱胎于其诞生的文化背景,不会随着时代之变化而罹受不测。
四、最是人心不可控
徐承茵的正面形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基于其与柔福帝姬的感情发展并为之付出巨大牺牲以完成,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则主要基于其与李功敏、陆澹园的心性行为比较和与前后三位画学正的交往行为中获得,三任画学正之性情差异及至陆澹园之恶与徐承茵之善助推小说叙述之参差手法的成熟。在人性恶的叙写中,关于陆澹园逛妓馆的场景尤其触目惊心。
陆澹园于方腊农民起义之際冒着巨大危险营救徐承茵父母及妹妹苏青之后,遂与徐承茵之妹苏青订婚,在彼时的汴京官场上,陆澹园一路顺利结交权贵而不断登龙上位,使得处于宦僚落魄之途的徐承茵长怀“多时希望姻弟来京可以扺掌做长夜谈”之念想,适逢陆澹园新近升官而志满气昂又逛妓馆风流成瘾之际邀约李功敏和徐承茵一行再赴妓馆行风流事。徐承茵则再遇当年入汴京城之际尚是青涩羞怯而今已为名妓之楼华月进而畅想人间大爱种种:
大凡男女间之事,最是要得专心。如果两方存着一片痴心,将人世间任何纵横曲直,全部置诸度外,也不分你我,则灵肉相通,身心如一,彼此同进入海上仙山的神妙境界。若是当中有任何阻隔,有如听到不悦耳的声音,闻及不愿入鼻的味觉,则此类事物立即将当事人打归尘世,此时一个人骑驾在另一人身躯之上,不仅猥亵,而且尴尬。
此番论断早已为现代精神分析学所证实,也实为一般人之常情。只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楼华月今日之身份只是一艳名远播的妓女而已,远非当年误入青楼羞涩不已的小女子,所以很快跌入人生得意的陆澹园怀中,空余痴情者徐承茵一人伤怀不已:
此时承茵不免在嫉妒之中掺杂着许多无名的情绪。再因着澹园更觉得对不起自家的小妹。他的妹夫尚未成亲即有这样的外欢,则他日徐苏青的空闺独守也可想象了。
此中一则因单纯的徐承茵对人性认识不足,以良善心性衬出陆澹园之失却一般人伦,大违古代文人士大夫一般心性,更脱轨于常人之心性,但此番情形在中国古典士大夫层并非个案。既如此则罢,更可甚在于楼华月之妹妹楼花枝的一句是非话彻底摧毁了徐承茵对楼华月以及人性仅存的一点幻想“她(引者按:指楼华月)一面忙着不停地嚷着说赎身从良;一面又见客张扬,到处卖俏,自抬身价。”徐承茵对自我人生定位不清,他以一般士大夫精神品格砥砺自己,但却简单地将自身全部感情寄托于一名繁华都市里的为稻梁谋的下层妓女身上,全然未顾及市井下众鄙俗的物事与人情之态,于是徐承茵“只望着床缘上的空心雕花栏杆发怔”。此处雕花为人工之物,又如梦幻之景,空心与花各有寓意,其真真假假、如真亦假、如梦似幻,一切都落入虚幻之中了。《汴京残梦》之“残梦”亦大抵如此了。
参考文献:
[1]黄仁宇.汴京残梦[M].三联书店,2018:172,90.
[2]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三联书店,2015:180.
[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9.
[4]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
[5]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新华出版社,2001: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