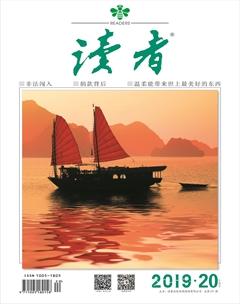见字如面
蒋曼

作家张大春写《见字如来》的初衷,是突然发现“当一代人说起一代人自己熟悉的语言,上一代人的寂寥和茫昧便真个是滋味,也不是滋味了”。
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熟悉的语言空间。
和女儿逛街,看到一款衣服,她说:“抹茶色挺好看。”我说:“那是薄荷色。”我妈说:“啥,就是军绿色嘛。”细一想,我们在对颜色的描述上,使用的都是属于自己时代的词语。它们之间素不相识,即使是指同一物,也判若水火。
张爱玲在《沉香屑》中描述山腰上的白房子:“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鸡油黄足够传神,油润和新鲜如在眼前。女儿看到这里却很迷惑,听了解释,反而说:“天,真是让人恶心的颜色。”她们这一代人是真正远离庖厨的君子,对她们来说,肉和蔬菜一样,是在超市的暖光灯下整齐地排列着,失去田野泥土的商品。
闺密在朋友圈晒自己的美食:羽衣甘蓝、胡萝卜欧芹、地中海盐、意大利醋配上漂亮的沙拉碗。她妈一细看,恍然大悟:“羽衣甘蓝,我以为是啥子稀奇玩意,就是我们老家种的包白菜!以前要吃整个冬天,连猪都吃得想吐的白菜。”同样的卷心菜,羽衣甘蓝的背后是精致的文艺青年给生活镶上的梦幻花边,包白菜背后却是足够土味的忆苦思甜。
我们成长在自己的世界,词语已经让我们形同陌路。吃包白菜的母亲和吃羽衣甘蓝的女儿隔着万水千山。也许有一天,陈词滥调会是个褒义词,至少它讓人们还拥有某种粘连在一起的情感,感同身受,不只是面面相觑。
代沟是必然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也表现在我们的语言里。就像大地上的岩石,即使同样坚硬,紧挨在一起,也分属于不同的地质年代。
一个老演员听到人们称他“骨灰级”时,勃然大怒。啼笑皆非的尴尬和误会可以化解,它所隐藏的隔膜却日渐深厚。所有的人都枕着他们自己的词语才能安眠。
四川和陕西交界处的某处高速路口,四川境内曾赫然写着“棋盘关”,颇有塞上风云、金戈铁甲的铿锵之音,历经千年仍缭绕在行路人的耳畔。陕西境内却写作“七盘关”,一眼望去,背后是《蜀道难》中重重叠叠的群山。同一座关口,两地展现的是不同的侧面。世界并无不同,只是人处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我们的词语也许会成为我们的关隘,然而关隘处总有通衢,那些文字和词语的背后有无数故事的讲述者。说文解字时,我们相遇在彼此的光阴中,即使铺陈转折,也最终不离不弃,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