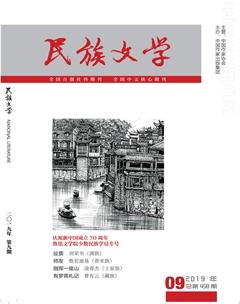草木五篇
刘惠春
一、梨树
我多想对人说一说梨树的孤单,多想让人知道,那些时间的深渊。
我和母亲说,在院子里种棵梨树吧,像邻居家一样,花开得好看,还能结果子吃。
母亲说,梨树不是好树呢。
我哂笑,妈,你可是蒙古人啊,也讲究这些呢。
母亲回头瞪了我一眼,盘古至今,哪里的人都不喜欢离别。
我只好爬上房顶,去看邻居家的树。
邻居家的房子低矮,站在稍微高的地方,院子就一目了然。何况我站在房顶上。
邻居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正在开花的梨树。周围的房屋、院落、人群都是灰突突的,只有那一树梨花,每一朵都那么白那么干净,明晃晃地耀着人的眼。梨树下的一张木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阳光倾泻而下,照在年轻女人的身上,那些光像是从她身上发出来的。
这光芒照到了我脸上,我被那光吸引住了,光里面的花瓣极为安静,像是一种罕见的事物,经过那个年轻女人,在风中盘旋了一阵,然后消失了。
我不知道,是那些消失的花瓣,還是那个光芒中的女子,让我感到了难过,一种真真切切却又说不清楚的难过。难道母亲说得对,梨树不是好树?
也许就是那时,那些光那些难过给了我某种多年以后才能明白的启示。
院子里看不见我,母亲就会大声喊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不情愿地从屋顶上下来。母亲说,不要总盼着花开,花开了,就会离开树,飞去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仰着头对母亲说,我又不是花,不会去很远的地方。
母亲忽然笑了,看着我说,真是傻丫头,哪只鸿雁不远飞呢。我听不懂母亲的话,我也看不懂她笑容里面的忧伤。
梨花落了,那个女人也离开了。
那间没人住的院落,成了一些挖小煤窑的人夜里落脚的地方。那些年轻的光棍汉们把院墙推开个口子,跨过来,向母亲讨要热水,也会来屋子里的炉子上热饭。那棵没有人管的梨树,像没有家的孩子一样,露出了恓惶的模样,叶子一片片落着,还没有到冬天,整棵树都变得光秃秃了。
人们说,这棵树怕是要活不过这个冬天呢。
春天的时候,母亲迈过院墙给梨树浇水,她像孩子一样盼望着梨树的叶子快快绿起来,只有这一点点单纯的心思,没有别的了,就是等待。
看到第一片叶子的时候,母亲小心地摸着那片叶子,娇嫩,新鲜,像一张年幼的脸,在母亲掌心里安静地笑。母亲有些恍惚了,她笑自己,这是两样事嘛,真是老糊涂了。可是,每一天,母亲都要来梨树下站那么一会儿。风吹过来,树的叶子开始摇晃,像无数的小手,拍着巴掌。母亲仿佛也跟着晃起来,母亲都对它们说过些什么呢,那些树叶一样繁密,一样纷落的话。风过去,所有的叶子就慢慢静下来。稀疏的光透过叶片落在母亲的身上,发上,那些头发,梨花一样白。
日落了。远处的荒原暗了下来,一层一层,薄薄的凉。太阳就那样下去了,母亲又在喊我了,没有人应。然后,母亲看看地下的梨花,静悄悄地回屋了。
秋天的风,一阵一阵地吹起来,梨树的叶子开始哗哗地往下掉,雨水一样,眼泪一样。母亲扫着那些叶子,不断有叶子落在她的身上,这个深深弯下去的身躯,那些落叶都要把她埋起来了。
几个果子挂在枝头,东一个,西一个,抬起手就能够到它们。果子沉甸甸地压着树枝,可是总也不落。阳光照着这些褐色的果子,它们瞬间就变成了温暖的暗红色,像是炉膛里燃着的煤球,真想伸出手去暖一暖啊。
刮风了,落雪了,母亲都要去看看梨树,用手摸一摸这几个果子,它们还结实地悬挂着,母亲就会安心,就说,冬天还要有一阵子才来呢。
那些梨花还在开着,那些果子也都在枝子上呢,可是我的母亲却不在这人世了。
这都是我离开家以后的事了。
黄昏一到,荒原上的灯一盏一盏亮了,暮色像秋天一样蔓延开来。不时地,远处会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很急促,没有深夜时的凄凉,却令人想到秋天陡起的风。母亲在灯前给我们讲她劳作的地方,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滩,晚上会有海的腥味。老早以前,那里是海。母亲很肯定地说。可是母亲一生都没有见过海。母亲是个热闹的人啊,喜欢人多,喜欢讲故事,喜欢说盘古至今,我一点都没有遗传她。母亲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话想要说出来,我一直以为还会有很多的时间,我可以和她安静地坐在梨花下,抱一抱她,和她说一句柔软的话。
我想起了和母亲在一起的其他许多的黄昏时光,它们如此温暖,如此飞逝如电,令人心碎。大风吹远的梨花,没有说完的话,人要经历多少,才能够明白一朵远远飞走的梨花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经,我多么烦恼母亲不停地喊我的名字啊,可是我不知道,有那么一天,母亲不在了,就再也不会有人这么叫我了。这一生,有谁喊我的名字像母亲一样多,一样焦急?
梨花飞舞的寂静盖住了所有的响动,远远地,有个声音穿透这死寂,呼唤着我的名字。
什么都不能成为离别的理由,梨树也不能。母亲。
二、沙葱
每一种植物,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它们的命运,有些是可以食用的,有些是用来观赏的。比如沙葱,在荒原上,它就是用来吃的。
见过的草木中,我第一个能叫出名字的就是沙葱,我是在饭桌上认识它的。小时候,沙葱天天都会出现在饭桌上,配合一切吃法,凉拌,热炒,做汤,当馅。即使和肉放在一起,它们的味道也从来不会被淹没,一张嘴,满是辛辣的山野气。
沙葱,在许多年里,都是天长地久一般的存在。
东晋文学家郭璞曾在《尔雅注》一书中盛赞“食之香明与常葱。”北宋史学家苏颂在注《尔雅》中云:“山葱也,味美可食。”《本草纲目》中说:“北边云台戍地,多野韭、沙葱,人皆采而食之。”可见,从古至今,沙葱的功用就是用来吃。它也能入药,助开胃、消食、杀虫、不思饮食等,还是和吃脱不了干系。
春天来的时候,荒原上静悄悄的,只有风的吼叫,所有的风都离开后,偶尔会有星星点点的雨飘落下来。这一点点的雨水足以让细细密密的沙葱一簇一簇长出来,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它们就长高了,就可以吃了。
弱小的沙葱在荒原里并不醒目,高不过半尺,叶片尖而细,总是躲在大蓬大蓬的沙蒿和梭梭下面,安安静静,一点也不招摇。如果遇到一块平坦的地方,沙葱会长成一大片。
荒原上,草野之气远远大于人气,而这稀少的人气就是由沙葱聚集起来的。孩子们欢呼着奔跑在荒原上,他们的欢呼声,异常响亮,像鸟群呼啦啦从天上飞过。年轻的女子们笑着,彼此戏谑着,她们手脚麻利,说着话,却一点也不耽误手里的活。沙葱娇嫩的身体不断发出清脆的断裂声,油绿的新鲜的汁液流淌下来,落进每一个张着大口的袋子中。
近处的沙葱没有了,就往远走,更远的地方。
沙葱花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先是看到落日,然后是一些飘移的云朵,然后,像是突然闯进来的,沙丘背后,出现了一大片盛开的沙葱花。
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这样荒凉的情境中,那些花全部盛开,毫无犹疑,浩浩荡荡,一片紫色的海。黃昏的余晖里,它们变成了透明的淡紫色火焰,全世界的光都聚集在它们身上。那是落日照在它们身上的光,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它们自己身体内部的光,一刻不停在向外散溢。
那是某种太过陌生的遭遇,因为无法预料,仿佛突然与一个巨大的无法形容的事物猝然打了一个照面。就像《聊斋》里,平白荒野遇见狐仙的书生,只能被定在那里,只能张口结舌。
它已不再是我天天拔来吃的沙葱,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事物,一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事物,我无法表达的事物。那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美,但我却突然懂得了一棵开花的沙葱,它就在那里,吸引着我,召唤着我,美就是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进入了我的精神结构,如此巨大,触目,光芒四射,把我引向了懵懂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它是一种唤醒,美本身。
此时此刻,只有那些明亮的光,紫色的火焰,此外什么都不存在了。
在我的人生里,这是一段不可度量的时间。那漫长的一刻,只有我一个人,在荒原浩大的黄昏里,面对着这一片沙葱花。风吹着它们,也吹着我,它们向我传递着我尚不能理解的讯息。我不是在看一朵花,我是进入了一朵花,我感觉着它们,这比看它们更深入我的内心,我的心被它们充满了。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推向了荒原的深处,另一个平行世界里。我成了另一个我,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个我。
黄昏是寂静的,花朵是寂静的,我也是寂静的。
后面赶来的女子们跺着脚,失望地大叫,这么好的沙葱,居然老了,不能吃了。
这些声音硬生生地把我拉回了现实。
这些花多好看啊。我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她们竟然没有被沙葱花打动。
好看有什么用?
她们说得对,好看有什么用呢,好看又不能吃。也许,在她们眼里,沙葱的存在就是用来让人吃,让人填饱肚皮的。它竟然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呈现出花朵的气质,这是不可原谅的。沙葱不应该是种美。
我在美面前,感到了悲伤。
但我也为这些花庆幸,它们要有着多么大的耐心,多艰难的努力,才躲开了众多的手,才安然绽开了这一片花。如果不是被人漏掉,它们根本无法还原它们本来的面目,植物的面目,花朵的面目。它们会像更多的沙葱,被拦腰斩断,被水煮锅炒,被不停吞咽。我相信,每一种草木都是想要开花的,它们和人一样,存有自己在世的时刻,它们回应生命的,不都应该是开花吗?那些没有开过花的沙葱,那些喂养了我们简单身体的沙葱,它们在夜里哭泣吗,没有人知道。
沙葱并不珍贵,只是荒原上最微小的事物,荒原上也没有什么可珍贵的,但美是珍贵的。荒原上有花开着,这个世界好像就变得珍贵了。
许多年里,我一直疑惑着恍惚着一个问题,美是本能,是我们对自然对生命的感觉,美只需要我们在场,却从来都对我们无所求啊。可是为什么,就有人觉得美是无用的呢?
三、酸溜溜
“酸溜溜”的植物学名是沙棘, 苏海图的大人、孩子们都叫它“酸溜溜”。这个名字,其实已经相当于描述了这种草木,形状、味道,呼之欲出。念着这个名字,那圆溜溜的样子就出现了,酸酸的口水顺着嘴角跑了出来。
我拒绝沙棘这个坚硬的没有表情的名字,它影响我对“酸溜溜”的回忆和叙述。但我又该如何叙述一棵“酸溜溜”呢,就像我该如何说清楚一个孩子一无所有的快乐呢?
短暂的夏天,孩子们每天都要奔向荒原,只为一头扎进某个地方,然后忘记一切。一整个夏天,“酸溜溜”都会在荒原上等着我们。
“酸溜溜”小小的果实最初是青色的,慢慢地,在阳光下由淡黄变得绯红、深紫,覆着一层薄薄的皮,晶莹剔透,看上去就像宝石一样。娇嫩的果实,轻轻一捏就碎掉了,红红的黏黏的汁液顺着手就流下来,那些汁液粘在手指上,会把手指染红。我们连咬一口尝尝都不必,看它的颜色,就能够判断它的甜蜜程度。那种甜,跟糖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种独特的味道,荒原的甜,童年的甜。
“酸溜溜”的刺很多,几乎通体都是刺,这也许就是它的学名有个“棘”字的原因吧。一定要非常有耐心,一颗接着一颗,从指尖顺着手指落入手掌。放进嘴里尚未咀嚼,果实已冲过舌头奔进喉咙,甜,还有酸,能够细细品味的时候,牙齿已经酸倒了。
男孩子可没有这么耐心,他们一着急,就从枝上啃着吃,总是会扎了嘴。很多时候还会把衣袖扎破,回家少不了要挨大人一顿骂。可是,最甜的“酸溜溜”都是他们找见的,一大枝一大枝地折下来,大家一齐嬉笑着,围坐在沙丘的阴凉下面,那些汁液饱满的快乐。
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和我们,一起在“酸溜溜”棵子里蹦跳。还有“沙和尚”,就是那种跑得飞快的沙生蜥蜴,手掌一般长短,身体是扁平的,背面的颜色和沙漠几乎一模一样,如果它不是紧贴着沙面嗖嗖向前跑,是根本看不到它的。它们疾速在沙丘上奔跑,从一棵驼驼刺到另一棵,捕捉着黑色的虫子。它们最喜欢在梭梭根底下钻洞,孩子们趴在梭梭下面,和“沙和尚”对峙,一个洞里,一个洞外,看谁先失去耐心。但手是不敢伸进去的,万一里面不是“沙和尚”,是一条蛇呢。
捉“沙和尚”并不是很有难度的事情,只要趁它不备,顺着长尾巴将它捉住,它就不能动了。所有的男孩子都以捉“沙和尚”为荣,女孩子是不屑也不敢的。“沙和尚”捉在手里软软的,小眼睛可怜地瞅着人,让人不忍心折磨它。荒原上的任何生命活着都是不容易的,孩子们抓到“沙和尚”玩耍一会儿,便放它逃生去了。
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要么抬头看天上倏然飞过的一只什么,或者看着地下一只慢慢爬行的虫子,找不到我能去做的事情,可这就是我的童年啊,我又能到哪里去呢?
更多的时候,我就找一棵枝叶浓密的“酸溜溜”,躲在下面看云。天空那么广大,白色的云朵一大团一大团地向远处飘过去了,那些云啊,一去不回,它们终于去了它们想去的地方。
玩闹够了,每个人都会去重新摘一些“酸溜溜”,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吃,他们太小了,还不能够跟着我们来荒原上玩耍。这时候就会非常有耐心,每一棵枝子上只挑最好最红的摘,慢慢地便走远了,和其他孩子分开了。
阳光白炽、炙灼,火烧一样,四周没有树影,云仿佛也怕热,飞快地走着。哪里都找不到一丝阴凉,手臂的皮肤在反光,辣辣的扎眼。每一座沙丘都像黄色的热浪,大得没有边际,荒原的空旷一下子将我彻底淹没了,全世界好像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偶尔出现的声音特别容易惊动我,一声鸟叫,一声虫鸣,我都会急急寻去。我伸长脖子四处张望,伙伴们都不知跑到了哪一个草丛后。草比我高,我知道他们在,但我看不见他们,便急忙跑到一个高高的沙丘上面去找他们。
四野里非常寂静,只有这些孤零零的小小的人儿在日影下以各自的方式慢慢移动着,每一个都晒得黝黑,每一个都抱着一大枝子“酸溜溜”,每一个身上都沾满了湿热的汗水,头发上落着草屑,膝盖上带着被“酸溜溜”的硬叶片划伤的细小血痕。我看着他们,心里一样东西满满的,却又说不出来。
没有人照料,孩子们就这样自顾自地在荒原上长大了。
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永远停留在了荒原上,那些快乐来得那么容易那么简单,但消失的速度却如此缓慢,直到现在,直到此时此刻。
四、梭梭
在荒原的漫长叙事里,如果必须有一个主角,那一定是梭梭。坚韧,顽强,牺牲,奉献,所有关于生命的大词,都可以用来歌颂一株梭梭。梭梭天真地领受着这盛大的多重意义,仿佛植物界的英雄。
我从来不觉得梭梭是英雄,如果一定要将这个称号给它,梭梭也只是一个悲情英雄。我并不是想否定附着在梭梭身上的意义,也没有想重新赋予它意义。荒原上的草木根本不需要附加任何形容词,它们只想安静生着,爱着,看顾这荒原。草木不需要人,是人需要它们,无论在生存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所以人才会把自己创造出来的词,强加给一株梭梭。
谁没有一无所有地挣扎过,谁不会理解一株梭梭。它的种子像孤儿一样被抛弃在沙漠里,如果几个小时之内没有一滴水,它就会死去,只要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就够了。那些干瘪的种子在日头下,声嘶力竭,没有人能听得到。
母亲说,黄昏时的天空像着火一样,第二天就会下雨。可是在荒原,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多么通红的充满渴望的黄昏,第二天,还会是一个明晃晃的大日头,还会是干涸的荒漠。没有什么能减轻荒原的干旱、炽热和大风,活着,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挣扎。
荒原上的孩子和梭梭一起,盼望著一场雨水。一朵坠落的云,几滴零星的雨,就足以让孩子们和草木欢呼雀跃起来。在长长久久的焦灼中,只能拼尽全力去抓住每一点点可怜的水分,任何一点点都会抓住死死不放,感激涕零。
哪一个生命的初始不是痛苦、较量和抗争呢?活下来的梭梭拼命长根,地底下的根系庞大而深刻,向着四下扩张,那些根系能够达到地上植株的八九倍大。如果深埋的根被风刮了出来,你会看到,梭梭的根茎像密密的缆绳,像章鱼的爪,深深地嵌在地下,牢牢地抓着沙丘。这个时候的梭梭,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干旱、高温和严寒都无法再伤害得了它。
梭梭把生看得如此重要,对生付出了这样巨大的努力,以至于忍受了生带来的一切折磨,包括失去它隐秘的爱情。
梭梭的树根上会寄生苁蓉,那是一味珍贵的中药。苁蓉吞噬着梭梭,吸取着梭梭的气息和水分,以此来充实自己。是梭梭的滋养和守护,苁蓉才能够在干旱贫瘠中安心地开着白色的淡紫色的花。梭梭不知道,它对苁蓉付出的越多,它的悲伤就会越大,这悲伤不是来自苁蓉,而是来自人,是人把苁蓉从梭梭身边夺走了。
梭梭根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大洞。一切挣扎都是徒劳,梭梭把苁蓉藏得多么深,人们也总能找见它。人们挖走了苁蓉,还会把籽粒洒在梭梭空空的心里,期待它的心血、情感再一次被榨取被掠夺。他们站在梭梭的外面,他们站在荒原的外边,他们听不到梭梭内心的声音,那些苦涩的断续的叹息。梭梭以为自己可以打倒任何严苛的环境,可是它最终在贪婪的破坏者和掠夺者面前败下阵来。
失去了苁蓉的梭梭,是不完整的,但它宁肯不完整,也不接受另外的种粒在它怀里生长。它蔑视那些人工梭梭,不停被播种,不停被收割,因为生命被过度吸取,所有的枝干叶片都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荒原上的梭梭有坚硬的骨头,它的爱情只给一株苁蓉,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孩子是最善于学习的,我们也跑到沙漠深处去挖苁蓉。苁蓉好难挖啊,没有工具,只有几双手,但是挖东西也是一种乐趣,像是齐心协力在干一件大事情。苁蓉终于被我们挖出来了,大家欢呼着,把苁蓉表皮上的沙粒擦去,互相传着吃。生的苁蓉一点都不好吃,可是我们还是奋力啃啮,咀嚼,填塞着我们焦渴的身体。
我们离开时,梭梭拽了一下我的衣服,我回过头去,吃惊地看到,梭梭白色的枝干直直地伸向天空,像无数双高举的手,我不知道那是在质问,还是在指控,我们拿走了它最爱的东西,它用生命滋养的东西,只给它留下一个深深的洞。那个洞像一枚钉子,钉进荒原的胸膛,钉进我的心里。太阳朝地面跌落下去,落在梭梭后面,梭梭瞬间着了火一样,那些血一样的晚霞啊,流淌到梭梭身边,从背后拥抱着它,像是安慰,又像是祈祷。梭梭成了黑暗的一部分,隐在它自己的身影里。
有很多年,梭梭在我的记忆里,都只是一种伤心的植物。我惧怕自己有梭梭那样的一个灵魂,那些贴附着荒原肺腑的东西,那些疼痛的东西,那些悲伤的东西。那么大的风,那么多的沙子,都没能把它身体里的洞填平。那些洞,让梭梭长成了一个空洞的姿势,也许,它宁愿让那个洞空着,仿佛它还在继续爱下去。
冬天的荒原,大风不停呼啸。梭梭的根紧紧地聚拢着,裸露在外面,枝干向四处散开,白白的,硬硬的,没有一点水分,像干净的骨头,像不可逼视的王冠。挣扎存活的梭梭,空荡荡的梭梭,一无所有的梭梭,在最后的寒冷中,还要把它的身体也奉献出来当柴火烧。
哥哥用刀子砍,他的手也裸露在外面,长着冻疮,鲜红一片。砍不了几下,两只手就会冻得像铁一样冷而硬,无法伸直,要揣在袖筒里暖和一会,再伸出来继续砍。他砍一下,那梭梭晃一下,我的心也跟着晃一下。
一棵植物被撕裂开来,是什么感觉?蓝得让人落泪的天空啊,悲伤地闭上了眼睛。
梭梭终于把我晃哭了。
哥哥停了下来,转过头来看着我,疑惑地问,是不是冻得太厉害了?然后用他那铁一样硬的袖口帮我擦眼泪。那袖口滑过我的脸,像薄薄的刀子,我哽咽起来,冲哥哥喊,你别砍它了,它多疼啊。
梭梭不说话,只是摇晃着身体。
哥哥犹豫了片刻,看看我,又看看梭梭,把刀子扔在了一边。
那个下午,我们捡了很多干枯的枝子,还有沙蒿。沙蒿干干的,没什么分量,我和哥哥一人能背一大捆。母亲看着我们背回来的柴火不高兴地说,沙蒿是最没用的,轰一下,草灰满天。梭梭才是最好的柴火,沙漠里走夜路的蒙古人,只烧梭梭。
那棵梭梭终究是被别人砍走了。
梭梭把自己放在火中,它一生费尽心力地活着,现在终于不用再挣扎了,谁也不能再从它身上拿走任何东西了。但是,它的意志,它的顽强,那些塑造了它的东西,本来也是谁都无法拿走的。梭梭镇定地缓慢地燃烧着,洁白的骨殖不发出任何声音。它不允许自己像其他的草木,火苗闪闪,噼噼啪啪地喊疼。
在最黑的夜晚,在最冷的风中,梭梭的明亮火焰如此平静如此安详,直直地伸向天空,“像皇帝一样面临死亡”。
五、沙枣
约翰·欧文在小说里写,沙枣树是一种美丽的树。
这个细节让我疑惑,这是不是我记忆中的沙枣树?
我一直以为,沙枣并不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树种,只有在西北居住过的人们才熟悉它。在重庆读书时,曾把沙枣带给同学吃,她们惊讶地说,你们小时候就吃这个呀,沙子一样,怎么能吃得下呢?这些话像一把明晃晃的刀子,让那些无人理睬的沙枣瑟缩起来,凄凉而无辜。
欧文继续描述,沙枣,叶子漂亮,银绿色,开黄花,有香味。
我停在这几行字上,一株异域的沙枣树,我的情绪突然不可遏制地激动起来,我知道,我们在述说着同一种树。
可是为什么,许多年里,我都没有觉得沙枣树美丽?美丽从来就不是沙枣树的形容词。
它的银色的叶子,它的黄色的花朵,像荒原上人们的脸,总是覆着一层薄薄的灰。没有人专门去种它们,也没有人管,它们自己也不择地势,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就长起来了,山坡上,垃圾边,煤堆旁。它們从来没有耀眼地活过,始终都是黯淡无光,蓬头垢面的样子,看着它们会让人疑惑,它们真的可以命名为树吗?
五月一到,沙枣花不管不顾地开了。
日日夜夜的大风不停把它的花苞打落,满地米粒一样大小的花苞,密密麻麻,任人践踏。但是还会有更多的花出现,它们仿佛对开花这件事怀有莫大的热情,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那盛开的样子不矜持,也不端庄,更不会让人有淡品、细想的余地,沙暴一样,洪水一样,一波一波直接涌了过来,把人淹没到窒息。
沙枣花的香气很特别,怪异的浓烈,我到现在也无法精确地描摹出这种味道。它不像是香气,它更像沙尘,浮在空气中,经久不散。在这样莫名所以的香气里,人会变得蠢蠢欲动。年少时,第一次收到的花就是沙枣花,花儿包在一张玫瑰图案的包装纸里,不知道是谁把它放进来,每天都会有一枝。花孤单地躺在课桌里,我心里充满了厌弃,不知道是对这枝花,还是把花放进来的人。花扔掉了,但它的浓烈香气缭绕不去,像罪证,像灾难,好多的天里,都是匆匆来去,不敢抬头看人。
不,不,关于一棵沙枣树,这些都不是源头。
沙枣是穷孩子的食物,路边的沙枣尚青,就被人摘了下来,摆在校门口售卖。苦涩的枣子用糖精水煮过,柔软,多汁,一种人工的甜,五分钱一茶缸,但也没有钱买。放学路上,忍不住去摘路边人家伸出院墙外的沙枣。一个胖孩子从院子里冲了出来,打掉了我手里的沙枣,然后,又用脚狠狠地踩着,几颗沙枣皮开肉绽,混在土里面,辨不清面目。回家的路上,一个人哭得如此悲痛。
小小的孩子们,整整齐齐排着队,背着水和馒头,走两个小时的路,去黄河边的荒滩上打沙枣。黄河边有大片的沙枣林,因为近水,长得高大,果实繁密,老师说要把这些种子寄到远方去。真是让人为他们心疼呵。那些长大的孩子,去了远方的孩子,星烟四散。他们走得如此之急,那些沙枣还没有成熟,就不见了他们的身影,而我也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脸。
黄河边上的沙枣树啊,还充当过更崇高的角色呢,那是没有任何娱乐的年代啊,以采集树种的名义,宣誓,篝火,诗歌……笑声,话语,萌动的心扉,羞涩的恋情,单薄的青春,一切都只为这一刻存在。我们经过的幸福,在秋天明亮的天空下,散发着饱满快乐的气息。此后许多年,或早或晚,沙枣终会无声落下,被人遗忘。
可是,为什么,沙枣带给我的仍然是苦涩呢,仿佛只有苦涩,我才可以抵达,那些纯粹的念想,永恒的瞬间。
我怎么能忘了那片荒滩,荒滩上劳作的母亲?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她必须要跟随接送她们劳作的卡车每天来回奔波,否则她就要走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到家。
母亲那时候还年轻呵,一棵果实饱满的沙枣树,就让她快乐起来,她要给她的孩子们打沙枣。黄昏收工的时候,她拒绝了跟车一起回来。
金黄色的沙枣,散落在地上,母亲的心,像一粒粒沙枣,雀跃着。她蹲下来,把她的外衣铺在地上,那些沙枣安静地挤在一起,闪着光,一堆小小的金子。
雁过的凄清的叫声,母亲没有听到,西边的天空暗黑下来,母亲没有看到。母亲站起身来时,卡车压出的车辙已经看不到了。天上没有星星,一轮淡黄色的月亮俯看着她。
母亲抱着她包满沙枣的外衣,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没有一丝光亮的路上。因为紧张,因为迷路,因为跌倒,到家时,满满的沙枣只剩下了一小捧。
母亲打开衣服,一颗一颗往外捡沙枣,她沾满了土的脸慢慢皱起来,她的嘴紧紧地抿着,仿佛一说话就会哭出来。我不敢看她的脸,我的视线落在那些沙枣上,那一小捧沙枣也沾满了土,在深夜的灯光下,泛着微微的黑。我拿起一顆,把它放进嘴里。坚硬的果皮,苦涩的沙土,缓慢的甜,还有体温,汗水,那些永不会落空的,温暖。
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的沙枣。
这些苦楚让人泪盈满睫。我重新回到了荒原,只有那里才是我和沙枣树存身的地方。春天会回来,带着它的风沙,但我已经看不见沙枣树了。那些黄河边的沙枣树,一年一年生长着,一直长到某一天,忽然发现它们站在一片大水之中。
我记得那一年,在西北的腹地穿行,车窗大开,一种熟悉的味道飘了过来。这种气味深深地进入我的肺腑,我怎么能忘记这味道呢,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我的血液里,我自己的气味中。
在一车人惊讶的目光中,我执拗地下了车,走到路边的林子里。
是的,就是五月的沙枣树。满树黄色的花,去年的枣子还孤零零地挂在枝头,我的目光抚摸着它们,泛光的叶子,纤弱的花朵,那些没心没肺大笑一般突然爆发的香气。一个掏空的世界。我曾经身处其中,如今这已经都过去。
我索性走进里面,摸着它们,它的花,它的果,像见到多年未见的家人。许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那一瞬间,我被打回原形,一个荒原上孤单无助的孩子,和简单粗陋的事物相依为命。
我摘了一把沙枣,独自坐在树下面吃起来。那些沙枣落满旧年的积灰,没有一丝水分,干瘪得不像样子,只剩下一层皮包裹着核,吃起来又干又涩,很难下咽。但是我还是把手里那一把枣子都吃光了,吃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