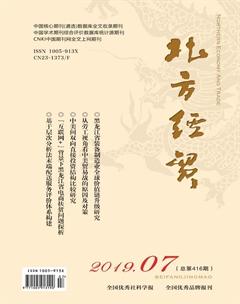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突破最高数额之限制
韩浩
摘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一直伴随并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近年来,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正步入深入发展的重要关口,传统的立法思维已经逐渐滞后,在预防、惩罚两大主要功能的驱使下,应当逐步探索突破惩罚性赔偿金最高数额的限制,以實现社会各方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金预防功能;惩罚功能;最高数额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7-0060-03
China's Puni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he Maximum Amount
Han Hao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d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s entering an important barrier of in-depth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legislative thinking has gradually lagged behind. Under the drive of the two main functions of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we should gradually explore the limitation of breaking the maximum amount of punitive damages.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society.
Key words: punitive damages prevention function; punishment function; maximum amount limit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源起与发展
(一)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过约二百余年的发展,已经衍生出了非常成熟的体系。制度诞生初期,受英国法的影响主要适用于侵权案件。19世纪后,美国法院开始对故意忽视原告权利的行为,判处惩罚性赔偿金。[1]而后,惩罚性赔偿金由惩罚个体转为保护个体。20世纪初至60年代,商事、铁路诉讼、个人侵权、恶意欺诈、侮辱、产品责任、商业侵权陆陆续续被纳入惩罚性赔偿的范围之内。20世纪80年代,惩罚性赔偿金被“狂热的”适用:法院经常判决惩罚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的额度经常很高;法院判决惩罚性赔偿金的频率和额度均迅速增加;以上三个现象在美国系属全国性问题。[2]如1998年,美国一家生产木材防腐剂的公司因六十五名原告受有人身损害而被诉,法院判决每人一美元的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同时,却判决该公司应赔偿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美国司法实践中判决惩罚性赔偿金“过热”的局面,令被诉一方“苦不堪言”,物极必反,一场惩罚性赔偿的改革运动悄然而至。从联邦最高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判决来看,对惩罚性赔偿的审查趋于严格。[3]但是也有实证研究指出,这次改革运动并未真正触动高额惩罚性赔偿的根基,也并没有改变法院审理惩罚性赔偿案件的思维定式,判决高额赔偿的案件仍然时常出现。
(二)台湾地区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深受美国的影响,以其“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中,[4]直接在法条中设置了上限,防止惩罚性赔偿被滥用。此外,在台湾地区关于公平交易、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立法”中,也建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总体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惩罚性赔偿基本是交易法上的规定;第二,适用范围扩张至侵害财产权,不限于传统侵害人身权领域;第三,赔偿额的确定考虑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并规定了最高赔偿倍数的限制;第四,主要适用于故意侵权场合。[5]
(三)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消费者保护法》(1993年)首次制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随后几年中《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相继制定了惩罚性赔偿条款。学理上普遍认为,该制度正在从合同责任向包含侵权责任过渡。从立法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以身份法领域为起始进行“试水”,逐渐向合同、侵权等领域逐渐稳步发展,呈现出与美国立法相反的发展过程。我国立法选择较为谨慎,以遭受欺诈,严重人身损害等条件为惩罚性赔偿的索赔要件,同时设置了最高限额。从立法的广度来看,也稍有不足,如在知识产权领域仍然存在空白点。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再解读
传统理论认为补偿、报应和遏制是该制度的主要功能。王利明教授认为,事实上,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还是补偿和惩罚。[6]也有学者认为补偿功能并非该制度的主要功能。
(一)预防功能
预防功能在美国称为deterrence,又被译为“吓阻功能”。我国学者在相关文献中将其翻译为遏制功能。遏制功能是对惩罚性赔偿的传统解释,分为一般遏制和特别遏制。一般遏制是通过惩罚性赔偿对加害人及社会一般人产生遏制作用,特别遏制是指对加害人本身的威吓作用。[7]在笔者看来,遏制功能完全可以称为预防功能。遏制作用在语言色彩上显得严厉,给人的感觉更侧重于对于行为人的“特殊遏制”。而预防功能,语言色彩则更为中性,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叫法也符合中文法律的用语习惯,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同时体现出法律的指引、预测、教育作用。一般预防在于警示他人不再从事与被告相同的行为。特殊预防在于使个案中的被告今后不再犯相同的过错。1791年,美国一被告允诺与原告结婚,但在原告怀孕后,被告拒绝履行婚约。法院在判决中表示:“被告之行为及其令人厌恶,败坏他人名誉,应付惩罚性赔偿责任。[8]法院认为该案的判决精髓不在于估算精神上或者实际上受到多少损害,而在于确立范本,避免社会上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这是一般预防功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