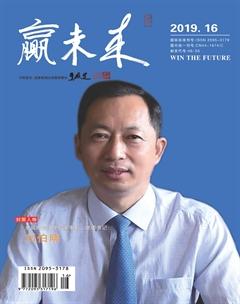近代英格兰中产阶级崛起背景下的教育演进


摘要:17世纪至1 9世纪初是英国中产阶级崛起时期:平民和中产者子弟通过学徒制,加入新兴中产者行列;非国教徒中的中产家庭迫于政治和宗教压力,开始自力更生兴办学园,以满足教育需求;大城市和市镇的中产阶级,为了联姻成功,率先将女儿送到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教育存在非正规、不系统、重营利等特征,但其发展方向,预示英国教育新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中产阶级;学徒;非国教学园;女子学校
1 英格兰中产阶级教育的目的
在教育史上,英格兰教育体系具有典型的“双轨制”特征。贵族聘请家庭教师,送男孩去公学就读,在牛津、剑桥取得学位,步入上流社会;穷人的孩子则无需深造,他们参加慈善学校或贫民学校,随时准备回家劳动,或被送到市镇当学徒。十六世纪后,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开始崛起——中产阶级。这个阶层伴随中世纪结束而生,到十九世纪已成为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
作为演进中的群体,人们很难对“中产阶级”进行严格界定。学界倾向于从社会学角度,将其概括为“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群体”。穆斯格雷夫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描述,有助于理解其内部差异:(见表1)
资料来源:F.穆斯格雷夫,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教育和职业[J].经济史评论,第12卷,第1期,1959:99-111.
十七世纪倒十九世纪,伴随商业化和工业化,英国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不过正因如此,中间阶层的内涵及人数也总是处于变动之中,难以被精确判定。事实上英国中间阶层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及社会意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据估算,到十八世纪末,英格兰中产阶级约50万人,占总人口的6.7%[1]。
中產阶级重视教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达到三个目的:(1)巩固家族财富。英格兰法律规定,不动产由长子继承。因此,中产阶级的父母,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将长子培养成合格的继承人;另一方面,要让其他兄弟学有所长,以备谋生;女儿则要培养成淑女,以觅得如意郎君。(2)提升社会地位。教育造就了中产阶级“绅士”,增加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上的话语权,彰显了家族荣誉,使他们有机会与贵族为伍。(3)获得道德幸福感。教育让中产阶级更加虔诚,他们服从教会,乐善好施,以博得乡邻赞许,并将财富视为上帝对其美德的嘉奖。
从群体演进角度看,英国中产阶级崛起分为三步:第一步,追求财富,成为中产者(从十五世纪开始);第二步,提高文化,成为绅士(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第三步,参与政治,获得议席(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标志)。这三步的逐级推进,与中产阶级教育发展密切相关。
2 中产阶级早期形成路径——学徒教育
十七世纪,英国在“晚期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纺织、刀具、家具、器皿、制陶、车辆、首饰、酿酒、采矿、冶金、建筑、造船等工业部门,以及将原料和成品销往各地的商业部门的兴盛,给英国社会带来活力[2]。”城镇工场、商店和乡村作坊主开始广招学徒,在廉价劳动的同时学习手艺。英格兰学徒制受法律和行会约束,新学徒年龄通常在11-12岁,学徒期为4 7年。师傅会根据生意需要,教他们数学和书写,学徒期满提供从业“证书”。学徒有高低贵贱之分。根据1563年《学徒法》:外贸商可接受拥有价值两英镑的不动产所有者的儿子为学徒,集镇批发商可招收技工的儿子,而桶匠和瓦匠只能招收无产者的孩子。因此,来自中产阶级的学徒和来自贫民区、孤儿院的学徒,在职业起点上就存在差异。
中产阶级子弟通过学徒制,维持了其社会地位。以雕塑家亨利-切尔为例:他是缝纫用品店店主的儿子。1718年,亨利被送到一位伦敦木匠家当学徒。学徒期满,他在威斯敏斯特建了自己的作坊,为贵族或大学制作雕像。由于技艺精湛,他的作品能卖到100几尼(约合105英镑)。因此,很多父母愿意交纳不菲的学费,让孩子做亨利的学徒。1760年,亨利-切尔被进封为骑士[3]。当然,出身并非唯一标准,学徒的资质也起着一定作用,例如,一个叫约翰-黑尔的学徒,就因文字能力差,而被店主开除[4]。
学徒教育是英国职业教育的萌芽,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教育形式之一。在公学、文法学校和慈善学校之间,学徒教育就像一把“楔子”,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学习机会。虽然学徒教育内部具有等级性,但由于底端向平民开放,使那些出身良好、心灵手巧的男孩有机会成为中产者。18世纪后期,学徒教育被学校职业教育取代,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3 中产阶级子弟的教育场所——非国教学园
当平民子弟开始学徒生活时,富裕的中产家庭则憧憬将男孩送入公学或文法学校。但是,公学是贵族教育的“堡垒”,“到1800年,仅在伊顿、威斯敏斯特、温彻斯特以及哈罗这四所公学接受教育的英格兰贵族,就超过了其总数的70%[5]。”文法学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英格兰长时间没有新建文法学校,现有学校课程陈旧、经费不足、教师短缺,已失去十七世纪初的鼎盛繁荣[6]。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英格兰中产阶级教育呈现多样化:地位较高的中产者子弟,进入公学;富裕的中产家庭,高薪聘请家庭教师;殷实之家送孩子去私人学校;技工、商人、店主、自耕农只要付得起住宿费、学费和忏悔节教师礼金,就可将孩子送到地方文法学校(十九世纪初约600所)。国教徒可选择质量较好的圣公会古典学校(十九世纪初约200所),非国教徒则自力更生兴办学园。其中,兴起于十七世纪中叶,消失于十九世纪初的“非国教学园”(Dissenting Academy),在中产阶级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非国教派包括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贵格会等,十八世纪初约35万人,起初贵族和乡绅比例较高,十八世纪中叶,城镇中产阶级成为主要成分[7]。1662年,英国颁布《宗教一致法》(Uniformity Act 1662),非国教徒的教师和学生被公学和大学拒之门外。于是,在教会和中产者资助下,教师们开始自办学园,收取学费维持运作。
学园招生人数受师资和场地限制,20人至200人不等。规模大的学园由知名学者担任校长,雇佣教师进行教学;小学园则由一位教师独立支撑。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英格兰先后出现过70多所非国教学园(见表2)。虽然,学园毕业生无法进入牛津、剑桥,但他们可以去莱顿、乌德勒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
资料来源:阿什利·史密斯,现代教育的诞生:非国教学园的贡献1660-1800[M].伦敦:泰勒和弗朗西斯出版公司,1954.
非国教学园的课程设置,有别于公学和古典大学。学园早期侧重教派宗教教育,此后逐渐向社会需求倾斜。1670年,理查德-弗兰克兰在北约克郡拉斯梅尔( Rathmell)建立的学园,开设逻辑、形而上学、圣灵学、神学、自然哲学、年代学等课程。学园最初的15个学生,其中6个毕业后成了非国教派牧师[8]到18世纪初,独立于教会的“伦敦国王协会”(1730年)开始兴办学园。学园课程日益世俗化,除了传统的神学、拉丁语、希腊语、哲学、英语,还开设算数、速记、会计、几何、法语、德语、历史、科学、商业、测量、航海、军事等课。至此,学园课程设置呈现出英国传统、非国教理念(如,素齐尼主义)和中产阶级实用精神相融合的特征。十九世纪后,随着宗教宽容和1836年伦敦大学的建立,学园退出历史舞台。
“非国教的学园,把现代性学科作为中产阶级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了中产阶级人才,为社会变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9]。”虽然,学园的教学水准参差不齐,还经常面临被关闭的危险,却培养出一批中产阶级精英,他们活跃于英国商界、法律界和医学界。
4 中产阶级的教育突破一一女子学校
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仍是男权等级社会:“女子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是由她的父亲或丈夫的地位等级决定的”,她们的任务是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她们在少女时代便开始为这些任务做准备,并被灌输了‘婚姻才能使女人生命完整的思想[10]。对贵族而言,家庭和修道院是女孩接受教育的理想场所,学习重点是上流社会的礼仪和文化。中产阶级女子教育的目标则是:成为虔诚、优雅的贤妻良母,能阅读《圣经》和料理家务。
进入十八世纪,经济繁荣带来了文化繁荣,古典文化复兴、出版业兴旺、诗歌戏剧盛行、海外见闻传播,在为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冲击着英国中产家庭。“以母为师”(包括其他女性长辈)的传统女子教育变得力不从心,女子学校应运而生。
女子学校有日校和寄宿学校之分,创办者通常是出于生计需要或个人兴趣,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女性。商人约翰-海恩斯6岁的女儿,就在克拉克夫人(Mrs.Clark)个人创办的日校学习。为了防止女孩沾染不良风气,家长们更倾向于寄宿学校的严格管理,还有人提出宏大的女子学校计划:“应该在伦敦附近建一所大房子,有附属教堂、礼堂和、宿舍、果园和庭院,由教区牧师、女校长和女舍监负责管理,聘请临时教师教授唱歌、跳舞、针线和烹饪,父母可以监督学校的财务状况。”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建立女子学校已成大势所趋[11]。
伦敦的沃尔布鲁克、德特福德、斯蒂普尼、伊斯灵顿、哈克尼区、托特纳姆和切尔西都曾建有女子学校。这些女子学校招收10岁至16岁的女孩入学,每年的学费在10到20英镑不等。到1827年,一些女子寄宿学校的学费达到每年57英镑,若选修其他课程,则另行收费。
女子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阅读《圣经》、祷告词、赞美诗、语法、写作、历史、女工和艺术。学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资料显示:一个叫贝蒂(1640)的女孩因傲慢、叛逆、难以管教,被送到寄宿女子学校。结果,在女教师的帮助下,贝蒂顺利渡过叛逆期,成了淑女,嫁给了一位牧师,令其家人颇为满意。但舍伍德夫人(1775)在回忆录中,则对女子学校充满憎恶,她抱怨老师是“二流女帽贩卖商一样皮笑肉不笑的英格兰妇女”、“不修边幅的法国女孩”和“满脸疮疤的瑞士女人”。
教育的性别差异,在近代英格兰根深蒂固。与贵族女性被视为“精致花瓶”不同,中产阶级的女性有更务实的社会职责,她们要料理家务,管理仆从,照顾子女,协助丈夫打理生意。这导致两个结果:其一,女性需要更多的知识;其二,她们无暇教育长大的女儿。因此,将不足婚龄的女孩送到学校,就成为中产阶级家庭,一举两得的解决方案。女子学校客观上,缩小了男女知识差距,从性别上巩固了中产阶级文化基础,为英国教育公平开辟了道路。
5 结语
近代英格兰中产阶级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偏到全”的过程:教育场所从家庭农场,到市镇作坊;教育内容从古典知识,到实用技能;教育对象从偏重男孩,到关注女子。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英格兰中产阶级教育经历了——摸索、争论、实践、发展消亡的过程,预示着社会文明的结构性变革即将开始。英国中产阶级教育具有多样化、实用化、人性化特点。这是因为中产阶本身具有多样性,其教育需求也是多样的;他们的教育目的较为现实,即是通过教育投入维护家庭利益;没有取代贵族的意愿,也没有迫在眉睫的衣食之忧,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教育态度积极,也更愿意尊重子女的意愿。十九世纪下半葉,国家干预、实科学校、中学理科班、伦敦大学、汤顿调查、初等教育法(1870)、女子中等教育、男女混校相继出现,使英国教育呈现出明显的中产阶级风格。
纵观英国中产阶级崛起过程,始终伴随着新生力量和保守制度之间的斗争,在教育上则体现为“阶层固化”和“阶层跃升”两种功能之间的博弈。虽然,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和教育壁垒,使英国中产阶级小富即安,并不奢求成为贵族。但是,英国工业革命和社会繁荣,为学有所成的年轻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客观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对通过教育“获得财富,改变命运”充满信心。这种教育热情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经济、文化基础较好,较平民视野开阔,故而成为英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力,
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英国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间段、速度快,为了子女的前途命运,中国父母将教育视为“救命稻草”。但是,不同于近代英国百年间“自下而上”的教育演进,中国中产阶层的急速壮大,未给教育改革预留充足时间。因此,中国教育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基层实践探索”必须同步进行。中国教育改革急需通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化”、“高等教育普及化”和“职业教育精英化”,打破制度束缚,增加教育机会,为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共同富裕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2]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182.135.
[3][10][12]【英】劳伦斯·詹姆斯著,李春玲等译,中产阶级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3-189.
[4]艾丽莎-莱文尼.诚实、稳重、勤奋:18-19世纪英格兰学徒制的师徒关系[J]社会史研究,第33卷,第2期,2008 (5):183- 200.
[5]【英】琳达·科利著,周玉鹏,刘耀辉译.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9]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17,123。
[7]【英】W.A.史培克,英格兰的稳定和动荡(1 714-1 760) [M].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101.
[8] 【英】艾琳·帕克,英格兰非国教学园: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6469.
[11] 【英】肯尼斯-查尔顿,现代早期英格兰的女性、宗教和教育[M]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1:134-140.
作者简介:王峥(1984.03-),男,汉族,天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