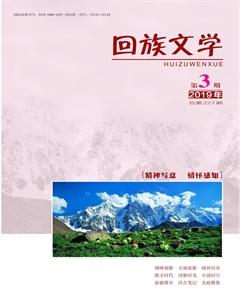亲戚三题
王 旭
哈 美
车拐下柏油路的时候,像是船被推进了海里,瞬间开始颠簸、滑行。透过车窗能看见前面的路面,石头、泥巴和雪水相融、交织,亲密得没有缝隙。轮胎从石头上滑落,碾压得泥水四溅,然后又重新滚上石头。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轮胎是在肆意地欺辱着路面。
这条未知的路看不到尽头,不堪的开头已经预示了后面的坎坷。我不知道哈美家会在路的哪个位置,也不知道哈美是什么样子。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走上一条陌生路寻找一个陌生人。
哈美是我的第二个亲戚,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除了哈萨克族,建档立卡户这个概念,就是那个永远打不通的电话号码——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辗转要来另外一个号码,也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在听过N遍优美的提示音后,终于传来了一个哈萨克族女人的声音。哈美的妻子汉语不是很好,说不清楚他们家来了谁,应该来谁。不敢放弃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不管她是否听懂,我重复着一个信息,我是你们家亲戚,要去你们家生活。电话打通一个小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这条未知路。
路况很差,有些地方泥泞超出想象,车轮在泥水中跋涉,被泥巴牵引着滑动着。最初的几户人家消失了,一座小涝坝一眼见底,看不到积雪,一片荒滩萧瑟寂寥,一条傍山小路旁边是水冲出来的深沟,除了车灯孤寂地跳跃着,四周都安静地沉入了日暮。
突然,几只小巧的身影从沟底疾飞起来,惊扰了视线。带路的拜克来说是呱啦鸡,小生灵被沉重的汽车声惊动了。呱啦鸡身材小巧,喜欢一群群在荆棘丛里做窝,据说味道鲜美,以前是冬季的猎物,现在作为保护动物,管理严格,没人敢捕猎,也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庄稼地边,农户家墙外的开阔地上,胖嘟嘟的身体悠然自得,与人和谐相处。
远处有了人家,透出一丝温暖和干爽。人家没有整齐的规划,不知道最初是沿着路修建的,还是后来路把一户户串联起来,每户人家都相距很远,灯光就愈加散淡缥缈。
这里有六户地村民小组的旱地,拜克来很熟悉,所以他的领路语一直是,再往前、再往前。那天问起哈美的住址,有人给我比画了一下,在松树下面,晚上还有狼。不知道距离松树还有多远,对拜克来的再往前的领路语也就不惊奇了。
山黑黝黝的身影好像截断路的时候,拜克来说拐过去就是,没有院墙,也没有路,一座黄色的房子透出一丝光芒。车拐进铁丝网的断开处,一阵急促的狗吠声,屋门开了,门里出来两个人,戴着帽子的消瘦男人和丰满的女人,这是哈美和他老婆吗?我喊哈美,他答应着过来握手,从车上提下来饮料水果,屋子里炉火很旺。
哈美让我们到里面屋子上炕。屋子的墙是粉红色的,屋顶两盏灯坏了一个,剩下的好像打不起精神,昏黄暗淡,粉红色的墙就显得格外刺眼,沉沉地挤压过来。
我们盘腿坐在炕上,长方形的炕桌摆着水果和馕,哈美一直在等我。
哈美老婆步履缓慢,感觉有病的样子。碗里倒上滚烫的茶,加上一勺奶子,哈美说喝茶吃馕。桌上的馕有两种,颜色有点发白,外表简单的是自己烧的;颜色金黄,上面沾满芝麻的是买的。我吃着有芝麻的馕,吸溜着冒着热气的茶,给哈美介绍我是新亲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上他,哈美憨憨地笑。这里信号不好,电话经常接不通。
驾驶员和拜克来走了,我和哈美重新坐在炕上,馕吃饱了,茶喝好了,哈美小声说,我们煮一点肉吃吧,我拒绝了。这个季节冬宰的肉基本上都要完了,条件好的人家熏马肉、牛肉,还有羊肉,条件不好的就剩炒菜的肉了。哈美老婆劝我喝茶,我说好了,她开始收桌子。
哈萨克族喝茶有一种仪式感,很正经地坐好,桌子上摆着馕、干果,开水烧好放入茶叶还要熬一会儿,女人专门坐在炕前倒茶。滚烫的茶倒进碗里,加一勺奶子,传递过来,条件好的还有酥油,自己可以调,据说养胃,喝茶吃馕,边吃边聊。不像汉族,随时随地用开水泡茶,想喝就喝。
为了喝茶的时候不再麻烦,我从包里掏出水杯倒满了,不加奶子的茶里放了盐,喝起来有点咸。哈美的国语不错,我说的他能听懂,他说的我也能明白,少了隔阂。他说小时候经常和六户地的回族娃娃玩,国语水平还行。
我们隔着炕桌,互相了解着对方。他的房子是去年政府免费给修的,八十多平方米,还给了四头牛,二十五只羊,两个娃娃都在上学,大的在疆外,具体地方说不上。哈美从身后一堆衣服里给我找地址,一个口袋一个口袋翻,找出一张纸不对,又找出一张还是不对。他趿拉着鞋去翻箱子,兴冲冲地拿着一张纸过来,我一看是修房子的用料单。在老婆的提醒下,他终于找来了,是在浙江衢州。哈美只上过两年哈萨克语学校,一个方块字也不认识。
小儿子在县城上高中,每周回来一次,哈美要骑摩托车到公路上去接。哈美说上学不用交钱,每次走的时候得给二百块钱,一个星期的零花钱。
他想起来什么,又趿拉着鞋出去了,进来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他说,你的名字、电话写哈,記不住。我在小本子上写上名字、单位、电话号码,他小心翼翼地收好了。
房子南北两个窗户,北面的窗户有风一缕缕地进来,南面窗户外面订的塑料布发出一阵阵哗啦啦的声音,下山风已经包裹了这座孤零零的房子,跳动着,努力钻进来。我坐在火墙边,能感觉到风里夹杂着冰雪的寒气。
哈美说小时候就搬到这里,算来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的草场在这儿,走不掉。夏天给汉族人家代牧能挣些钱,下面有五亩水地,种些麦子,汉族一亩地三麻袋,他的一麻袋多就算收成好了。政府给的牛和羊慢慢开始繁殖,过几年日子就好了。
我说你的儿子以后不回来了吧,这里太偏僻,没有发展前途,他说不回来了。我说不回来好,他们应该走出去,让儿孙也走出去。
我们都沉默了,风没心没肺地呼呼着,撞击着贴着窗户的塑料,声音熟悉而又久远。
每个人的长大都是在背井离乡,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县城到大城市,从土坯房到砖房,从砖房到楼房,似乎一直在努力把先人的生活遗迹一点点抹掉,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拼命刻上自己的印记,很多年以后,这里也许再也没有哈美的痕迹,只是一段记忆。
哈美又去给炉子添煤,能听见炉火轰隆隆的声音,我总感觉能闻到火墙缝隙里散发出来的煤烟味。也许是好久没有坐在火墙边了,我摇摇头,看看有没有中毒的症状。墙壁上的粉红色竟然不是壁纸,类似于一种泥巴的材质,直接抹在墙上,显得粗糙,难怪有那么重的挤压感。
这里住着十几户哈萨克族牧民,哈美说好几家都买车了,口气里感觉心痒痒的,我说车在这里用途不大,费钱的机器。我想起了狼,他说以前有,现在都到后山了,有鹿还有呱啦鸡,我问有没有枪,他嘿嘿笑,现在那个不能有。
哈美的老婆在那边的房子里看电视,哈萨克语节目,声音很大。我掏出手机,电线杆一样的信号断断续续,像被风吹来吹去,纠缠了半天,电线杆完全消失了,等了一会儿还没有回来。
哈美在对面睡着了,他靠在一堆衣服上,戴着帽子的头没有后仰而是前倾着,低低耷拉在胸前。这种姿势只有经常外出劳作的人才有,向后没有舒服的枕物,只能短暂的眯缝一会,头完全向前垂下时就会惊醒。
我喊哈美:哈美!他一下惊醒了。你瞌睡了吗?他问。虽然感觉困了,我还是忍住说没有。哈美坐起来说,这个房子冷,要不你到那个房子睡吧,那个炕上热和(暖和)。我犹豫了一下说没事,不冷,其实除了靠近火墙的半边身体,另外半边一直凉飕飕的。
哈美的老婆是另外一个乡镇的,基本和这里是平行的,但是那里已经通路了,条件好多了。哈美的姊妹都嫁到别的地方了,估计都来得少,串一回门也不容易。
我不是一个很会找话题的人,说话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哈美说忘了给我取枕头。在哈萨克族人家做客,炕上盘腿坐久了,主人会给枕头,让你靠着墙舒展一下。靠在三个大枕头上,我伸直双腿,浑身都忍不住的一阵舒坦。半间房子的炕足够扔掉所有的压力和疲惫,尽情地把蜷曲和僵硬从地毯的缝隙里丢下去。
看手机已经快十二点了,冰雪还未消融,哈美还处在冬歇期。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我还是决定睡了,要珍惜大坑上无拘无束、自由不羁的美好时光。哈美掀开炕桌,铺好褥子放好被子,又拿来一个小手电筒,晚上出去拿这个,外面太黑。
打着手电筒站在院子里,无边无际的夜把光亮压缩得稀薄而又涣散,远方黑暗迷茫,只有眼前几墩干枯的芨芨草摇曳着,和风做着无谓的抗争,恍然间觉得草丛的后面应该隐藏着一只饥渴的狼,想想没有狗吠,又释然了,把一泡热腾腾的尿灌溉在芨芨丛上。
哈美没有关房门,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本来是要提醒的,如果真有煤烟,房门开着安全。靠在火墙边,钻进被子里,辗转了几下就睡着了。
早晨七点多我就被冻醒了,感叹那个整个冬天不生炉子也不怕冻的小伙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外面房子有动静,哈美两口子也起床了,又舒展地赖了一会儿床,才爬起來穿衣。
阳光一点也不刺眼,只是把一层淡黄的温暖均匀地涂抹在沟沟壑壑里。春风冰凉,我放眼四望,探寻这个陌生的地方。山就那么清晰地挺立在眼前,山坳里的松树像一簇簇黄绿的毛绒玩具,触目可及,瞬间矫正了近视眼。
几户人家错落有致,东一家西一户,山顶的、坡底的,红墙的、黄墙的,一条路像是枝干茂盛的树,把一家家串联起来,很是有趣。
相距这么远,沟通是个费劲的事情,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通讯就基本靠吼了。现在的也不是很好,手机信号像是捉迷藏,看着有了,一按键又消失了。
哈美的老婆做好了饭,炒了一盘包包菜,奶茶馕,三个人围着炕桌,菜炒得很有味道,我们边吃边聊。我说哈美,夏天多代些羊,可以多挣钱。哈美说不行,草场太窄了,两边都是庄稼地,不小心就吃了庄稼,一个人看不过来。
我问夏天有旅游的人吗,他说多呢,尤其采蘑菇的人一群一群的,羊肚子蘑菇可贵了。我说开农家乐可以吗,他说上面有个回族开的农家乐,人也挺多的。说完还补充一句,夏天你们一家子来这里攒劲得很。
吃饱了,哈美还在让,你吃得太少了,多吃点。我问吃菜怎么办,他说每星期去大有镇买菜。我说你这里很宽敞,可以种菜养鸡,养一群鸡,自己吃肉还能卖钱。他说老鹰多,专门抓鸡,大鸡小鸡都抓。
哈美去喂羊,路边有一垛草,一群羊赶出去,从草垛上挑下一些草,羊就安静地围在一起,没有惊扰,与世无争,草就吃得悠闲自在。哈美老婆提着两桶子雪,倒在锅里消融。
这里叫路家泉,顾名思义有泉水。哈美说泉水从来没有干过,夏天都喝泉水,我觉得这跟人烟稀少有关,没有过度采伐,让地下水经年不竭。
我问升国旗吗,哈美说每周一都升,在跟前邻居家。远远望去,人家的院子里有一根高高的杆子,我说升国旗好,每个公民都应该升国旗。哈美说生活好了,要感谢党和政府,我说对啊,房子政府免费修,羊也给牛也给,以前想都不敢想,只要勤劳日子会越过越好。
太阳越来越高,昨夜冰冻的土地开始消融,泥泞打消了想到远处走走看看的想法,只能在狭小地方转动着。从早晨打完电话后,手机上的电线杆已不足以拨出一个电话,不知道驾驶员什么时候会来,能不能找到。
一丝焦灼在心里弥漫,没来由的。劳累的时候渴望有个安静的地方,空气清新、开门见山、鸟语花香,没有熙攘的人流,享受远离尘世的自由和惬意。实现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孤寂,对物质匮乏的不适应,对简单交流的无味,对与世隔绝的恐慌。
哈美靠在墙上,眯着眼睛,想着心事。他的心事一定很多,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不同经历的人,会更容易有心事。儿童、青年、中年,弹指间五十多年,要隐藏多少心事。
风拂过脸颊,丝丝缕缕地钻进肌肤,有刺骨的感觉,无处可藏。这是山区春天的风,努力把残存在松树、小草、石头里的冰冷搜刮出来,天才会慢慢热起来。
哈美固定着姿势,黝黑的脸庞已经适应风的亲昵,浑然不觉,悠然被风抚慰着。
生活是习惯和顺从环境的过程,一切都觉得是应该的、自然的时候,生活就固定了。
冬天的寒冷,春天的泥泞,夏天的茂盛,秋天的收获都变成习惯,成为哈美的生活。在这块承载希望和痛苦的土地,白天劳作耕耘、放牛牧羊,晚上和老婆在炕上看电视,聊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想以后发生的事情。
时近中午,哈美说中午吃个拉条子,我无法拒绝,因为什么时候离开还是未知数。哈美的老婆手有残疾,这是哈美告诉我的,但是一点不影响做饭的速度,一会儿拉条子就上桌了。哈美给我盛了一大盘子,他自己端着很大的一个碗,我说吃不掉,他说吃,肚子饿的时候他能吃三大碗。菜是早晨剩下的,哈美拿大勺子给我往盘子里舀菜,抬头看见他的碗里几乎不见菜,端着一碗白面,剩菜太少了。下次来一定多带些菜。
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直奔哈美家,我在好奇驾驶员怎么找到的。他說一路上打了五六个电话都无法接通,看见我微信上的图片,一幢黄房子,前面还有木头梯子,才循着而来。
给哈美五十元伙食费,他推辞了几下收下了。我说下个月再来看你,他说好好。
像是在回放昨天的镜头,松树、青山向后退去,哈美的房子,稀疏和荒凉都在向后退,越来越远,直至消失不见。泥泞消失的时候,我们走上了柏油路。
回头望去,路已经看不见了,我还是努力回望着。顺着路远去的地方会成为我的另一个家,那里生活着亲戚哈美一家。
跟着羊群去旅行
时间已经到了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碧绿,绿的庄稼、绿的草场、绿的松树,绿的浓度不同,就把绿色分割成一块块,随着山势的起伏,错落有致,变成深浅不一的调色盘。
美丽的景色让人总有想干点啥的冲动和渴望,否则会有辜负的遗憾。我问了哈美,没有下雨也就没有雨后春笋般的蘑菇,地瓢成熟的季节还没有到,所以除了看绿色、拍绿色,就找不出和绿色相关的趣事,有点百无聊赖的感觉。
哈美已经习惯了和我相处,大部分时间可以陪我聊天,他的工作也不多,每天给牛羊饮水,晚上把牛羊赶到草场的圈里,牧民的生活比农民要悠闲一点。
哈美的妻子怕我着急,指着家里的无线路由器,让我和大山外面不至绝缘,手机划拉了几下也没有兴趣了。我很少玩游戏,手机对于我只是接打电话,看个微信,浏览新闻。
哈美在院子里陪岳父岳母聊天,老两口从另外一个乡镇来,翻过哈美家东边的山,沿着一条崎岖蜿蜒的土路。那边有个医生,哈美的岳母在那儿抓药治病,在这儿住了已经有一段时间。老两口的国语水平都不太好,和我聊天像打铁,此起彼伏,总不在一个节拍上。
我庆幸包里背着小说,趴在占满三分之二房间的炕上,肆无忌惮地让身体伸展开,眼睛里是故事情节中的人物,耳朵里是哈美和岳父的哈萨克语音。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能随遇而安的人,在家里的床上我可以没有时间观念地看书,错过早饭、不吃午饭、饿过晚饭,一次次在爱人怒目而视中,嘿嘿笑着,马上睡。听见她的呼吸声我继续沉浸在书里。
没有发现黄金屋,没有找到颜如玉,只看到眼科医生迷惑的眼神,面对她指挥棒下的各种“E”,我茫然地摇头,“0.2”“0.3”的视力,她肯定把我打入睁眼瞎的黑名单。
在哈美家炕上,没有人打扰、没有人监督,心却安静不下来。书看得索然无味,仿佛在数字消磨时间。我惊奇自己的内心,这样美好从容的环境里,竟然不能心无旁骛。
哈美进来打招呼,现在要饮牛羊,我顿时有了兴趣,要跟着去。哈美小眼睛瞬间就亮了,嘴巴咧着笑,掩饰不住的兴奋。
哈美心里应该是有隔阂的,直觉告诉他把我当客人了,一边小心翼翼展示着简陋的生活,一边又渴望我能走进来。他不知道,时下的城里人都害着重返大自然的焦渴症,鄙夷着农村的单调,又大快朵颐无公害的鸡羊蔬菜。一个城里人说,二十多年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让我震惊不已。
其实我对农村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哈美没有发现。突然看到对他的工作感兴趣,身边又多了个说话的伴,这种感觉肯定很快乐,其实我更高兴。高兴来源于内心,如此广袤悠远的环境,不用把心禁锢在一间水泥屋子里,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跃奔跑。
哈美话很多,把我当做平淡生活里彻头彻尾的外来者,急于让我熟悉他周围的一切,边走边给我指引左邻右舍,指引远处的路,近处的草。
住户分散,地势不平,草就疯狂地长,拼命填补所有的空间,高高低低,脚下的路是草地,走的次数多了草就东倒西歪形成了路。
哈美的牛羊在他的草场里,草场面积一千多亩。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是怀疑的,验证过草场证才深深惊叹,土豪啊,对于我这种以平方米为单位的人真正地天文数字。
哈美的草场对着房子,步行几百米就到了,门口是简易的栅栏门,绳子绑着防止牛羊跑出来,打开门地上是牛粪,牛也渴望自由,常常倚门翘望,出门无果最后留下了失望的印记。
我不想变成一朵鲜花,在牛粪堆里就走得歪歪扭扭,怕一屎足千古恨。左边是铁丝网,把草场和庄稼隔开,右边是山坡,郁郁葱葱,脚下是开垦出来的一条路,像是大型机械的作业。
心跳跃在满眼的绿色里。哈美说路是他挖出来的,我有些吃惊地望着他,这个工程量不小呢,就凭眼前这个瘦瘦弱弱的男人,不过也找不出来他吹牛的理由。
我急切地寻找着羊群,想起文友的一篇散文《跟着羊群去旅行》。一个“跟”字道出无限的自由和放松,漫无目的,无牵无挂,任由心绪跟着行走的羊群,高山平地,草场树林,或行走或停驻,或低头或张望。羊是领头者,是引路者,我会没有思想,没有愿望,变成山野中的一点一滴。
我还没有找到羊群,还在跟着一堆堆的牛粪旅行。没有告诉哈美我的想法,如果放羊也算旅行,那么他就是旅行家。
转过一道弯,六只羊挤在路边的铁丝网旁边,对着我们惊恐不安,两只大羊四只小羊,小羊毛茸茸的,特别可爱,我以为是哈美的羊群,他摇头否定了。仔细看了一眼,说这是某某的羊。我有些吃惊哈美的判断,某某我认识,是农区的养殖大户,关键是他家距离这里差不多十几公里。这是六只羊啊,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挂吊牌,怎么能一眼认出来呢。哈美说得很肯定,并且判定是从后山跑来的,他的草场只有后山没有围栏。
六只羊挤过铁丝网,冲下山坡,瞬间已经跑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回头张望着。我们中间隔着一块绿色。
哈萨克族在长期的放牧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独特的辨别牲畜经验。我们所忽视的细节、不关注的特征,正是他们辨别的依据。哈美给我这个路盲加眼盲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大课。
我常常尴尬在大街上面对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微笑,也会擦肩而过时听见爱人的提醒,刚才人家冲着你笑呢。回过头去,已经分辨不出来模样,换几辆出租车都找不到宾馆,大部分时候分不清东西南北,屡次的糗事让我对自己越发丧失信心。
如果跟着羊群去旅行,羊群不带我回来,估计一定會把自己丢掉。
在两个山坡之间的开阔地上,一群羊散开着,像绿地上的一片白蘑菇,哈美说这是他的羊群。我遥望着,要跟着它们去旅行,羊儿走我就走,羊儿停我就躺在草地上,嘴里咬一根狗尾巴草,望着蓝天白云,看一只鹰的影子在头顶盘旋,用要命的嗓子唱一首歌,在羊群的咀嚼声里思考人生。
我朝着羊群走去,我要去旅行。羊显然被不期而至的陌生人惊吓了,奋蹄疾奔,一下拉大了距离。我也愣住了,和想象出入太大。
我试图再次靠近,羊群非常不友好地继续狂奔,距离又被拉大了。我有些失落和沮丧,难道要追着羊群去旅行,把缺乏锻炼的身体跑成一团稀泥。
哈美不知道我的想法,否则他会好心地把羊群赶到我面前。我遥望着低头徘徊吃草的羊群,悠然自得,屁股一抖一抖嘲笑我的稚嫩想法,只能用目光跟着羊群去旅行了。
哈美也许害怕我走累,说牛还在远处的山上,他要去赶回去,让我先回去,我只能接受他的好意。
我独自走在路上,看着绿色斑斓的土地,一切都是安静的,每一个生命都在默默地成长,彼此相望,互相欣赏。如果有来生,是否还能站成现在的模样。
庄稼正值妙龄时光,希望在慢慢拔节,下次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童年的味道
哈美正在打草,看见我扔下镰刀跑过来握手。哈美媳妇开始烧茶,滚烫的奶茶,有点冰硬的包尔扎克,应该是从冰柜里取出来的。
我和哈美盘腿坐在炕上长条桌的两边,哈美说喝茶,喝撒。我吸溜着奶茶,问最近家里的情况,哈美说都好呢。
喝茶是哈萨克族的一种交流方式,喝一口聊一会,端起来再喝一口,喝得悠长,不急不缓,在茶水的热气里慢慢松弛,然后在滋润里交流。
我和哈美的茶喝得有点余味不足,语言、经历、见知都有差别,每次都喝出沉默,喝得草草收场。
喝完茶,我要帮哈美去割草,他说不要了,草不割了,明天再割。
然后问想不想去揪地瓢,仔细看着我脚上的鞋,问滑不滑,能不能上山。每次来我都会穿运动鞋,适合山上行走。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哈美隔着窗子指着前面的山,能爬上去吗,他把我当作一个养尊处优的人。我笑了笑,没问题,他不知道我曾经徒步穿越过车师古道。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哈美放心地笑了,好像他的一个心愿可以了却了。
哈美的小儿子叶儿包拉提手里拿着手机,跃跃欲试地等在门口,看见我出来几个跳跃,从院子里的旧沙发上拿起一个小盆子,看来他们都已经说好了。
揪地瓢在哈美心里已经计划了几个月,我也酝酿了好久。第一次到哈美家,他就给我夸耀这里的蘑菇和地瓢。蘑菇没有引起我的兴趣,虽然是价格不菲的羊肚子蘑菇,但我对蘑菇知之不多,区别不开有毒和可以食用的。地瓢却有着难以忘却的亲切和美好,那是舌尖上永远的童年味道。
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故土情怀,努力把故土所有的美好都呈现出来,渴望得到肯定和赞美。哈美的身边除了土生土长的植被,再也没有可骄傲的,所以他会经常告诉我,夏天这里会有许多采蘑菇、揪地瓢、避暑的人。感觉这是夏天的乐园,事实上每次除了我之外很少有新鲜面孔。
但是哈美一家依旧锲而不舍地给我展示这片土地的丰硕和甜美。五月,哈美媳妇让叶儿包拉提带我去摘椒蒿、野韭菜,六月的羊肚子蘑菇我没有赶上,赶上了七月的地瓢。
叶儿包拉提上高二,身材瘦小,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一只手里的手机哼哼唧唧唱着歌,一只手里的小盆甩来晃去。我要他拿个塑料袋,爬山上坡端个盆子不方便。可他还是坚持,对自己爬山的水平充满自信。
我们翻进“土豪”哈美的草场,叶儿包拉提指着倾斜的山坡问能上去吗。我说没事,这样的山坡对我是小菜一碟。转到山坡的另一面,叶儿包拉提说这里可以找到地瓢,黄绿的野草和裸露的山土,今年是一个缺水干旱的年成。
我低着头弓着腰,自下而上地寻找,我知道寻找地瓢的奥秘。地瓢长在背阳的地方,农村人习惯称呼为阴洼,照不到太阳,果实藏在叶子下面,从上往下,往往一无所获。
我在野草里、刺堆中搜寻着。几颗红色的果实终于跳进眼帘,红的暗淡,让人爱怜,像红色里加入一抹黑色颜料。
我小心揪下一颗,放在手心里,椭圆的外表上凹凸不平,布满小小的颗粒,没有娇艳欲滴的饱满,看不到甜蜜的汁液,只有好像被热量榨干的成熟。
有人说地瓢是野草莓,不知道有没有依据。地瓢形似草莓,个头却小得多,是高度浓缩版的。如果说草莓是白富美,地富水满的种植浇灌,汁液饱满,外表靓丽,地瓢只能算是矮丑穷,在荒山野岭顽强的自生自灭。
地瓢没有想象中的繁茂,三三两两稀稀落落的,叶儿包拉提说你尝尝这个。他的手心里摊着几个品相不错的,我拿起一个放入嘴里,没有满口生香,只有淡淡的一丝乡野味道,山风吹过的气息,山土孕育的干涩,炙热太阳的焦灼。
盆子底都没有被地瓢盖住,叶儿包拉提说上面一个地方多得很,要不你在下面揪我去上面,然后端着盆子朝上一溜烟跑了。
山野间瞬时空寂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太阳开始西斜,阳光照在对面的山坡上,浅淡明亮,镀上一层光芒。
小时候“六月六”像是节日,传统节目就是揪地瓢,左邻右舍、姊妹亲戚相约着上山。那时候雨水多,地瓢红得发黑,有清香的甜,带着茎杆,一束束地捆扎好,放在枝条编的筐子里。我们吃的满嘴满脸都是红色,甘甜的滋味一直挥之不去。
我往下走了几步,寻找草高且密的地方,效果明显,地瓢明显地多起来。我揪满一把找了一片张开的草叶放在上面,绿色上滚动着点点红色的小玛瑙,特别好看。
地瓢要揪,揪有小心翼翼的感觉,是对幼小果实的怜惜,三指聚拢,轻轻用力,红色的果实带着绿色的几片茎叶,滚落手心,颤颤悠悠。
我的成果放满三片草叶的时候,叶儿包拉提端着盆子从上面冲下来,他所谓的上面多,其实也仅仅揪满盆子的三分之一,加上我的,勉勉强强不让人失望。
我坐在山坡上抽烟,广袤的天地,烟抽得无拘无束,空旷缥缈。叶儿包拉提坐着玩手机,也许海拔的因素,这里可以使用流量,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寂寞。
叶儿包拉提突然问我,叔叔你說这里缺一样东西,是什么?像在考我,我说如果是自然条件是缺水,如果是人的思想是缺乏观念,走出大山的观念。他说就是缺水,他没有问为什么是观念,这或许是他还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他说将来要回来,在这里发展,我说你们都不会回来的,以后除了你爸爸妈妈你们都不想回来。他看了我一会,没有辩解,眼神里的光芒暗淡了。
朝着东南方向,翻过好多山,走过很远的路。那里是我的家乡,依山傍水,现在河坝已经干涸,屋顶上长满野草,留守的人日益老去,好多年以后或许再也没有生活的遗迹。
叶儿包拉提是我很久没有接触过的年轻人,会问一些对他貌似很引以为重的问题。然后很成熟的样子和我讨论,这是青春期的必然过程,他在思考也在迷惘。
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特警,满脸沉醉的样子和我讨论。他自己的想法,老师的建议都让他充满难以抑制的兴奋。他穿着一件胸口有国旗的黑色体恤给我炫耀,说是特警的衣服,专门买的。
可是他在理想面前依然无法克制好多不良习惯,整天抱着手机,吃饭看一眼手机吃一口饭。这些貌似时髦的习惯,会狠狠影响他的未来。
我给哈美说离开这里去县城,开个小饭馆,专卖哈萨克族风味的手抓肉。我知道县城有一家专卖手抓肉的哈萨克族饭馆,生意火爆。哈美躲闪着眼神,说等叶儿包拉提考上大学后他考虑到县城。
我朝着北面,那里可以看见县城。天是发亮的深黄色,我能想象到阳光的炙热,又是一个高温天。
绿色的山峦和明黄的天空遥遥相望,一条路时断时续,被遮挡被隐藏。从碧绿走到明黄有多远,要多长时间。叶儿包拉提肯定能走出去,手机、电脑已经给他展示了太多外面的精彩,削弱了对故土的留恋,他不会选择在这片土地上打草、放羊。
叶儿包拉提说要回家吃饭了,我端着盆子,边走边凑到盆边上深深嗅了一口,一股自然的味道冲击着鼻腔,芬芳香甜。是童年的味道,有一种对故土难以割舍又无法相依的情感。
叶儿包拉提在崎岖的路上蹦跳着,阳光洒满全身,很多年以后不知道他是否能想起童年的味道,想起在绿色里跳跃的样子。
王旭,男,汉族,70后,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民检察院干警。新疆昌吉州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