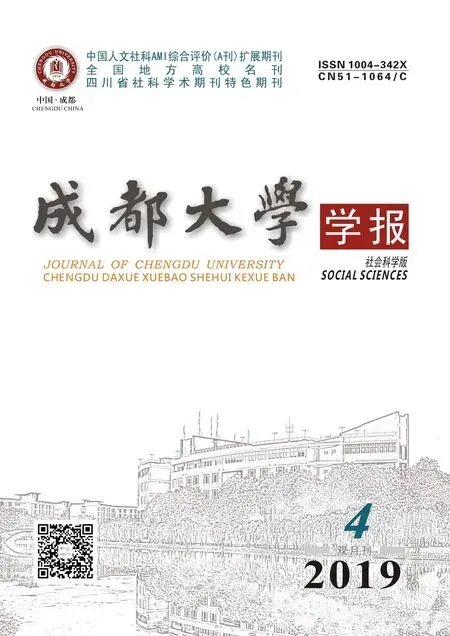道教影响下的薛涛诗歌研究*
卢 婕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卿希泰先生认为:“唐代道教兴盛,反映在诗歌中,以神仙思想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成为唐代诗歌门类之一。”[1]52-56葛兆光先生认为“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2]10-13作为中国本民族传统宗教的道教对于我国唐代诗歌的影响是巨大、深远而多维的。唐代女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留存诗作92首,是中国古代留存诗歌数量最多的女诗人。薛涛诗歌作为重要的传世文献,证明了道教在助推我国唐代诗歌,尤其是唐代女性诗歌经典化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道教影响下的薛涛诗歌语言
《全唐诗》小传言薛涛“辨慧工诗,有林下风致”[3]。所谓“林下风致”,是指薛涛颇有“竹林七贤”之风,有淡泊从容、飘逸洒脱的风度。然而,身为乐伎的薛涛身份卑微,何以其诗文能有“林下风致”呢?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其诗歌中频繁选用的道教语汇。道教语言本身有一种古奥典雅的气韵。薛涛将道教语言入诗,这使得其诗歌语言具有清奇雅正的特点。
首先,薛涛好以“仙”字入诗。比如,在《摩诃池赠萧中丞》中,薛涛先是回忆曾经与萧祜一起辅助武元衡,然后感叹今天虽能与萧祜泛舟同游,而武元衡却已经遇刺身亡。她写到:“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旧仙舟。”在记叙泛舟一事时,薛涛选用了“仙舟”一语。与其他诗人在记叙泛舟时所用的“扁舟”“轻舟”“兰州”“孤舟”“渔舟”“归舟”“行舟”等相比,“仙舟”自是多了一份傲岸泉石的逍遥和超脱世俗的淡泊,为薛涛的诗文生出一份高雅不凡的韵味。又如,在《斛石山晓望寄吕侍御》中,薛涛在描述斛石山日出的壮美时,用“曦轮初转照仙扃”,将斛石山比作白日飞升、羽化登天时需要经过的“天门”——“仙扃”。在《海棠溪》中,薛涛描写位于道教圣地青城山的海棠溪春景为:“春教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她将缭绕在海棠溪的彩云看作灵山“仙霞”。又如,在初入韦皋幕府时, 为感谢韦皋赏赐新服,薛涛做了《试新服裁制初成》三首。其中,在描述韦皋赏赐新服的宫殿时,她写到:“紫阳宫里赐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用“仙雾”氤氲来暗指韦皋宫殿不只是富丽堂皇,还具有灵秀之美。在写到衣服的颜色和款式时,她写到:“九气分为九色霞,五灵仙驭五云车。”而在写到穿着道服进行表演的乐伎们的气度和姿态之美时,她又赞叹到:“长裾本是上清仪,曾逐群仙把玉芝。”从以上例子来看,薛涛诗歌中时常流露出一种“神仙”向往。在精神上,她欲脱尘而去,与仙为友。因此,在对诗文的遣词用句时,自然而然,她总是青睐于使用与道教中宣扬的一些与“神仙”相关的语汇。神仙崇拜是中国道教信仰的核心。黄云明认为:“一般来说,人为宗教都将人生理想境界设定在彼岸的死后世界,惟有道教的神仙信仰与此不同。虽然道教也称仙界为天界,但是道教更多地将仙界设定在现实的人世,只不过是远离市井闹市的海外孤岛或者丛林山巅,神仙府地不是精神境界而有实际的地理位置,神仙学说中最初传说的仙山方丈、蓬菜、瀛州,人们也相信它们是真正存在的,正因为如此秦皇汉武才多次谴使入海寻访长生不死之药。唐宋以后,市井闹市也成了神仙出入之所,人间即仙境,神仙和人的距离越来越小。”[4]100-104或许正是因为从唐朝开始,仙与人的距离缩小了。原本需要生而有异相异行、勤修道术或得道高人的接引才可成仙的道教理想在唐代变得更易于实现。“仙”字成为薛涛诗歌中的一个高频词汇,一方面说明了唐代神仙信仰中仙与人的关系、仙境与人间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薛涛利用人们的神仙信仰,成功地洗去其乐伎身份对其诗歌的负面影响,令其诗作出淤泥而不染,不艳不妖,尽显高洁端庄之美。



二、道教影响下的薛涛诗歌典故
薛涛善于用典,极具征事引辞之巧。比如,《谒巫山庙》《酬人雨后玩竹》《斛石山书事》《酬文史君》《酬吴使君》《春郊游眺寄孙处士二首》《送卢员外》《送扶炼师》《酬杨供奉法师见招》等多篇作品的用典都显露出薛涛高超的才识和敏捷的思维。薛涛深受道教影响,道教典故自是谙熟于心,运用起来得心应手。道教典故与其诗文的结合产生了不俗的效果。尤其是在酬赠诗中,她常以道教名人与所酬赠对象相比,这样一来,既加深了诗人与酬赠对象的友情,又使得其诗文不至媚俗。而在叙事诗、咏物诗和抒情诗中,薛涛也时以道教典故入诗,这使得其诗文内蕴丰富而俊逸飘举。

道教典故还出现在薛涛的咏物诗中。薛涛在《西岩》中写到:“凭栏却忆骑鲸客,把酒临风手自招。”杨慎《全蜀艺文志》载:“太白读书处,一在西岩,万县对山,有大湖在顶上;一在匡山,彰明县中。”[16]40-44薛涛在此诗中咏到的西岩应该正是李白读书之处——今四川万县西山太白岩。诗句中的“骑鲸客”一典出自杜甫在《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中的诗句“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讯今如何?”仇兆鳌注:“俗传太白醉骑鲸鱼,溺死浔阳,皆缘此句而附会之耳。”由于杜诗的流传,后人常以“骑鲸客”代指李白。受杜诗的影响,民间甚至流传李白不是溺水死亡,而是骑鲸仙游去也。从薛涛的诗文来看,她也愿意选择相信“谪仙人”李白最后是骑鲸遁入沧海,重归仙班。典故中的人物李白是唐代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除了“诗人”这一身份之外,他还是一名受过符篆、列名道籍的道士。因此,对于同样与“诗歌”和“道教”有着不解之缘的李白,薛涛自然会倍感亲切与仰慕。在眼前景物的激发之下,在“诗”与“道”的激荡之中,李白骑鲸远去、把酒临风的潇洒形象使得薛涛的怀古幽情得到酣畅淋漓的抒发。而在《赋凌玉寺二首》中,薛涛笔下的凌玉寺的美景是“闻说凌云寺里花,飞空绕磴逐江斜。有时锁得嫦娥镜,镂出瑶台五色霞”。诗中提到的“瑶台”典出《穆天子传》。据记载,周穆王从“东土”经历至少上万里的行程抵达西王母的国度,与西王母在瑶台上宴饮对歌,西王母谓周天子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而周天子答:“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瑶台”(或瑶池)是道教中生育万物的创世女神西王母与诸位神仙歌舞宴乐的仙境。薛涛笔下的凌玉寺繁花似锦,枝叶和花影被月光投射在地面,就如同是在林间的石壁之上镂雕出了瑶台仙境一般。尽管在这首诗中,薛涛所记的凌玉寺是唐代开元初年建在今四川省乐山县东的一座佛教寺院,但是薛涛用典时却选用了道教中的著名神话。从这一点来看,道教对薛涛诗歌创作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除了酬赠诗和咏物诗之外,薛涛的抒情诗也喜用道教典故。比如,在《乡思》中,“峨嵋山下水如油,怜我心同不系舟”一句就化用了《庄子·列御寇》中的名句:“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薛涛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因为看到峨眉山下的岷江水,诗人就想象着可以乘船从岷江出发通往长江,然后越过三峡到达东部平原,再逆汉水而上,回到故乡长安。薛涛在诗中选用的“不系舟”这一典故一方面表达了她对漂泊无常的人生旅途的悲哀与自怜,一方面表达了她渴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心灵状态和欲以清虚淡泊和恬静旷达超越现实无奈的理想。在此诗中,庄子笔下的“不系舟”的外延在两个相反的方向得到延伸:一是生命的悲哀与无奈,一是超然淡泊的心态。这两种意蕴水乳交融,使得原本寻常的思乡主题得到扩展和升华。日本学者斋藤茂称赞此诗:“表达含蓄、富有理智”[15]86。
典故具有记载先贤圣迹的历史价值和作为例证指导实践的社会价值。随着文学的发展,典故被频繁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典故的运用不仅能济文辞之穷,还可济文气之不足。诗人们往往苦心孤诣地从古代典籍中刻意挑选或精心熔铸些许典故于作品中。因此,诗歌中的典故虽是只言片语,但却总是最能体现诗人内心深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薛涛诗歌中的典故涉及到大量的道教神话、人物和地点,这说明作为唐代乐伎的薛涛,在滚滚红尘中辗转飘零,但其内心真正向往的却是道教那超尘出世、清静无为的境界。
三、道教影响下的薛涛诗歌想象
薛涛的诗歌不仅以清奇而雅正的语言和丰富而纯熟的用典为妙,其浪漫瑰丽的想象也令后人称奇。作为在封建制度和父权社会中被损害和被压迫的弱女子,薛涛在当时能有如此不羁的想象力并且以诗文将之记载而流传千古实为不易。道教趣味和道教意象令她的诗歌摆脱性别带来的创作限制,而在唐代声名远播。据张篷舟先生考证,与薛涛唱和的,除了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六届镇帅外,还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王建、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僧广宣、韦正贯、萧祜、卢士玫、李程、张元夫、段成式等文坛名士、仕宦名流。只有姓氏、官衔或排行,现尚未知名字者,共有16人。此外,虽无姓氏、官衔或排行,但涛诗确为与人唱和者,亦有4首。[17]98在笔者看来,如此多的名人雅士愿与薛涛唱和的原因不仅仅是其诗歌“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更重要的是薛涛诗中反映出的思想情感能与之形成共鸣。明人胡震亨评价薛诗“无雌声”[18]70。当代学者赵松元认为薛涛诗歌颇具“丈夫气”[19]。而薛涛之所以能够突破性别带来的创作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思想中浓厚的道教底色。
在《寄词》中,薛涛用“菌阁芝楼杳霭中,霞开深见玉皇宫”把天上神仙的亭台楼阁想象成“菌”和“芝”的形状。在这句诗中薛涛明显地运用了互文见义的手法来描写楼台亭阁之貌。此处的“菌阁芝楼”并非以“菌”喻“阁”、以“芝”喻“楼”,而是将“楼阁”想象成为“菌芝”仙草。“菌芝”即灵芝。中国古代非常推崇和迷信灵芝。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里说:“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许种也。”“诸芝捣末,或化水服,令人轻身长生不老”。[20]196道教典籍总集《道藏》中收录的成书于隋唐年间的《太上灵宝芝草品》甚至记载了道教发展的一整套采集和服食灵芝的方法。由此可见,道教视野中的“菌芝”不仅仅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而且还被赋予或寄托了道教实现其“长生久视,羽化成仙”理想的重要作用。道教神话故事中的长寿女仙麻姑就是以灵芝酿酒为西王母祝寿。薛涛在此诗中以把眼中所见的亭台楼阁想象成为“菌芝”,这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二者在外形上具有相似性,更重要的是,薛涛受到了道教关于灵芝仙草的“前认识”所影响。这些影响构成了薛涛对眼前的楼阁的“前理解”或“前意识”。在她欲对眼前楼阁进行审美和阐释之际,这些深埋于其意识之中的道教意象便自发地进入其审美活动和阐释活动之中。因此,薛涛想象力的疆域不是寻常古代女子所熟悉的深宫宅院、闺阁绣楼,她的想象力所纵横驰骋的世界是一个因为道教信仰而丰盈起来的神仙世界。由于唐代大力提倡道教,甚至把《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等道教典籍列入科举考试内容。《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记载:“元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于京师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生徒有差,谓之‘道举’。举送、课试与明经同。”[21]8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薛涛富含道教想象的诗歌自然能引发更多当时深受道教影响的名人雅士的认可了。
在《金灯花》中,“细视欲将何物比,晓霞初叠赤城宫”一句将艳丽的金灯花比作聚集在“赤城宫”的彩霞。相传彭宗“年一百五十岁常如二十年少,周历王丙申太上遣仙官下迎为太清真人,治赤城宫。”[22]北周庾信有诗言:“仙童下赤城,仙酒饷王平。”[23]342初唐陈子昂有诗言:“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24]16从以上传说和诗文来看,“赤城宫”应该是道教理想中的神仙宫殿,象征着道教的最高理想。薛涛将“金灯花”比作道教仙宫周围聚集的彩云,从表层意义来看,是为了状金灯花之色貌;但从深层意义来看,她是借物抒情,托物言志。金灯花又名彼岸花、曼珠沙华、幽灵花、地狱花、无义花。因为其花色艳丽如血,且鳞茎有毒,故被视为不祥之花。薛涛欲以背负着不祥之名的金灯花来言说自己对道教理想的无限向往。身为官伎的她虽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身份所累,必须周旋于凡尘浊事之中,身负恶名。但是,志向高洁的她希望自己也能如金灯花一样,虽然声名不佳,但也心怀善念,一心向道,最终可以获得内心的空灵、清远与虚静。可见,道教不仅仅为诗人提供了非凡的想象空间,还给予了她直面人生的自信与坦荡的胸怀。
“道教文化对唐代诗人的出处行藏、功业观念、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熔铸了唐诗既注重功名又顺应自然的思想内容和既自由浪漫又淡泊超然的美学风范。”[25]76-81薛涛诗歌中的道教想象具备了达成其世俗目的与表达浪漫道教理想的双重功能。一方面,薛涛在诗歌创作中发挥的道教想象有助于她满足大众趣味、进行交际酬应;另一方面,她的道教想象有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奇效,插上道教想象之翼的薛涛诗在品格和意境上自然是别具一格。薛涛诗歌中的道教想象折射出来的是整个唐代信道知识阶层“既不禁欲,又要长生,既能享受人间欢乐,又能超凡脱俗,既快活,又高雅”[26]38的愿望。正是由于抓住了、融入了或者契合了这一共同愿望,薛涛才能以一介乐伎女子的身份在诗人辈出的唐代诗苑保有一席之地。
文学作品经典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官方与知识精英对作者或作品进行建构和塑造的结果。作为唐代乐伎身份的女诗人薛涛显然无法成为官方选择的经典化目标,然而从唐代以来,她的许多诗歌却在大浪淘沙般的经典化过程中流传了下来。根据张蓬舟统计,薛涛共留存诗作92首,是中国古代留存诗数量最多的女诗人。笔者认为薛涛诗能大量流传于世的重要原因在于知识精英与她形成的情感共鸣,而道教就是薛涛与知识精英形成情感共鸣的最重要的基石。无论从诗歌语言、诗歌典故,还是诗歌想象来看,薛涛的诗歌都因为其明显的道教特色而绽放异彩。道教因素不仅影响了薛涛诗歌创作,使其语言清奇雅正、典故新鲜蕴藉、想象超凡脱俗,道教思想还助推薛涛诗在经典化道路上突破封建社会阶级和性别的双重阻力,成为唐代首屈一指的著名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