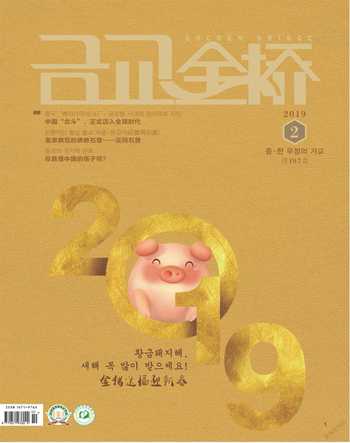匿名作家计划:一场大型“蒙面派对”
2016年年初,爆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换了笔名的J.K.罗琳(《哈利波特》作者)被出版社退稿,并被建议“参加写作课”。新闻引起深思:作家的名声对他的作品来说意味着什么?
2018年5月,创办10年的文学主题书系《鲤》,联合腾讯大家、理想国,举办了一场富有悬疑感和游戏精神的文学竞赛——“匿名作家计划”。
这是一场充满刺激、悬疑、火药味儿十足的文学比赛。没有题材的限制,没有年龄的苛求,参与者只需要遵从一项法则:去除名字,退居幕后,将作品全权交给读者审判。
一场神秘的文学“PK”
2018年6月初,“匿名作家计划”文学赛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发布会。近300位读者及观众到场。为了保持“匿名”的神秘感,主办方在每个座位上随机摆放了许多作家的面具,简·奥斯汀、阿特伍德、黑塞、波拉尼奥等都在其中,使这场发布会看起来更像是大型读者“蒙面派对”。
发布会上,作家梁文道、路内、张悦然及腾讯大家的副总编辑杨瑞春,共同探讨了文学的匿名与风格。其中提到“匿名作家计划”参赛者中既有中国顶级作家,也有年轻的文学新人,旨在打造一场优秀小说家之间的文学“PK”。
事实上,“PK”已成现代人的本能。“匿名作家计划”有趣,在于它既顺从了人们的本能,又保留了足够的空间——标准更开放,节奏更宽松,评判更多元。“匿名作家计划”自2018年底正式启动以来,以每期“7位匿名作家+1位踢馆作家”的方式,将35篇优秀的匿名小说在网络公开,交予读者评判。同时每期作品以匿名的方式,交给化名为“韦小宝”“唐璜”等文学人物的评委,最后经过终评评审团,在全程直播模式下评选出决赛作品。
其实,当代作家大多是通过“PK”成长起来的,只有经过杂志社或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们的筛选,作品才能与读者见面。只是在过去,这一“PK”过程不对外公开,更易落入“一言堂”现象。“匿名作家计划”则相当于将传统文学编辑的筛选过程公开化,增加决策透明度。
去除文学的势利与偏见
在人人能直播的年代,通过新媒体的多种通道,年轻的作者有很多发声方式,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能被更多地看到?
“匿名作家计划”中,11位作家入围,入围作品均属精品,收获了不少读者的好评。
然而,捧得首奖的郑执却是一位文学圈里的“陌生人”。他出生于沈陽,19岁离开家乡做了10年的港漂,两年前才来到北京。在上台揭面领奖时,郑执坦言自己“十分紧张”。他讲到自己曾一度为生计而放弃了严肃文学的道路,非常感谢“匿名作家计划”为他提供了被读者看见的可能性,“以前我没有机会踏入严肃文学的文坛,也没有在知名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所以这几乎算是我的第一次。很多成名作家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重新认识自己,但我就是单纯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认识一下。”
《鲤》的主编、也是此次“匿名作家计划”活动的发起人张悦然曾谈到匿名的初衷,“它应该来源于我的一种困惑。作为一个作家,我常常在想我的名字和我所写的东西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张悦然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热爱名人,热爱那些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名字,即便是《鲤》这样受众并不十分广泛的文学杂志,也会邀请很多名人写稿。因此我跟朋友们决定,隐去所有名字,只看文字本身,只依靠文字决定作者的价值。”
知名学者止庵也表示,对于一部纯粹的作品,创作者的名字其实并不重要,阅读就应该把所有作者都当作新人,书都当作是新书。人都“势利眼”,匿名可以把“势利眼”去掉,也可以克服像是自己仰慕的对象、熟人等影响评判公正的部分。
是城墙亦是武器
其实成名作家大多都有固定的风格,就像每个人的嗓音都有辨识度,很容易被辨别出来。然而此次“匿名作家计划”中却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事。
匿名作家031号的作品《卜马尾》因情感细腻,曾被认定出自某位年轻女作家之手。当主持人揭晓该小说作者为著名男作家马伯庸时,现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此外,还有几篇也出现误断的情况,评委甚至打趣说应该得一个“最佳化装奖”。
“已成名的作家既受惠又受制于自己的名字,几乎不会面临被退稿的尴尬,但也难以逃离‘定型’的公众成见。”张悦然在与作者们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许多人很希望隐去原来的风格,换一副不被人认出的面孔来进行全新的写作尝试。
“匿名作家计划”开始之前,曾有很多人认为,这对于成名作家而言,是一次对权威的挑战和冒犯。他们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声名,可能会遭到批评、质疑。可也忽略了他们多年来的为声名所累。
而此次匿名形式恰好为这些作家提供了一个陌生的战场,在这里他们戴上面具,试图开拓新的写作疆域。就像《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意大利匿名作家埃菜娜·费兰特曾所说:匿名为读者提供了谈论纯粹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同时,名字与作品的分离也为写作者提供了超越自身边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