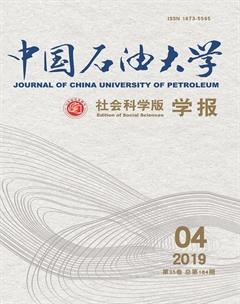《地下铁道》中的异托邦建构
左金梅 周馨蕾
摘要:异托邦是福柯基于对边缘空间和边缘人群的关注而建构的空间哲学,是社会机制内真实存在的局部化场所,以独特的视角窥探整体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理念。美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在最新作品《地下铁道》中,通过女主人公黑奴科拉的逃亡历程交错建构了三类功能迥异的异托邦:偏离异托邦中所谓的主流标准揭露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森严的权力等级制度,兼具补偿性与易碎性的幻觉异托邦深刻剖析了人性的复杂与隐秘,保护弱势群体的危机异托邦则展现出超越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怀特黑德在小说中对上述三类异托邦的精妙建构客观反映了美国黑人荆棘丛生的艰难处境,表现出黑人为生存所付出的令人动容的努力,让人们再次直视与反思那段被刻意淡化的黑暗历史,显示出一位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度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福柯;偏离异托邦;幻觉异托邦;危机异托邦;边缘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4-0077-08
美国新贵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以下简称怀特黑德)构思长达16年之久的最新作品《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年一经出版,便荣获“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17年普利策小说奖”,小说讲述了生而为奴的少女科拉(Cora)在南方种植园受到种种欺辱之后,下定决心开始反抗,通过隐秘的地下铁道一路向北逃亡,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获得自由,实现了自我拯救的故事。“地下铁道”原本是喻指在美国废奴运动时期帮助黑奴从南方蓄奴州逃跑至北方自由州和加拿大的秘密网络路线。怀特黑德在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创造性地将其具象化,变为真实存在的地下铁路系统,为小说平添了几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并借此描写了女主人公科拉在美国不同地区的生存状况,揭开了白人遮盖在黑人血与泪历史之上的资本主义的温情面纱。
目前,鲜有关于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本文拟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下简称福柯)的异托邦理论解读《地下铁道》中黑人所处的边缘空间。异托邦是社会机制内真实存在的局部化的空间场所,凭借特有的边缘视角,具有反映全局的功能,可以窥见其他常规空间内部的隐蔽的权力关系与文化理念。福柯认为异托邦至少有6种类型,《地下铁道》中的异托邦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偏离异托邦是指偏离了“标准行为”的人群的生存空间,但所谓的标准则是由主流存在全权掌控,而以科拉为代表的黑人群体彻底丧失了话语权,小说中的种植园、博物馆和监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边缘人群被排斥和压迫的痛苦;幻觉异托邦是边缘人群所向往的理想空间在现实世界的折射,兼具补偿性与易碎性双重特质,作者为科拉建构了三次幻觉异托邦,分别是南卡罗来纳州看似和谐平静的生活、北卡罗来纳州的阁楼和印第安纳的瓦伦丁农场,这些作为她逃亡之旅的缓冲期,既为主人公提供了继续前行的希望与动力,又使她在幻觉异托邦破碎时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与复杂的人性;危机异托邦是为处于危机状态的弱势人群而设置的庇护所,在科拉的逃亡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开始在佐治亚州的伶仃屋和小菜园,后来是每一次乘坐的地下铁道,以及最终目的地北方,3处危机异托邦为科拉所提供的保护让她看到善良的火种未曾熄灭,其光芒仍在闪耀。怀特黑德通过对《地下铁道》中异托邦的建构重现了19世纪美国黑人所遭受的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表达了作者对以黑人为代表的边缘人群的关注,对美国至今依然存在的种族主义的担忧,同样也体现出他对彻底消除种族歧视的迫切渴求,对真正实现种族平等与民族融合的憧憬。
一、偏离异托邦:权力话语的等级制度
福柯认为偏离异托邦本身是一个被隔离的封闭空间,“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1]55,但所谓的“标准行为”则是由主流人群制定,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只能被动服从,从而形成了严格的权力等级制度。《地下铁道》全方位展现了权力等级的明确划分,在佐治亚州的兰尔德种植园、南卡罗来纳州的博物馆和田纳西州的监狱里,种族主义的阴影无处不在,白人是统治阶级,黑人是被统治阶级。
怀特黑德通过科拉的双眼,给读者展现的第一个偏离异托邦就是美国南方蓄奴州佐治亚的兰尔德种植园,奴隶主制定了全部的规则,或者说奴隶主就是规则本身,一旦有黑奴违反规则或者让奴隶主感到不满,那么惩罚就随即而至。兰尔德种植园有一个可以背诵《独立宣言》的黑奴迈克尔,如果奴隶主有兴致,会在见客时特意把他叫出来表演,博宾客一乐,但是当奴隶主厌烦时,便开始对他施加酷刑,折磨致死。在偏离异托邦中,黑人的身体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2]155,黑奴的生命在掌权者眼中一文不值,怀特黑德冷静地描绘着地狱般的图景。
在偏离异托邦中,有时甚至都不需要白人监管,黑人也会自觉服从,这种驯服是经由权力的内在转化使其自动施加到黑人身上的。兰尔德种植园每年也会有一两天是属于黑人奴隶的节日,那就是乔基的生日。生日对于黑奴来说,完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乔基已经50多岁了,一个黑奴能活到这个岁数,绝对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他每年都会过一两次生日,其实是他随意定的日子,黑奴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聚会。虽然他们在这一天依然需要上工,但是可以期待一个温暖的夜晚,可以奏乐,可以跳舞,在永远为奴的状态下,只有这短暂的一刻,似乎才算是真正的人,与非人的日常隔开。兰尔德老爷子对乔基的生日宴没说什么,他的大儿子詹姆斯接手种植园之后,对此也没有过问,于是这个传统就被保留下来了。白人奴隶主清楚地知道“一点小小的自由是最毒的惩罚,可以将真正自由的丰盛表現为饮鸩止渴的慰藉”[3]30。宴会开始之后,大家载歌载舞,每个人都会带来一点儿食物,小孩子们还有各式各样的比赛,然而兰尔德兄弟的突然出现,结束了这一切,黑奴们自觉朝两边散开。虽然奴隶主发出号令,让他们继续奏乐跳舞,奴隶们就仍然奏乐跳舞,但氛围已与刚才截然不同。众人围成圆圈,每转一次都要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一下兰尔德兄弟的反应,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举动恰恰印证了偏离异托邦中权力的规训作用。
黑奴在兰尔德种植园不断被压榨,在边缘空间挣扎着讨生活,无论他们的言行多么谨慎,一旦不符合白人奴隶主的意愿或心情,就会受到处罚。“人是由许许多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则、准则和规范塑造而成的。”[4]因此偏离异托邦已经形成一种可怖的权力效应,并且愈加稳定持久,奴隶主无需动手对黑奴的肉体诉诸暴力,一个眼神就可以对黑奴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将“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2]227,种族之间的权力等级早已内化到人们的内心深处,难以消除。虽然科拉逃离了佐治亚的兰尔德种植园,她却逐渐发现自己始终无法摆脱偏离异托邦的梦魇。
南卡罗来纳州的自然奇观博物馆是另一个偏离异托邦,“博物馆是19世纪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异托邦”[1]56,而且博物馆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1]55,在一个空间场所中,各个不同年代的展品所包含的时间年轮可以无限积累,从而起到教育大众的作用。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更需要博物馆来展示不同的文化,原本实事求是地摆出真相就是博物馆的标准,也是它的职责所在,但是因为博物馆被白人控制在权力之下,所以发生了本质性的偏离。
科拉在博物馆的3个展厅上班,当模特进行表演。第一个展厅是“非洲腹地即景”,一座茅屋占据了展览最显眼的位置;第二个展厅是“运奴船上的生活”,内墙被涂成了漂亮的蓝色,再现了大西洋上的天空,科拉登上甲板,穿着水手的衣服,脚上蹬着皮靴;第三个展厅是“种植园典型的一天”,科拉只需坐在纺车前踩几下,然后做几下朝小鸡模型撒种子的动作。科拉没有在非洲和船上的经历,但是她在种植园的亲身经历可以让她明确指出第3个展厅的错误之处,其不准确、和现实不一致的地方实在太多。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博物馆负责人菲尔茨先生时,他避重就轻,以展厅空间有限为托词,拒绝修改。事实上,被贩卖的黑奴根本没有机会站在运奴船的甲板上去瞭望蓝天,他们基本衣不蔽体,全部挤在幽暗潮湿的船舱之内,持续了几百年的奴隶贸易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重要引擎”[5],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在种植园里,很少有奴隶可以如此幸运地去干纺织这种轻松的工作。黑奴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不是展厅玻璃另一面的白人愿意看到或者愿意听到的,因此由白人布置设计的3个展厅重在强调异位的象征性与模拟性,它们“构成有效的象征符号系统,重构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对象化过程”[6]137,间接说明拥有权力的白人潜意识里不愿意去面对自己所缔造的如此不堪的历史真相。“真相就是商店橱窗里不断变换的展品,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任人摆弄,看上去很美,可你永远够不到”[3]132,在博物馆里,主动违背“真实”这一基本原则的是白人,但是他们却不会受到丝毫惩罚,只因他们是权力的拥有者,获得了绝对话语权,博物馆变为了“胜利者的意志、力量和话语,因为‘谁在说决定了‘说什么”[7]134。
白人一直为自己在北美大陆的身份建构而不断努力,但是为了强化身份,白人将黑人等有色人种看作“他者”,放在对立面,从而出现了“以牺牲‘他者来获得自我身份的确定的现象”[8]。怀特黑德在采访中谈道:奴隶制度离我们并不遥远,其余波仍在,时至今日都会受到它的影响。由南卡罗来纳州博物馆所建构的偏离异托邦再一次论证了美国隐性的权力话语等级制度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监狱作为偏离异托邦的主要形式之一,构成了文化和权力的重要空间,也正是“由于监狱,人们揭开了政治秩序的背面”[9]。科拉虽然没有进过真的监狱,但是她被里奇韦抓住之后,在田纳西州的经历可以称之为监狱生活的另一种变形。科拉被锁在移动的囚车上,手腕和脚踝都戴着镣铐,并且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她在火灾后的满目灰烬和疫病的重重包围下走过了末日般的田纳西。里奇韦虽然是一个残忍的猎奴者,却维护着监狱的井然有序,并且十分重视犯人的待遇,从他入行以来,就一直允许他的囚徒得到均等的一份食物,此外,还有专人记录,把逮捕押送的黑人一一记在本子上,甚至还包括账目往来、市井闲话和天气状况等,从一定程度上变相实现了监狱的改革。
在这部以奴隶制为题材的小说中,里奇韦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以反派形象出场,但怀特黑德是一位老到娴熟的作家,不可能单纯塑造这种非白即黑的单薄角色,在“田纳西”这一章节中,作家只运用了一个往事片段就使这个人物形象立即丰满起来。里奇韦虽然是有名的猎奴者,但是他完全没有自己的奴隶。帮助里奇韦驾车的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霍默,只有他曾在里奇韦名下当过14个小时的奴隶。当年里奇韦看见霍默那双明亮的眼睛,动了恻隐之心,花了5美元将他买下,并在第二天写了解放证书放他走,还他自由。哪怕是狠毒如里奇韦,内心也会有柔软的一部分。霍默却没有离开,而是选择继续跟在里奇韦身边,这一选择出乎读者的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霍默见过太多黑人的悲惨遭遇,他的母亲已经被卖掉了,他没有未来,肯定还会有人把他抓住,然后转手卖掉。跟着里奇韦,还能识字,见世面,这无疑是霍默最好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管有无解放证书,黑人都是被禁止自由和被排斥的对象,属于不正常的异类,这取决于“一种暂时的文化标准”[6]134,从而建构了偏离异托邦。
偏离异托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而是与一系列的意识、政治、经济、文明等社会形态息息相关,由是导致了话语权力的等级制度。佐治亚的兰尔德种植园,标准行为等同于白人奴隶主的个人主观意愿,文明秩序重新倒退至原始社会时期;南卡罗来纳州的博物馆进一步体现了白人对权力的滥用,掩藏事实真相,但是處于底层的黑人根本无计可施,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边缘人群;田纳西州的移动监狱使科拉彻底失去了自由,美国白人阶级一直以来宣扬的“平等”一词充斥着谎言与假象。如果让科拉一直身陷偏离异托邦,那么对于一个16岁左右的花季少女而言,生活的负担和生存的压力实在太过沉重,所以怀特黑德也为她建构了幻觉异托邦,让科拉在黑暗漫长的逃亡之路上略有喘息的机会,并给予她始终奋力前行的希望与动力。
二、幻觉异托邦:短暂的美梦
福柯认为异托邦具有创造幻觉空间的作用,幻觉空间反而能够揭示最为真实的空间,“这个作用发挥于两个极端之间”[1]57,幻觉异托邦可以创造另一个几近完美的空间,但这并不是乌托邦,而是投射出的一个理想空间,继而在他处实现,对所在现实进行补偿。怀特黑德在小说中为科拉建构了3个幻觉异托邦:南卡罗来纳州表面的和平共处、北卡罗来纳州的狭窄阁楼和印第安纳州的瓦伦丁农场,都分别为她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以帮助她不被无休止的苦难压垮,同时也使她更加认清了美国种族主义泛滥所导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个幻觉异托邦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科拉乘坐地下铁道成功地从佐治亚州逃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改名换姓,变更身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南卡罗来纳虽然也属于南方蓄奴州,但是相对其他州而言,这里对黑人的态度更为包容。科拉现在叫作“贝茜·卡彭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安德森家当保姆。科拉喜欢在下班之后走回宿舍,因为她喜欢感受这座城市入夜之后的活力,喜欢观赏百货店摆出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她甚至自己攒钱去格里芬大楼买了一条蓝裙子。科拉的住处是一个拥有80个床位的大寝室,“这是她从小到大睡过的最软和的床了。不过话说回来,她从小到大只睡过这一张床”[3]107,且周六可以睡个懒觉,这是她以前在种植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南卡罗来纳州还看重有色人种教育,帮助他们进步,以前科拉目不识丁,现在她能去学校上课学习。此外,她还可以去医院体检,去洗澡,去参加联欢会。在科拉眼中,南卡罗来纳州所呈现的幻觉异托邦与佐治亚州残忍血腥的兰尔德种植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就是她梦想中的家园,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她对于是否继续北上显得格外犹豫。
但让科拉满足的南卡罗来纳州背后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黑人仍旧是社会空间中的末等公民。在有色人大卖场里,同样商品的价格是白人商店里的两三倍,白人所表现出来的仁慈友善只是一种迷惑双眼的虚幻假象。白人利用黑人进行梅毒实验,在白人眼中,黑人的价值只有在这时才能得以体现;欺骗黑人女性去做绝育手术,从根源上对黑人的人口数量进行控制,甚至是消灭。白人一开始提供的种种福利实际上都是幌子,“这个社会空间象征着伪善的生机和虚无的种族平等希望”[10],白人从骨子里认定黑人是劣等的种族,不该存活于世。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方式,科拉逐渐认清真相,南卡罗来纳州的幻觉异托邦“向所有的人开放,以使人能够感受到自身得以进入的实在性,但同时又使人明确感受到‘自身并‘不属于这一空间”[11],它虽然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却并不接纳全部,黑人从来都不在这个空间的规划范围之内。科拉的清醒终归迟了一步,猎奴者里奇韦发现了她和她的黑人朋友西泽,虽然她幸运逃脱,但西泽却被杀害,南卡罗来纳州的幻觉异托邦成为了西泽等众多黑人的坟墓。
第二个幻觉异托邦则建构于科拉逃到北卡罗来纳州之后,她得到了白人马丁·维尔斯的帮助,躲到他家假屋顶上的逼仄密室里,“这里从地板向上逐渐变窄,高不足一米,长也仅有四米五”[3]173,墙上仅有的小孔是光和空气的唯一来源。北卡罗来纳州对黑人的排斥达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甚至对保护黑人的白人也会杀害,因为他们发现黑人这一边缘群体在日益庞大。造成白人焦虑的重要原因,更多的是生存空间问题,对白人而言,减少黑人的数量,他们自然就能获得更多的空间。另外,一旦黑人摆脱枷锁,追求自由,甚至有可能还要复仇,白人自身的处境就会变得危险,所以他们势必把黑人一网打尽。科拉透过墙上的小孔,可以看见对面的公园,公园在每个星期五的夜晚表演抓捕黑奴的情景剧,如果那天巡逻队真的抓到了黑人,就会借此机会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具有一种政治功能,它“虽然是一种匆促而普遍的形式,但也属于变现权力失而复得的重大仪式之列”[2]53,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白人无坚不摧的力量,把种族之间的悬殊发挥到极致,以强调权力的固有优势。很长一段时间内,科拉只能蜷缩在暗无天日的阁楼上,必须一动不动,因为最轻微的动作也会使年久失修的地板发出巨大的声响,如果让保姆菲奥娜发现并举报,不光她会被逮捕,帮助她的白人马丁·维尔斯一家也会受到牵连被绞死。
在科拉遭遇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双重折磨时,怀特黑德再次替她建构了一个幻觉异托邦作为补偿和调剂,“也就是说这个极端的异位功能要造成我们不在真实世界的幻觉,我们或许在极乐世界或许在其他世界”[6]143。在阁楼上最开始的几个星期,科拉开始幻想,幻想自己已经到达北方,有一个明亮干净的家,房屋设计很有品位,她似乎看见了丈夫的身影,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邻里之间也非常和睦。而这种非常普通平静的家庭生活,却只能出现在科拉的幻想之中,此处的幻觉异托邦可以使她暂时忘记伤痛,“通过反映理想而呈现现实秩序的不完美”[6]145。再美的幻觉异托邦也终有醒来的一日,巨大的落差将科拉的现实反衬得格外悲凉。幻觉异托邦就像是一面鏡子,“在镜子中,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那里却没有我,在一个事实展现于外表后面的不真实的空间中”[1]54,科拉所幻想的未来,恰恰是她的潜意识的投射,从而形成可以给她安慰的幻觉异托邦。
最终保姆还是向抓捕黑奴的黑夜骑士举报了阁楼的异常情况,科拉被猎奴者里奇韦带走,帮助她的马丁·维尔斯和他的夫人埃塞尔被杀害。怀特黑德通过科拉的一站站冒险,“把小说本身当做历史谱系的延展”[12],在读者眼前有血有肉地复原那个暴虐与博爱同样令人震惊的时代。怀特黑德是一位既温情又理性的作家,他在《地下铁道》的整个故事中,全程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客观叙述故事走向,鲜有主观评价。但是当科拉面对无边黑暗时,他会特意为她创造一个可以疗伤的幻觉异托邦,作者虽在故事之外,却也用自己的方式为主人公伸出援手。除此之外,科拉这次短暂的幻觉异托邦也为后文做了铺垫,因为结局她确实成功逃到了北方,但她是否在北方过上了她向往的生活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悬念给读者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怀特黑德在小说一半处就埋下伏笔,足以彰显其精巧的行文构思与叙事策略。关于科拉在阁楼上的情节,怀特黑德化用了哈丽雅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的自传小说《女奴生平》(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同样是在美国蓄奴时期,女主人公为了摆脱奴隶的命运,在外祖母家狭促幽闭的阁楼中躲避了7年之久。为了获得自由,位于边缘地带的黑人总是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努力。
第三个幻觉异托邦在印第安纳州,这是最为精彩也最为遗憾的一个异托邦。科拉在北卡罗来纳州被里奇韦抓住,后来在田纳西州遇到善良的自由民黑人罗亚尔等人,将她解救出来,随后一行人乘坐地下铁道前往印第安纳州的瓦伦丁农场。这里的幻觉异托邦与南卡罗来纳州的幻觉异托邦有诸多异同点。在这里她又可以上课了,还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新书,但这次她变成了班里的落后生;她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无需挤在80人的大寝室了;她下地干活,这是她最为熟悉的工作,干起来得心应手,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人拿鞭子抽她了;这里还有一座图书馆,黑人也可以进去阅读……而且,她认识了一群人,例如瓦伦丁和蓝德,他们本身就是自由民,生活条件优越,受过高等教育,言谈举止中处处体现着上流社会的修养,他们本可以自由自在地幸福一生,但却为了废奴运动而到处奔走,为了给黑人一个家而不断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从不在意个人得失,真正让他们放在心上的是所有黑人的共同利益和命运。通过与他们交谈或听他们讲话,科拉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他们是科拉精神层面的启蒙老师,启蒙的目的是追求自由与解放,应被“看作人本身就该有的一种权力,一个过程”[13]259,这是她第一次体验这种权力。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博爱的精神和坚定的志向教给科拉最珍贵的一课——黑人的崛起只能依靠自己。
富足的瓦伦丁农场是一个奇迹,无数逃亡的黑人在这里歇脚,然后继续上路,或者直接选择在这里定居,“这里因此成为了有色人进步的象征——也成了众矢之的”[3]278。尽管印第安纳也是蓄奴州,但这一次科拉是真的不想再逃亡了。怀特黑德既然把瓦伦丁农场建构为幻觉异托邦,就暗示其终有破碎的一天。瓦伦丁农场的最后一次大会是在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召开的,这一天是瓦伦丁农场的末日。蓝德的原型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子弹同样击中了正在演讲的蓝德的胸口,“接着是来复枪射击、尖叫和玻璃碎裂汇成的大合唱,一种疯狂的混乱席卷了礼拜堂”[3]322,科拉的恋人罗亚尔也被杀死,整个瓦伦丁农场都笼罩在火光之中,白人开始了他们的恣意狂欢——大屠杀,他们丑恶的脸上充盈着喜悦,白人意图毁灭黑人的一切,他们的疯癫行径却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次大屠杀是“用错误来掩护真理的秘密活动”[14]。科拉万念俱灰,至此,第三个幻觉异托邦也彻底崩塌。
如果瓦伦丁是白色人种,他的农场又如此成功,那么这是他自己努力奋斗的成果,即使其他白人会嫉妒,也只会暗地里使坏,但绝不敢明火执仗,因为美国法律是保护白人的。但是瓦伦丁有非洲血统,尽管他的肤色非常浅,这在刚开始为他创建农场时提供了诸多便利,可时间一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其实是有色人种,种族歧视早就融入了白人的血液,他们认为愚笨的下等黑人不配拥有这样的财产,便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作者犀利地“揭示了美国建国以来种族问题的‘旧伤”[15],“美国梦”向来是世世代代美国人的人生信条,激励着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到这片土地,但种种事实却告诉人们,大肆宣扬的“美国梦”却不能摆脱种族主义的阴影,所谓的公平只存在于幻觉异托邦,现实空间的公平不过是一句空谈而已。
幻觉异托邦是短暂美梦的化身,只是科拉逃亡路上的供给站:南卡罗来纳州处处都是虚伪的善意,“暴力开始变得温柔,肉体控制偏向于灵魂掌控”[13]V,让黑人身陷牢笼却浑然不觉;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逼仄阁楼里,科拉展开了自己最美好的幻想,也正是这份幻想给予她继续前行的动力,在黑暗中不断坚持;印第安纳州的瓦伦丁农场则完成了对科拉的心灵启迪,她的精神世界正在初步建构,科拉所追求的自由不应仅局限在身体层面,更应该是精神的自由,二者兼备,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这也是她逃亡的最终目的。3处幻觉异托邦使科拉认清了美国种族主义的严峻形势,帮助她进一步成长,找到属于自己的庇护所——危机异托邦。
三、危机异托邦:安全的庇护所
危机异托邦是为处于危机状态的弱势人群所提供的特定边缘空间,起到保护作用。尽管《地下铁道》的题材十分沉重,主人公科拉的坎坷遭遇令人唏嘘不已,但从最初的伶仃屋与小菜园,到后来乘坐的地下铁道,以及最终的北方,3个危机异托邦都为科拉撑起了保护伞,在她最为无助的时候,给予她慰藉与温暖。
在《地下铁道》的开始,科拉生活在南方佐治亚州的兰尔德种植园,在这里科拉遭受了无数残酷的鞭打,而伶仃屋和小菜园分别是她身体和精神的危机异托邦。科拉生而为奴,当她的母亲梅布尔逃出种植园之后,科拉便举目无亲,失去了所有保护,只能独自一人在种植园里小心谨慎地讨生活。同为最底层人群的其他黑奴并没有给予这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足够的关怀,恰恰相反,人们看到她现在孤苦无依,便开始贪婪地盘算她那为数不多的“家产”,第一步就是把科拉撵到伶仃屋,霸占她之前的住处。伶仃屋是属于落难者的家园,只有那些被奴隶主打断骨头或者殴打致精神失常,无法继续从事劳动生产、失去利用价值的黑奴才会被驱逐到伶仃屋自生自灭。遗憾的是位于边缘空间的黑奴没有团结在一起,而是自相残杀,把边缘空间进一步划分为主边缘空间和次边缘空间,伶仃屋自然就属于次边缘空间。
当她的好友切斯特因不小心撞到白人奴隶主特伦斯而遭到毒打时,只有科拉勇敢地冲出去,扑到男孩身上,做了肉盾。科拉从小在残暴的环境中成长,了解人性的卑劣,怀特黑德透过她的眼睛去看复杂而丑恶的世界,但绝不让她同流合污,科拉人性中的善良因子
一直存在。在科拉受傷之后,是伶仃屋的女人在照顾她,给她准备食物,用盐水给她的伤口消毒,把湿布放到她的额头上帮她退烧。这些人之前与科拉的母亲从来不曾亲近,但依然出手相助;相反,之前受到过科拉母亲恩惠的人,却冷眼旁观,甚至落井下石。处于次边缘空间的人群相互照顾,彼此依靠,构成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异托邦,从而起到真正的庇护作用。
伶仃屋是保护科拉身体的危机异托邦,而让科拉精神世界有所寄托的危机异托邦则是小菜园。这个小菜园不足3平方米,但每个星期科拉都会花几个小时打理小菜园,这段时间是属于她自己的,精神状态可以放松。这块小菜园是科拉的外婆阿贾里凭借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开垦出来的,死后留给了科拉的母亲梅布尔,在梅布尔走后,这块土地自然就属于科拉,象征着祖孙三代的传承,更是只属于科拉一人的危机异托邦,在这里她总是格外安心,因此对小菜园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当科拉的小菜园被新来的6个黑奴壮汉强占并改成狗屋时,她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反击,她从伶仃屋的墙上取下一把斧头,迎着所有人诧异的目光,果断地举起斧头砍碎了狗屋,夺回了自己的小菜园。科拉为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异托邦而斗争的举动,体现出她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关心,而且她并没有把这种关心“简化为一种静止状态——不管是一种情感状态还是一种理智态度,它是一种具体行为”[16],这正是她与其他黑奴最不同的一点,恰恰因为如此,她才敢于迈出逃亡的第一步,付诸行动,并不断成长,思想上愈加成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伶仃屋和小菜园共同构成了科拉在兰尔德种植园时期的危机异托邦,保护着她的身体和精神,为她的逃亡之旅奠定了基础,是最初的起点。
第二个层面的危机异托邦是贯穿整部作品的重要线索,也是科拉的逃亡途径:地下铁道。这条铁道处于一种非常隐秘的状态,用以庇护帮助黑奴逃出种植园,前往北方的自由州。科拉一共坐过4次地下铁道,怀特黑德每次都对地下铁道的外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科拉第一次乘火车是和西泽一起,两人得到了白人弗莱彻和伦布利的帮助,一起从佐治亚州逃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地下铁道的月台有6米高,难以想象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花费了多少时间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全靠双手修出了这样一条逃生的铁路。所谓的火车也就是“机车只拉了一节车厢,这是一节破烂不堪的火车车厢,厢壁上好多木板都不见了”[3]78,当火车开动起来之后,车厢都要晃散架了。科拉正是依靠這列异常简陋的火车迈出了自己逃亡之旅的第一步。第二次乘坐地下铁道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从南卡罗来纳州逃往北卡罗来纳州。这里的火车设备更加寒酸,“底部的木板用铆钉固定在车厢底盘上,没有厢壁,也没有顶”[3]165。第三次科拉和救她的罗亚尔等4人一起乘坐地下铁道,铁道位于田纳西州的一座马厩的下方,车站的墙壁上贴着白色瓷砖,挂着油画,月台的桌子上摆着鲜花,“这是迄今最华丽的机车,即使透过包覆的煤灰,闪亮的红色油漆仍然反射着灯光”[3]293,火车是一节设施齐全的旅客车厢,里面有30个座位,宽敞舒适。第四次乘坐地下铁道是科拉独自一人,这条秘密的铁道在印第安纳州的一幢荒草丛生的废弃小屋下面,“这是迄今为止最破烂、最凄惨的车站。铁道与地面齐平,一下台阶就是铁轨,一路深入黑暗的隧道。一辆小手摇车停在铁轨上”[3]287,而且只能开出几英里,因为隧道越往深处越窄,墙几乎都挨在一起,剩下的路就只能依靠步行。科拉走到筋疲力尽时,就直接躺在轨道上睡觉,醒来就继续奋力前行,锲而不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平安出去,直到她看见了一个针眼大小的亮光。
怀特黑德把这4处地下铁道建构为一个统一的危机异托邦,可以“被说成是一个空间的关系网”[17],而且总是“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得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1]56,地下铁道是用鲜血与汗水打造出来的奇迹,专门为黑奴而建,为这类边缘人群的出逃提供了保护与机会。由地下铁道所建构的危机异托邦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虽然身处黑暗的地下,但却是光明的化身,给人带来无尽的希望,“在这一头,是走入地下之前的你,到了另一头,就是爬出来迈进阳光里的信任了”[3]240。“地下铁道”本身是一个极具时代感的陌生化名词,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但是怀特黑德凭借自己奇诡却不失真实的想象和让人身临其境的细节描绘,在书中对其进行了完整性的塑造,使之变为了危机异托邦空间,“这些真实的空间场所是嵌入和写入社会体制内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在社会机制内被认可的现实场所”[7]132,同样使得它们所代表的理想或文化理念,即废除奴隶制、解放黑人、还其自由,变为一种现实,只有融入社会体系之中,才有可能逐渐被接受或认可。
第三个层面的危机异托邦是科拉逃亡之旅的终点——北方。在《地下铁道》中,北方被多次提及,科拉最初逃亡的目的地就是北方自由州,怀特黑德把小说的最后一章直接命名为“北方”,虽然着墨不多,只有薄薄的6页,但足以建构一个宏观层面的危机异托邦,让人们看到善良的光芒从未熄灭,以黑人为代表的边缘存在终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北方的自由州里,黑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挨打,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因此北方成为了所有南方蓄奴州黑人的梦想,是他们安全的栖息之地,边缘人群可以受到保护。在小说的最后,科拉推开刺藤,走出了隐藏在灌木和葡萄树下的洞口,重新看到了太阳。有三辆马车从她面前经过,驾车的分别是白人、爱尔兰人和黑人,作者在此处的安排设计暗喻了民族的融合。白人对科拉置若罔闻,爱尔兰人对科拉伸出援手却遭到拒绝,科拉最终选择了那辆黑人驾驶的马车,这3种情况表明了种族主义虽然依旧存在,但是正在逐步消融,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作者内心深处的期许。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科尔森·怀特黑德独辟蹊径地在《地下铁道》中建构了3类功能迥异的异托邦并由科拉的逃亡之旅串联起来,从而使读者重新审视种族主义带给黑奴的难以愈合的创伤。偏离异托邦中的权力等级制度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最丑陋的一面,南方的种植园是所有黑奴摆脱不掉的噩梦,本应展示真相的博物馆由掌控着话语权的白人随意更改,监狱更是体现白人权力的空间,矛盾性与排他性是偏离异托邦与生俱来的属性,其中的标准只取决于主流人群,有色人种只能被动服从。幻觉异托邦相当于一个加油站,为悲惨的黑奴编织一个短暂的美梦,让他们稍作休整,南卡罗来纳州对黑人表演的虚情假意让科拉认清了现实,科拉在北卡罗来纳州阁楼上对未来的幻想让她有了再次前行的动力,印第安纳州的瓦伦丁农场让科拉得到了心灵的启迪,思想上的教诲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但是幻觉异托邦的纷纷坍塌,恰恰是对“美国梦”价值观的嘲讽耻笑,奴隶制的邪恶已经渗透到土壤之中,《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豪言壮语也只是停留在纸张之上。危机异托邦才是其庇护所、最终的归宿,保护着弱小的边缘人群,伶仃屋和小菜园分别庇佑着科拉的肉体与灵魂,纵横交错的地下铁道为黑奴的逃亡提供了机会,北方的自由州则是所有黑奴的追求目标,危机异托邦是用无数反对黑人奴隶制的勇士的鲜血浇筑而成的,他们理解平等的真正内涵,并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种族歧视至今犹在,所以怀特黑德坚持这个永不过时的题材,担负起一名有良知的作家应尽的责任,希望异托邦可以消失,黑人不再被边缘化,从而实现种族之间的融合共存。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
[2]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M].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4]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7.
[5] Walker, Barrington. Exhuming the Archive: Black 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Maritimes and Beyond [J]. Journal of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Region,2017, 46 (2): 196.
[6] 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 張锦.“命名、表征与抗议”——论福柯的“异托邦”和“文学异托邦”[J].外国文学,2018(1).
[8] 孙燕.人性·镜像:对《地下铁路》超越种族问题的解读[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2):79.
[9] 阿兰·布洛萨.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J].汤明洁,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5):161.
[10] 承华.怀特黑德的历史书写及其叙事策略——评《地下铁道》[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1):32.
[11] 贺昌盛,王涛.想象·空间·现代性——福柯“异托邦”思想再解读[J].东岳论丛,2017,38(7):139.
[12] Dischinger, Matthew. States of Possibility in Colson Whiteheads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J]. The Global South, 2017, 11 (1): 88.
[13] 米歇尔·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陈怡含,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14]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15] 承华.穿梭时空女孩的创伤之旅——解读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J].外国语言文学,2018,35(1):84.
[16] 杜玉生.主体性与真理——福柯论“关心自己”[J].外国文学,2017(6):79.
[17] 尚杰.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6(3):21.
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The theory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s is the space philosophy based on marginalized space and marginalized people. Heterotopias, real existing localized spaces in social mechanism, can observe power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oncepts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by the unique perspective.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Colson Whitehead constructs three types of heterotopias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Coras journey of escape in his latest work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The so-called norms in 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 reveals deep-rooted racism and rigid hierarchy of power; compensatory and fragile heterotopias of illusion analyze the secrets and complexities of human nature; heterotopias of crisis have the protective effect, expressing humanistic sympathy beyond all races. By exquisite construction of heterotopias, the writer objectively portrays difficult situations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ir impressive efforts to fight for survival.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makes people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at deliberately faded dark history, which shows Whiteheads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ound humanistic care.
Keywords: Foucault; 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 heterotopias of illusion; heterotopias of crisis; marginalized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