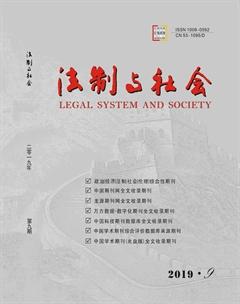清代官僚体系与第三领域的司法权力分配
摘 要 京控制度本身具有特殊性质,它是最高与最低的直接对话,这种非正常的跨越体现出中华帝国司法权力体系某些问题:皇帝的势力自上而下,然而基层社会亦拥有自下而上的力量,清朝司法及行政的压力空前巨大,造成了一个介于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司法行政的“第三领域”;本文试图就京控制度背后隐藏的上述三者司法权力分配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思考。
关键词 京控 基层社会 司法权力
作者简介:王倩倩,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116
京控制度为清朝一种非常规的司法制度。“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 清朝对于审级有着严格规定,对于越级也有着严厉的惩罚,但京控这种越过中间层层司法机构、使最高层统治者与最基层百姓直接对话的特殊伸冤方式却被建成了一种制度。尤其是在嘉庆一朝,基于嘉庆帝了解民隐的意愿,广开言路的决心,此类案件的受理力度得到了加强:“令都察院步军统领等衙门接到呈词即行奏明审理,以期民隐上通,不使案情稍有屈抑。” 此后,有清一朝,京控案件不断,直至宣统元年,官方档案里都可发现京控的身影。
京控制度本身具有特殊性质,它是最高与最低的直接对话,这种非正常的跨越,或多或少体现中华帝国层级森严的司法权力体系中某些潜在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以嘉庆时期突出存在的山东京控现象,就京控制度背后隐藏的司法权力分配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思考。
一、官僚体系的隐患——回避、考成与审转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防止因司法问题造成的民變,统治者需要一套完善的地方信息获得渠道,及时地把可能的叛乱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于是自康熙以来,清朝皇帝便针对信息获取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这其中影响最深的,就是以奏折制度为中心的监察方法。
奏折制度在创设初期,有权上呈奏折的人多为皇帝的心腹,信息也较为及时准确 。如康熙的宠臣李煦就曾就太仓盗案派遣家人王可成向康熙进呈奏折 。奏折可以让皇帝得到第一手的准确信息,同时,这种“风闻论事,而不究所从来”的秘密性质也让它成为了官员们相互监督的工具 。
然而,在帝国中后期,随着奏折的常规化,越来越多的官员获准使用奏折与皇帝沟通 ,官员“妄言”现象大量出现,信息的准确性大打折扣。此时,嘉庆便开始强化京控制度,一方面是为了跨过妄言的官员,直接获取准确的地方司法信息,另一方面也有利用这一制度进行的考虑 。然而,中华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确实存在这司法方面的隐患。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任官回避问题、考成问题、审转问题。
(一)任官回避:“临时”县官与“地头蛇”胥吏
清朝采取严格的任官回避制度,除了本省人不能在本省任职之外,乾隆时期更是扩大到原籍与任地相距五百里以内也要照例回避,有些本不需要回避的,如河道官员,也被纳入到了回避的范围。而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官员的任期通常不会很长,经常是少于三年。异地任官导致官员不通民情,任期短也使得官员易怀苟且之心,如此以来,熟悉当地民情的书吏和差役变成为了地方司法事务的主要承担者。
这些胥吏作为“编外人员”虽掌握权力却无国家发给薪水,自然容易利用权力谋私,成为地方司法的隐患。胥吏势力的增大,是皇帝与地方官权力博弈的结果,却容易给地方带来不安,一旦与恶势力结合,其破坏力更是可惧。
(二)考成与问责:总管地方官员的“行政承包责任制”
不通的民情与短暂的任期没有给州县地方官施展才华的空间,向上走便成了官员唯一的出路。对清朝官员来说,求得晋升,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三年考成中取得优良,二是避免处罚。考绩由督抚一级高级官员的短评决定 ;而处罚则采取问责制的形式:地方官员的失误,皇帝会问责到总管一方的高级官员上,乾隆以后,这一类高级官员通常也是巡抚、总督 。总而言之,巡抚、总督一方面要为皇帝负担着发现人才、举荐下级的任务 ,另一方面又要为辖区地方官员承担皇帝的问责,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等式:
(上级)问责+举荐(下级)=“行政承包责任制”
在这样的一种“行政承包责任制”之下,地方官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迎合高级官员的需要,因为晋升的命门掌握在上司的手里;而高级官员遇事则会选择包庇自己的下属,因为在问责制的前提下,保护下属就是保护自己。下面迎合,上面保护,高级地方官和地方官如同企业一般,形成了一个“上下一气”的互动网络,可想而知,民间案件进入这样一种互动网络,便只能按照此网络的逻辑,而非法律逻辑被加工处理了。
(三)审转:压力、逃避与幕友
清代统治者设定的审转制度相当严格:按照规定,除了户婚田土等自理词讼可以在一审机关了结之外,重一些的徒罪以上案件,均要交到上一级的司法机关覆审,并逐级上报复核,这一层层上报的过程也就是“审转” 。
对自理词讼而言,当一审机关对案子做出判决,只需要按月汇编给直属的府、道上级进行“查考” ,所谓查考,是一种仅对案卷的进行复核的形式审。 而非自理案件,尤其是徒罪以上案件的处理方法则不同,一审机关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只是一种意见,被称作“看语”,在一审机关审理结束后,案件还要向上进行审转,同时要把案卷、嫌疑犯、证人押解给直属上级进行“咨结”,在“咨结”的过程中,又会涉及到对案情的重新调查和新证据的引用 ,因此二审机关对非自理词讼的“咨结”是一种实质审。此后,二审机构还要把文书层层上交给更高级的审理机构进行“复核”,直至该类案件的最高审级机关方可批结 ,如寻常徒罪到督抚一级便可批结,人命案则要直到中央的部级机关方可批结 。在审转过程中,每一级上级若发现审理不当,均可驳诘,从府驳到部驳,关卡层层,毫不马虎。
这样一套严谨繁复的审转制度给地方官员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压力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是审限:“自理、命盗抢窃等案、情重命案” 等三类案件皆有“审限”罚则, 其中“自理”类的如户婚田土等项的案件限二十日审结,否则“违限,不及一月,罚俸三个月;一月以上者,罚俸一年;半年以上者,罚俸二年;一年以上者,降一级留任” ;二是 “断罪引律令”理念的严格落实:康熙时期,只有拟罪错误且涉及到人命的时候才会受到惩处,雍正时则于驳覆时引用法条错误即会受罚 ,到了嘉庆时期对于违反“断罪引律令”的处罚更是细致落实到各级地方官员。在 “上下一气”的体制之下,面对这套审转制度的压力, 各级官员承担的是“共同责任” 。
基层官员普遍会采取一些手段逃避审转制度的压力。首先,由于自理词讼在州县一级即可结案,只需按月汇编上报,不会影响考成 ,于是,官员便采取积压的方式处理自理词讼。其次,非自理词讼亦可以做手脚:为了逃避审限压力,有些州县衙门干脆采取不受理的做法,讳盗不办或是改盗为窃 ;对于无法回避的案件,则在案卷处下功夫。
徒罪以上案件要面临两个关卡,一是直属上级的咨结,二是更上级的复核,按规定应该要把案卷、嫌疑犯、证人押解给直属上级,但现实情况是,州县官员经常以缺钱等借口不押解人证,而直属上级显然对此十分理解 ,于是本應是实质审的“咨结”变为了案卷的文本覆查。至于更上级的复核,则主要关注案卷呈现的案情是否有疑点或矛盾,以及在援引、解释法条时是否恰当 。对于没有受过法学训练,在科举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州县官员来说写一份好的案卷文本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州县官员便会雇佣专业的幕友帮忙解决绝大多数司法问题 。如此,幕友与官员良好配合,无论是寻常案件的审理还是上交案卷的制作,都达到了一种“天衣无缝”的状态 。
在任官回避、考成与审转压力共同作用下,低级地方官与高级地方官抱成了团,配合着胥吏与幕友的帮助,形成了一个自我运行良好的官僚体系。很多进入这一体系的民间词讼案件如同进入了一个“黑洞”。于是,基层百姓冤抑难伸,赴京呈控便成了唯一选择。
二、民间纠纷的审前消化—— 司法“第三领域”的探索
嘉庆皇帝似乎也了解地方官僚体系的黑洞性质,并寄希望于京控制度来甩开这个司法信息“加工厂”,得到最原始最真实的民间案件信息, 然而,除开官僚体系“加工厂”的通病之外,作为信息“原料生产地”的基层社会,因各地区经济、社会条件不同,案件情况、司法实践情况也各不相同。比如,州县为一般意义上的一审机关,而在诸如重庆等商业发达的城镇中,商业讼案(包括航运纠纷)有机会超越“州县自理”的层级,而上升为府级以上官员承审的重大案件 。
当嘉庆开放京控之后,山东京控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省份,以至于嘉庆皇帝多次针对这一现象进行抱怨:“若云东省距京较近,民间控案便于赴诉,则直隶为畿辅近地,即山西、河南亦均密迩都城。该三省虽亦间有赴控之案,然总不至如山东一省之多。岂直隶等三省遇有上控之案,该地方官竟预为阻拦,不使来京申诉乎?” 。既然在嘉庆帝眼中,离首都的远近不是主要原因,那么,山东这个“原料生产地”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造就了如此众多的京控案件呢?
(一)白莲教的启示:官僚体制之下、家族之上的第三领域
在山东嘉庆一朝的京控案件中,总能发现白莲教的影子。无论是嘉庆之前1774年的王伦叛乱,还是之后1897年的巨野教案,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白莲教、大刀会等秘密组织对于山东的影响在有清一朝都是相当显著的。
韩书瑞女士对山东西北地区的研究中发现,该地区人口的大多数为小自耕农,人口也极为密集 。由于在清代官僚体制之下,行政单位只到郡县为止,这就造成了在山东,郡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涵盖了大量的人口及土地。这种“地多官少”的现实造成了官员除了赋税征收外不会有太多精力涉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管理”,于是,这些提供社会服务的任务则必然会落到“地方精英”的头上 。
然而,山东地方社会的现实并不乐观,没有证据表明,山东这片土地存在一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精英制度”。以寿张县为例,官员地位远高于家族,寿张县的家族和社群只有很少的力量来保护其自身对抗国家的要求,“社会管理”的任务无人承担 。于是,在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这种过度的“权力真空”,会被像白莲教这样不太权威的团体所填补 。
学者黄宗智通过观察发现,民间案件的正式审判发生于州县衙门,由官员进行;民间案件的非正式调解,经常由“中间人”以及小区和宗亲的男性长者担任 ;而万一民间的非正式调解失败,在进入正式法庭审批之前,还有一个可以消化纠纷的“第三领域”:一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由官民共同参与的领域 。这“第三领域”的参与者范围极广,同时兼具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特征,两种力量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状态。山东京控数量众多,除了地理位置的便利、地方灾害频繁、官吏积压案件等等原因之外,或许同当地这种“第三领域”无法有效率地吸收化解民间的纠纷有关。
(二)第三领域的民间化:华南地区的强大宗族
学者科大卫认为,宗族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一种以血源为名义的经济组织,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公司组织 。在以土地税为主的年代里,里甲可被看成是一种税收保障制度,起初以丁为中心,主兼田赋差役两项。然而明清以来,里甲的登记逐渐变成了以土地为中心,户籍除了于科举资格尚有作用之外,基本成为一纸空文 。
登记里甲的好处在于拿到官方承认的土地的产权,然而坏处则是必须要服役交税。所以,当时登记里甲的,要么是能够轻易解决税赋和兵役问题的武装豪强,要么是无法避免登记的弱势百姓,百姓只能通过依附武装豪强来解决生存难题。由于税收制度的改变,户籍登记由以人为主变为以地为主,祖宗便可以“造假”,宗族间的合并以及弱势百姓对豪强的依附也变得容易了 。于是,宗族成为了是一个围绕着土地为主的经济组织,而这一运行严谨良好的经济组织显然能够有效吸收化解组织内部矛盾:对宗族来说,里甲登记文件是土地凭证,家训是土地管理的规则,家族规定的书面礼仪则是体现合约者的权利义务,围绕着土地进行的大部分纠纷都可以很好地、不出家门地被解决。
其次,华南宗族总是积极地与国家权力进行良性互动,兴家学、重视科举就是很重要的一步,通过向上的渗透,华南宗族积极扩大着自身的民间力量 。宗族甚至在一些极容易产生纠纷大型公共事务上,比如水利工程上也显现出了可与官府抗衡的管理力量 。
可以说,华南的宗族在两方面表现出了非常优秀的能力,首先,它可以很好地吸收消化组织内部的纠纷,具有帮助政府减轻司法行政负担的作用;其次,它是一种可以对抗国家力量的地方社会组织,在地方事务上有更强的话语权,因而能够更好地维护宗族内部人们的利益。这种“双向的满足”使得华南宗族无论对内对外,都可很好地生存和发展,而华南地区的“第三领域”也在宗族地发展过程中,被明显地民间化了。
(三)第三领域的国家化:山东地区官僚体系的延伸
相比华南地区“第三领域”强烈的民间特征,山东地区的“第三领域”则被国家化了。明清时期,山东地区人口有了爆发性的增长,州县的管理地域并没有变得更小,但管理人员却大大增加了,行政司法任务也比之前更加严竣。于是,在州县之下,一套更为基层的乡村管理制度便被设计了出来:主要包括三种:税务用的里甲,地方治安用的保甲和教化宣传用的乡约制度。在这些制度之下,由官府选出,辅助官府进行地方管理的人员便被泛称为“乡保” 。乾隆年间, 山东巡抚杨景素就曾对山东地区的这种基层管理制度有一段描述:“东省旧例, 每村庄数处设立地方一名,或乡约、总保一名, 虽名色各有不同, 皆以供催征钱粮及拘拿人犯等事之用, 而牌头、甲长、保长则专为稽查保甲而设。” 理论上,州县政府直接委任每一级的地方管理人员,从主管多村的乡约、总保一直到主管10户的牌头为止。直接委任意味着直接负责,所有的地方管理人员都直接对州县官员负责,这种“扁平化管理”的模式使得各方彼此平等且互相监督,任何一种地方势力都不会坐大。
但实际上,这种制度并没有被落实 :主管多村事务的乡保是需要到衙门“具甘结”,但是主要负责村一级事务的甲长、牌头则不需要 。那些主要负责村一级最基本事务的牌头、甲长是由主管多村的乡保选拔,只需要就职的乡保向县衙列出名单,便能够正式委任,不需额外的手续 。由于州县官员的工作重心放在税收上,当这些人的任用能够保证赋税按时足额交纳、地方乡村社会稳定的时候,官府便会很少干预其具体运作 。并且清代山东地区这种乡约、保甲、里甲并行的乡村管理制度还存在着集中化的趋势:本来,负责治安的是保甲,到后来保甲基本名存实亡,调解民间纠纷被视为乡约的基本职能甚至是特权 。因此,理论上的互相平等、互相监督是不存在的,乡保很容易坐大成“地头蛇”。
州县官员直接任免这些乡保,而这些潜在“地头蛇”的乡保只需对州县官员负责,山东地区的“第三领域”不像是民间力量的表达,更像是官僚体制的延伸——“上下一气”“内部消化”。通过这种延伸,州县官员通将国家权力下渗入“第三领域”中。因此,如果说华南宗族是一种“双向的满足”,那么华北宗族便是一种“双向的不满足”,对下无法解决家族内部的矛盾,对上则无法抗衡官府的力量,因此,相比华南而言,在山东地区发生的民间纠纷,既不能在民间很好地解决,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面临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些在华南地区可以在宗族内被解决的纠纷,便积压在基层百姓之间,到了一定程度,便只能越过官僚体系,赴京呈控。
三、结语
清朝的皇帝通过这一套设计精妙的官僚体系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套官僚体系的最初构想,应该是使皇帝的权力能透过这样的一套体系,从上到下传递到帝国的基层。这个构想在实践中遇上了麻烦:官僚体系实在过于精巧完整,常常出于自身利益,会对皇帝希望获知的准确信息进行加工,在司法领域的层层配合更是“天衣无缝”。然而,皇帝对这种能够脱离其控制、自我运行的机制总会怀抱几分戒心,总是在思索着其它的方式来更好地控制这套官僚体系,京控制度便是王朝历史中的一个很小的尝试。
皇帝的势力是自上而下的,然而基层社会亦拥有自下而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各地区大小不一。清朝广阔的疆域以及人口使得司法及行政的压力空前巨大,造成了一个介于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司法行政的“第三领域”,一个结合了正式于非正式、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的领域。在有些地区,比如华南,基层社会向上的力量占据了“第三领域”的绝大多数空间,在司法领域,纠纷可以很好地在宗族内消化,就算不能,因宗族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巨大影響力,上升为官府不敢忽略的案件。而在以山东为代表的华北地区,国家向下的力量,很好地渗透进了这个“第三领域”。有冤的百姓没有强大宗族力量的支撑,而又要直接面对国家延伸至“第三领域”的强力,于是,冤情的上达,则会选择避开阻碍,绕道而行,“直达天听”的意愿,也就再所难免了。
注释: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44.
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谕.嘉庆朝上谕档:第4册.310-311.
孔飞力.叫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61-171,252-267.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50.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4:33.
白新良.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J].南开学报,1999(4):57.
崔岷.洗冤与治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15.
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149.
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4,176.
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42-169.
邱澎生.法律之治:明清讼师与幕友对法秩序的作用[J].化学物理通讯,2006(总第81期):8.
邱澎生.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冲击[J].中西法律传统,2008:61-64,90-96.
欧中坦.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42.
[清]穆翰.明刑管见录.6.
邱澎生.国法与帮规:清代前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决机制.301-333.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清实录山东史料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4:744.
[美]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73.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07-131.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M].香港:香港出版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66,95-110,149-162,179-220,297-320.
常建华.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J].河北学刊,2008(6):65-71.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朱批奏折.转引自段自成.论清代北方乡约与保甲的关系.47.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229-258。
段自成.论清代北方乡约与保甲的关系.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