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行
李晓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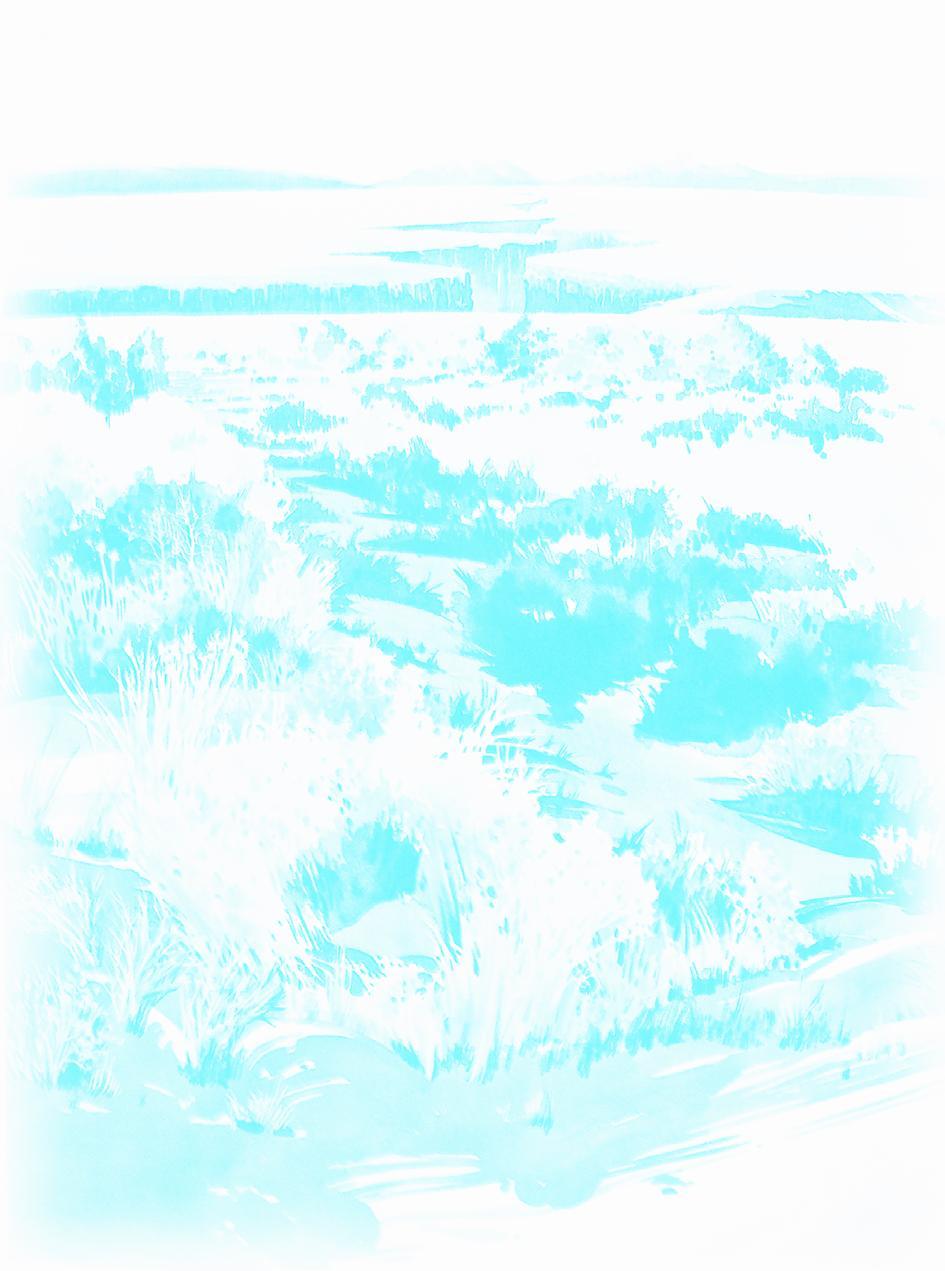
执着追求并且从中得到最大快乐的人,才是成功的人。
——梭罗
草之语
我生来对草木充满了亲切感,每当到了陌生的地方看到陌生的树木和草,都要停驻仔细打量,看看有没有与我的生命相通的气息。我熟悉草,甚至熟悉草木的情绪,知道不同的季节对于草木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白茫茫的冬天与萧杀的秋天,草木以各种姿态呈现它们的坚强。
草有草的生长周期,人有人的生命历程。平时,人们太容易忽略小草。草和百姓相似,都属默默无闻一类。在人和草木的交往中,有的人认为草不会开花。其实,草本植物中除较低等的蕨类植物和苔藓植物外,大多数的草都会开花结果,只不过它们的花果太不起眼,就像大街行走的普通人,平常的衣服,平常的步履,平常的表情,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有过怎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跟着一个人进行跟踪采访,都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寻常的东西。我也是一个普通人,父母为我选了上大学的专业——师范类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后当一名普通的英语教师。如今我已经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了,但我教的学生中有两个不一般,一个当了万亿企业的老总,一个当了学校校长,他们说,李老师,你给我们说过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人可以没有权势,但是不可没有格局。”我都忘记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他们已经由一棵小草长成了大树。
一位老师能教了几个出息的学生,是缘分。人和草的相遇也是需要缘分,我上初一时,父亲常常带我到贵定县关力堡村去写生。我趴在关力堡表叔的窗户往外看,立即看见了窗外草地的花蝴蝶,马上就跑进草地。在草地,我把辫子打开,绿色的风便和我的长发一起飘扬。在我的体悟里,草和人是一样有呼吸的,只不过很多人忽视草的呼吸。草有自己的语言,或者可以称作“草语”。草们会和同类说话,甚至可以用肢体动作表达思想情感,只是人类听不懂它们在表达什么。我的家乡黔南有一个县叫三都县,深山有一种草叫风流草,只要听到人唱歌,它就会跳舞;风流草见到姑娘穿得漂亮,也会摇摇摆摆地跳舞,只是对那些邋遢的男人,无动于衷。草还会吹奏乐曲的,尤其是夜晚,草丛里弥漫着草们好听的奏鸣曲。在草丛,我相信只需把手伸过去,就可以接住夜空里的萤火虫,它们不仅发亮,还像铃铛和钟表一样会唱歌。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上大学时候,我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就快乐得发疯,感到美国的梭罗是草木的知音,当然也是我的知音。梭罗徜徉于大自然,他说“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的,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岸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贵州多山,我也常常一个人爬上某一座山头,静静地体察大自然:天空的云彩像是一条金鱼的图像,云彩的周围还有飞来飞去的白鹭,山坡上的草啊,鸟啊,它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天空的云彩在一早一晚会发红,像是火烧一般,而小草不会,小草的一生,或者是绿的,或者是黄的,绿的时候是活着的,黄的时候是枯萎了。对于生死,草们比人类要坦然得多。
草的梦
很久以来,我期待在某个夕阳款款而来的時候,有小草脚步声从长廊响起,穿越一个又一个门,走到我驻足城市的那个钢筋水泥的门牌号,走上19楼……这个时候我仿佛通灵,感到关力堡的草木又在呼唤我了。
于是乘车来到了关力堡,贵定县的关力堡离我所在都匀并不远,不到一个小时车程。表叔的房子就在公路边,我把车停表叔大门口,登上小三层楼的最高一层,看到房子后面的一大片草甸子,这是经过镇政府联系搭桥,专门为城市美化而种植的草皮。在草甸子里,我能看到在大片的枯黄中间,居然夹着令人心动的小小的绿。草地的东面是公路,公路的前面是绿山,黔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冬天,即使在隆冬季节,山坡仍然绿黄交加。田野里的田埂并不那么笔直,田梗边会有垛起来的圆圆的稻草垛,一层层围着木柱,中间高,四周低,雨水可以顺着草叶流下来。
草对于关力堡是过客,正好似人活在世界上都是匆匆过客。秋天结束的时候,会看到一部分草皮被卡车运走了,这时草甸子就不完整了,有草的地方是绿的,没有草的地方是黄的,而且地皮凹低。因而我盼望夜晚早早到来,夜幕会掩盖住一切。夜晚来了,关力堡寨子四周的山线逐渐模糊,山是深色的,天空是浅色,可谓山天一色。大自然安静了,人的大脑就活跃了起来。寂静不是绝对的,夏天和秋天可以依稀听见鸟鸣或是虫语。深夜,草叶会发出声波,仔细聆听,声波里有长句,有短句……这是草们自己的语言符号。星子们在天际闪着光,天空开着无数扇门。小河边的小树林更暗了,除了大人打着手电筒走过去,小孩子绝不敢过去的。人们对眼睛看得见的黑暗有恐惧之心,而对心底中的黑暗却麻木不仁。
关力堡的草坪里藏着各种会唱歌的虫,草和虫类都有自己的生活,我虽然不是草,也不是虫,但是我可以藏匿在它们身边,做一个隐身者。草和虫子,还有它们身边的树木好像并不反对我的隐身,它们只管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安置自己。草们的生命虽然不像人能活几十年,但是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照样活得精彩。在草甸子,我还看见了黑白相间的小鸟,比麻雀小,能发出尖细玲珑的叫声(我称呼它为灵鸟)。在贵州这个地方,没有北方的严寒,即使在冬天草们也不会干枯,只会发黄,在黄兮兮的大片的草丛中间,还会夹杂一些嫩绿的小草,它们急切地翘盼春天的到来。我注意到草很公平,年轻的草不会歧视年老的草。我喜欢这片草地,喝醉一般和草们无距离交流,没有官腔,也没有空话和套话。草甸子上草的身形如此纤小,使得我对它们就多了怜爱。我发现草也有自己的秘密,只是人类不知道而已。
表叔的孙子是一个快乐阳光的小家伙,每次我到关力堡,总是缠着我讲故事。我曾和小家伙淌过小河,捉泥鳅,我俩捉了三条黏糊糊的家伙,放进小水桶,往回走,路上向我讲了一个女孩的事:女孩在东安小学上学,三年级。她妈妈在广州打工,跟一个男人跑了。她爸爸去了广州,再也没回来。一天晚上,女孩一定做梦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她起床喊着爸爸妈妈往河边跑,奶奶跟在女孩的后面,没有跟上……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女孩躺在小河,从上游的小东寨漂到新安寨镇的关力堡……从此以后,在关力堡走夜路就有了莫名的恐惧。
草木寂静
一次次抵达关力堡,一次次登上表叔小楼打开窗户……又看到那片可以寄存灵魂的草地了。虽然是冬天,贵州的冬天不算太冷,草地大部分已经干黄,尚有一部分绿的小草和蔬菜。我看着小草,小草们也看我。白天的关力堡是安静的,夜晚到来后更加丰富多彩。我感到自己像梭罗一样喜欢夜晚的孤独感,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生活的时候,曾这样描写过心境:“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是的,平常我们在人群中有说有笑,实际上有时候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应酬,应酬得久了,就会产生虚假,虚假的笑容,虚假的奉承,虚假的生活……真的是糟糕透了。
我喜欢夜晚到来时那种堪称完美的安静。比如在关力堡的草坪上,刚才我还低头看手机,猛抬头看到大地上的光线已经走丢了,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在白日里生龙活虎的山头,怎么一闭眼就睡着了?关力堡的夜晚是我所熟悉的,晚八点以后,星星会落到草丛捉迷藏,你可着劲去跑,也不会惊跑它们。星星们还会笑嘻嘻地藏在窗下,说“我们偏不走!”夏天或者秋日,只要打开窗,就会听到野虫藏在草棵之下唱歌,窗外还有蝴蝶,蟋蟀,还有能飞得很远的蚱蜢。三十几米外有一溜树木,树叶大多掉了,但是枝丫依然很密,小鸟藏在里面,人看不见它,只能听见它好听的叫声。
位于云贵高原上的贵州,山是主角,山之间的平地并不多,无论是稻谷,还是小草,可着劲长,长到山根,就长不动了。山坡的主角是灌木,即使是有小草,小草也被灌木掩盖住了。山的上面是天空,山脚的下面是一条小河,沉静而神秘。水中剪影般地出现交错迷乱的树影和为枝条所分割的蓝色天空,形成一幅天然的抽象画。这一大片草地的四周是山,东西北三面的山像大馒头,独有南山呈马鞍型。山底的小河无名而宁静,清凌凌的水里漂動绿莹莹的水草,是生长在水下的草。天空的白云在不远的小河水中闪烁而过,然后踪迹全无。农民在小河边种蝴蝶兰,春天的时候,蝴蝶兰就像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如果把脸藏在花辨后面望月……月亮只剩下半牙时,最迷人。在月夜可以和一只小狗在田野上奔跑,心砰砰地跳。可以说,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草木的眼神一直淡定,迷人,而自己作为尘世中一颗粒子,却越来越小,感到时间是一顶扎不牢的一帐篷,只要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跑。
我的家乡不缺乏草木,但多年前年云贵高原遇到大旱,春天的山头和土地不是绿的,而是黄的,对于已经习惯青山绿水的贵州人,焦灼到了极点……我才知道,有些草即便没有实用价值,至少可以绿,用绿去滋润期待健康和幸福的人们。在乡下,你会遇见了一棵树,我问它信仰什么?树木告诉你说,信仰时间。一个人活着,存在的依据是什么?我以为坐在草地可以大悟。人们总是容易短视,只看重自己的物质需要,看不到其它植物和物种的存在。人们发狠的时候会说,“我要像踩断一棵小草一般整死你!”岂不知小草在地球的生命要比人类更加久长呢。草还喜欢和别的植物做朋友,比如说野菜,草从不会干涉野菜长在草丛。
在草地,有时候我的思绪很远,会想到一些哲学家的名字,从中国的孔子、孟子,到外国的苏格拉底、康德等,感到他们的思想成长可能与他们所在地的一片草地有关。有了草的生长,就有了思想的孳生地,美国的梭罗并不是哲学家,但是他热爱大自然,崇拜东方哲学,才有了他的《瓦尔登湖》。人类的三大哲学基本问题之一,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在人类争论不休的时候,草和树木已经静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只不过人类并没有草木悟性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