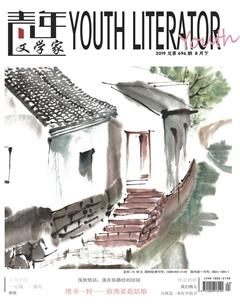“真相”与“真实”
杜昀阳

摘 要:《公民凯恩》是一部具有先锋性质的影片,无论叙事模式还是画面语言都具有反好莱坞特点。影片导演奥逊·威尔斯将一种“完美的形式主义”风格贯彻影片表里,而他那特立独行的叙事模式和惊人的影像手段各占这种风格的半边天空,它们不仅仅是影片的精美的装饰物,更是建构影片主题的“拼图碎片”。
关键词:《公民凯恩》;主题建构;叙事模式;道具;电影画面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3
一、叙事模式与“真相”的呈现
《公民凯恩》的叙事模式本身就是影片主题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呈现主题的工具。影片以报业大亨赫斯特为原型改编,观众对这种“人物传记式”电影的期待是:人物及其所处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角色传奇的人生故事以及他特殊的品质。显然,威尔斯意不在此,他似乎想要告诉观众一些超越人物、直指生命乃至世界真像的东西;而电影《公民凯恩》不止是威尔斯表达哲理的“语言”(工具),更是哲理内容本身。
首先,《公民凯恩》的叙事模式突破了电影规定性叙事,通过“外聚焦型”视点展现凯恩的一生。法国著名理论家热奈特通过“聚焦”(视角)一词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叙事模式。电影规定性叙事主要体现为传统的“零聚焦型”视角,相当于文学中的第三人称(上帝)视角,“叙事者”被隐藏起来,以保证叙事的客观性、自由性和真实性。相反,“外聚焦型”叙述手法强调“叙述者说得比人物知道的少”。[1]因为《公民凯恩》的敘述焦点回避了凯恩的主观世界,所以凯恩的行动充满了“神秘性”和“多义性”。
其次,由于特殊的“叙事者”加入了影片叙事,使得《公民凯恩》带有了一层“侦探推理片”特有的“探索真相感”。在类型电影中,类似于《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侦探推理片是以“智力游戏”、“思维推理”为核心趣味的,“叙事者们”所回顾的事件与影片中正在进行的故事紧密相连,互为因果。但《公民凯恩》中,叙述者所讲的故事与影片正在发生的事是割裂的,人物的生命成为了他人主观观点的拼凑。一开头,导演就通过新闻短片的形式饶有深意地向观众展现了凯恩的一生,唯一的悬念是关于“玫瑰花蕾”的谜团,但是影片的叙事却没有指向谜团答案。导演的叙事重点集中于:“叙事者们”眼中的“凯恩的生命片段”。这些“叙事者们”有:凯恩的情人——苏珊;凯恩的妻子;凯恩的同事;凯恩的管家。他们同时是影片中的“被采访者”、“叙事者”和“凯恩生命片段”中的“主人公”(在他们自己讲述的段落中)。在他们眼中,公民凯恩不是真实的“凯恩”,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凯恩”,是他们自己人生情感体验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公民凯恩”,都在寻找凯恩生命的真相——玫瑰花蕾之谜的答案。
影片叙事模式扩大了“公民凯恩”的所指,真实的“凯恩”在他人的“阐释”中越发神秘莫测。因此,在叙事模式层面,影片中的生命和世界具有了绝对的不真实性。一方面,这种“真实的不可能”与影片中报纸新闻行业的工作性质有着明显的对照性讽刺;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人生和世界的真相。在采访者们角度上,凯恩生命真相——玫瑰花蕾的所指,是永不可知的;从观众角度(观众在影片中占据着记者的视角),知晓凯恩生命的真相亦不可能;而从凯恩本人的客观生命进程来看,影片的叙事模式传达了这样的意味:人永远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在这些不同的眼光中,活着的生命变得“虚妄”,死去的生命则变得“虚假”。
也许,“玫瑰花蕾的所指”,即“生命真实”与“世界真实”具有绝对的不可知性、不可能性。有趣的是,新闻出版业在这种“真实的不可能”中所承担的角色,既是影片批判的重点,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真相的一部分。
二、主题化的电影道具——凯恩看到“真实”之不可能。
凯恩不可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世界,这是真相的第一层。通过分析影片道具在画面中的使用,可以得出结论:凯恩自身的不完整(缺失)之令他无法看到真实。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童年的伤痛和原生家庭明显影响了凯恩的人格。[2]在影片中,凯恩的缺失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部分:“童年”(代表了凯恩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隐秘情感)、“母亲的爱”以及“社会(世界)的爱”。它们与电影道具的对应关系如下:
由上表可见,母亲的缺失是凯恩无法看到全部真相的根本原因,结合电影道具在电影中的呈现,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走进凯恩的内心世界。
“雪橇”出现在凯恩离家前的段落中——凯恩在雪地里玩雪橇。这个场景强调“雪橇”是凯恩童年中最后的玩具。在凯恩收到资本家的礼物时,雪橇出现在画面中,它代表着角色童年的客观缺失和其主观的不承认。结尾段落中,雪橇被发现而后被烧掉。镜头中燃烧的火焰的静止画面延续了数秒,静止的画框中只有火焰在燃烧跃动,吞没了雪橇。这段完全寂静的时间似乎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也许,雪橇作为凯恩不完整童年的遗骸,早已经失去了生命。
“苏珊的声音”体现了凯恩童年中母爱的缺乏,同时它又是这层“缺乏”的延伸。母亲“抛弃”了凯恩,成为凯恩生命中永远的缺席。而她的缺席最终成为了凯恩人生中其他缺失的根源。在影片中,凯恩为了这个声音不顾他人的反对,用自己偏执的努力支持苏珊唱歌。最后,苏珊放弃了,她不愿意成为凯恩内心中的缺失的阴影。她的离开也标志了凯恩最终失去了对他人的控制。
“雕塑”象征着凯恩的社会关系和第一任妻子。凯恩奋斗,挣钱,用自己的方式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买了很多欧洲的雕塑,和雕塑一同来到凯恩生命的还有第一任妻子。在记者对凯恩同事的采访段落中,凯恩对待妻子的模式和对待报纸读者和社员同事乃至政治敌人的模式是一致的。它们代表了凯恩心中缺乏对他者的爱,正因为缺乏,凯恩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人民之爱,亦不懂的爱人。最终,凯恩第一任妻子、同事和读者都离开了凯恩。也许,这些人正如凯恩拼命收集却不曾问津的雕塑一般——他们从未真正属于过凯恩。
“玻璃球”作为核心道具,相当于语言符号——玫瑰花蕾,暗喻真实的不可知。个体情感的发现(个体与自身)和亲密情感的建立(个体与他者)是一体两面的,都属于主角体验自我存在的重要内容,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缺失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真实”变得不可能。
“玻璃球”在影片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玻璃球在凯恩临死前说出“玫瑰花蕾”的时候摔碎了,一个扭曲的空间呈现在画面中的玻璃碎片中。暗示了玫瑰花蕾作为真实的永不可知。
第二次出现,凯恩第一次到苏珊房间中,玻璃球在苏珊房间。这说明玻璃球是苏珊的物品,而苏珊又作为一种替代品存在——替代凯恩缺失的亲密情感(母亲般的爱)。由此,“玻璃球”代表了凯恩童年——自我情感发现和亲密情感——的缺失。
第三次出现,在苏珊和凯恩城堡房间中,苏珊将要离开,凯恩开始摔东西表达愤怒,但却没有摔碎玻璃球。这里可以看出,凯恩倾向于搜集并保留自己不曾拥有的“童年”和“亲密情感”
以上人物和道具的关系呈现出相似的模式,即“迷恋”和“收集”。对物的迷恋并不是源于对物了解,只是弗洛伊德所言的“恋物癖”(fetish)而已。弗洛伊德表示:“迷恋物是小男孩所相信并且——出于某些我们所熟悉的理由——不愿放弃的女性的(母亲的)阴茎替代物”。(the fetish is a substitute for the woman's (the mother's) penis that the little boy once believed in and - for reasons familiar to us - does not want to give up.)[3]总之,通过崇拜物品,自我心灵可以避免受未获事物的侵害。这是一种与母亲密切相关的“无意识否认”的症状。生命的缺失给凯恩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口,电影道具就如同贴在伤口表面的麻药,可以让人屏蔽掉真像盲目的活下去。不管对凯恩还是观众而言,生命中的真像永远是冰冷残酷的:疼痛从不曾真正消失。
电影中的四个主要道具是凯恩对自我本质缺失的一种外在弥补。悲剧在于,生命的真相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悖论:人都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是伤口的来源),同时人注定无法理解自己不曾拥有过的东西,由此人永远无法了解真实的自己。连凯恩自己都不能了解他自己,那么所有的旁观者(包括我们观众)亦无法做到。不得不承认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谜,也正因如此,《公民凯恩》才格外迷人。
三、深刻的影像形式:世界真实的不可知。
《公民凯恩》天才地运用了电影艺术手段,其影史地位至今无人超越。它向我们证明了:电影作为一种“用画面去思维”(普多夫金语)的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创作者通过主观化、表现化的镜头和剪辑构建了一个真假模糊的空间,这个空间层次丰富、动态变化且容量无限,向观众呈现了“凯恩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实是不可知的。
《公民凯恩》中可以拿来致敬的场景俯拾皆是,这些场景通过画面空间的平行对照抒发了作者的“内心之语”。以记者采访《问世报》会计伯恩斯堪段落(第三个采访)为例。记者在伯恩斯坦的办公室进行采访,办公室房间顶部很高,大而空的空间中最明显的是办公桌上方凯恩的巨幅照片。真实的人物在其中显得比较渺小,镜头的摄影也采用平视的角度(即旁观的视点)。画面中,两个人的对话证实了画面的含义:伯恩斯坦对凯恩的猜测建立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之上,比如他对白衣服姑娘的那些表达。
相对应的,闪回的几个段落展现了伯恩斯坦的回忆内容:在这些回忆画面中,人物多位于屋顶很低的空间,画面显得拥挤,暗示了回忆者(伯恩斯坦)关注的只是凯恩的主观世界,削弱了他周边世界的存在。同时,画面中频繁使用仰视的镜头,这种主观化的视點使人物显得高大,意味着注视对象的“不可知”。
综上分析可见,闪回前的采访空间与闪回中的回忆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共同指向了一个主观建构的“新闻世界”,不论它空阔宽大还是逼仄狭小,不论它意味着“寻找”还是“回忆”,它都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电影画面的艺术性主要通过摄像机的移动和剪辑来表现。比如:在第一个闪回段落中,凯恩搬到报社,与主编卡特先生见面。一个下降镜头展现了报社大楼的全貌——象征着人类的“整个世界”。接着,凯恩一行人进入大楼,一堆堆“巨大的人”和“各种家具物品等杂物”涌进狭小的办公室,《问世报》迎来了它的转折点。
第二个闪回段落中,凯恩在用餐时和卡特就“失踪女人是否死亡”进行“真假辩论”(定场镜头是窥视视角)。镜头大部分时间固定在餐桌前的地方,以凯恩为中心进行有限而且“吝啬”的摇动,仅把需要入画的人框住。同样在下一段中,凯恩与李兰一行人写着报纸的原则,摇镜头基本上只展现与凯恩交流的人(没有交流的人则不予呈现),比如说他把“原则”交给萨利去发表的片段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克制的”摇镜头表达了“凯恩世界”的真相——一切他者都围绕主体自我的需要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凯恩在朗诵自己写的原则时,脸部完全被阴影覆盖,此种特殊的布光手法让观众意识到,这些原则并非出自凯恩真实的内心。
接下来是过渡段落,一个上升镜头将画面从报纸标题拉远,一个大远景中满地的报纸显示出作者意味深长的讽刺。凯恩、李兰和伯恩斯坦看向窗外,这里采用双重曝光摄影,窗玻璃作为特殊的镜面,既映照出窗外的报纸搬运工,也“照见”了窗内的注视者——凯恩一行人。窗上印有《问世报》的发行量——circulation26000。
下一个段落与之形成对照,窗外凯恩三人注视着窗内《纪实报》的工作人员照片(被相框框住)。窗上印有《纪实报》的发行量:“circulation495000”。镜头向前推进,定格在照片上,摄影机镜框和相片镜框重合,从而形成了时空转场。摄影机的闪光灯一闪,时空已经过渡到六年后。在《问世报》的庆祝舞会上,观众知道了凯恩已经把《纪实报》用20年凑齐的工作团队挖到自己的手下,而且《问世报》报纸发行量达到纽约最高——684132份。
以上的场景过度十分精彩,通过画面信息的充分利用和画面间的平行对照,导演将原本十分复杂的时空叙事进行了高度电影化的表达。
“庆祝舞会”是伯恩斯坦所有的回忆段落的中心场面,同时也是影片中最为经典的场面之一。该场面的画面模式是冷淡而且戏谑的,蕴含了深刻的象征意味。它似乎包含了现实中“狂欢”的影子,包括观影者自己生命中的那些“镜花水月”。开始时,画面空间被斜线分成两部分——舞女们的跳舞场地和员工们的用餐长桌。镜头位于画面的右下方,隐藏于最隐蔽但视野最广的角落,如同一个冷漠的窥视者游走于方桌的后面,在前景——众员工的后脑勺——后方搜寻着凯恩的一举一动。它“站立”着,平视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一切。当舞蹈正式开始时,镜头随凯恩的位置转化到舞女的视角,它“化身”为舞女中的一员,用面无表情的欢笑评价着这场生命中最虚假的狂欢。在这看似欢乐无忧的庆典中,导演插入了两个大特写画面,打破了画面剪辑的流畅性,一个是李兰和伯恩斯斯坦的特写画面,李兰大声附和着伯恩斯坦,但空洞迷茫的眼神却引出了他心中的不满和疑问;紧接着另一个特写画面是乐队的表情,演奏者们闭着眼吹奏乐器,众人盲目的狂欢心理浸满了银幕。接着镜头从各个角落注视着舞会,画面在流动的时空中营造出无处遁形的戏谑和张力。场景最后落脚在李兰和伯恩斯坦的谈话,两个人正在讨论《纪实报》员工的“忠心”,此时,后面窗户里映照出了房间中的舞会场面。窗户从室内向外看本应该代表“通往真实自由世界的通道”。然而这里却反用了窗户的“窥视功能”:我们向窗外看,看到的却是室内的景象。这里通过窗户,表达了时空的“镜面意味”,即“虚假的场地”,同时又表现了时空的“窥视意味”,即“欲望的场地”。在这里“真实世界的不可知”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指射新闻出版行业,更扩展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
在這些回忆的段落中,“雕塑”在画面中的使用不能忽视。舞会上,凯恩宣布他下周要出国去欧洲度假。伯恩斯坦表示,欧洲还有许多雕像有待凯恩买下来。凯恩随口回应:“这不能怪我,伯恩斯坦先生,他们搞了两千年的雕像,可我买雕像只有五年时间啊”。“买雕像”与“挖员工”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类比。舞会场面结束后的衔接画面是:李兰淹没在满屋子的雕像中——他在凯恩家中为其打理满屋子的雕像。对应到舞会中关于“雕像”的对话,也许,“员工”与“雕像”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都不过是凯恩证明自己的工具而已。而这些“员工”与“雕像”一样,可以随时消失在他的生命之中。伯恩斯坦最后的回忆段落是凯恩带来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她或许就是凯恩从法国带回的最贵重的“雕像”。
《公民凯恩》的主题体现了隽永的生存哲思,揭示了生命和世界的真相。借助影片中具体的影像建构元素及其运用模式,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模式惊人的深刻性,它们如同锋利的刀子,把洋葱般的“凯恩世界”一层层剖解。也正因为如此,《公民凯恩》是一部靠“画面运动”取胜的电影。正如马尔丹那句经典的论断“电影作为艺术而出现是从导演们想到在同一场面中挪动摄影机那一天开始的”[4],影片向我们展现了真正电影艺术可以达到的高度——包括无与伦比的摄影以及剪辑的智慧。在今天,各种电影技巧已经不再“新鲜”,但是能将之和影片主题和人物内心进行天衣无缝的融合,并形成戏剧化的表达者少之又少。可见电影艺术家的智慧在于其灵活性和深刻性,他们懂得高明而且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形式风格”,不会愚蠢地把仅属于电影的宝贵财富当成庸俗女人的首饰。
参考文献:
[1]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9-130.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11-1.
[3]Sigmund·Freud ,'Fetishism'(1927e).
[4]胡星亮.影像中国与中国影像[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