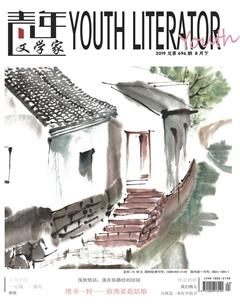《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的人文音韵美
曾佑强
摘 要:《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多少被忽视掉了,人们知道安吉拉·卡特改写了世界各国的童话,往天真善良的童话里注入了血腥、色情、恐怖等成人元素,可如果反复研读,细细揣摩之下,她的童话故事重复、变奏、狂想,却更像一首首吟唱的音乐,余音袅袅,是民乐的乡土气息,还是狂欢与颠覆的摇滚音乐?亦或是兼而有之,我们可以用耳朵跟随卡特的叙事韵律,用熟悉的音乐体验来照亮对故事这种传统手工艺的解读。音乐叙事体验参与了现世的政治批判,它狂歡与颠覆的摇滚音乐元素激活、包含了包括妇女,孤儿,穷人,醉汉,哀悼者,文盲等边缘人群的开放性人文主义情怀。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童话;人文音韵美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2
一、前言
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作为当代最具独创性、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其个人风格突出,作品诡异精致,复杂多变。她的独创性重点体现在以童话、民间故事、文学经典为蓝本,以丰富想象力和非凡叙事技巧将之加以重塑,呈现出童话背后的黑暗面,具有颠覆性兼奇幻美的独特写作模式。她在《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序言》中开宗明义,“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文学,无论是故事还是诗歌,都是被叙述而不是被书写的——人们聆听而不是阅读。所以精怪故事集也好,民间传说也罢,所有这些来自口头传统的故事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得以触及那些创造世界的普通男女所拥有的想象力”(安吉拉·卡特 2)注释[1]。她在故事集的序言结尾处提到“许多年前,已故的民族音乐家、民俗学家和歌手A L. 劳埃德使我懂得即便不知道某个艺术家的名姓也同样可以认出她的手笔。我将这本书献给这个建议,并以此表达对他的怀念”(20)。可以窥见音乐给她编写这部故事集有所启发。故事集总共十三章,另还包含了安吉拉·卡特自己写的前言,以及玛丽娜华纳撰写的后记,不可否认,卡特是想通过这部与男性故事形同进程的另一版本,来宣布分享属于女性的那部分故事叙述权力。反复研读之后,卡特采集的女性童话,让我们体会到民间叙事的音乐性,这种新的声音被反复播放与哼唱,夹带着狂欢与颠覆的色彩,让读者最终沉浸在作者包括女性及孤儿,穷人,醉汉,哀悼者,文盲等边缘人群的开放性人文主义情怀之中。
二、主导意象的运用
音乐家瓦格纳用一个特定的、反复出现的旋律来表现某个事物或者某个人物的特征,“在文学中运用主导动机就是用特定的事物象征某一特定的人物、境界或概念”(雷茜 72)。“文字、意象和观念,受到音乐力量的影响,现在都在寻找一种与音乐相似的表现方法”(尼采 50)。卡特运用特定反复出现的意象来表示人物、事物、思想情绪的特征。如在故事“蜜尔·阿·赫里班”中的巨人是典型的封建家长——残忍、丑陋、愚蠢,当巨人突然觉得口渴的时候,就打算“杀一个外边来的姑娘(蜜尔·阿·赫里班三姐妹),把她的血拿来给我”(32),谁知蜜尔·阿·赫里班听到了巨人的谈话,把自己和两个姐姐妹的马鬃项圈戴到了巨人女儿的脖子上,而把巨人脖子的琥珀疙瘩戴到了自己和姐姐们的脖子上,因此导致巨人的三个女儿被误杀,而且她们的血还被拿给她们的亲生父亲解渴。故事的巨人寓意如此的血腥与愚蠢,可见一斑。而类似荒唐的巨人形象再次出现在故事“鸟的较量”中,巨人要强行占据国王的儿子,当他发现被送来的是厨师的儿子时,他“就拎起他(厨师的儿子)的两个小脚踝,‘咚的地一声把他砸在了旁边的石头上”(99),相同的悲剧也发生在了管家儿子的身上。坏后妈的形象也作为故事集的一个主导意象反复出现。在故事“死人集市”、“坏后妈”、“小红鱼和金木屐”、“刺柏树”、“美丽的瓦西丽莎”、“青蛙姑娘”等分别出现了恶毒、残忍的坏后妈形象。以故事“死人集市”为例,当第一人妻子生双胞胎难产死后,于是第二任妻子负责照顾双胞胎,后妈捣谷子的时候,会把“上面一层细面粉拿走,把下面不能吃的渣滓留给他们”(208),有一次,双胞胎把打水的葫芦打坏了,被后妈用鞭子抽了一顿,一整天都没有吃的他们,只能去求助于死神的守门人,想见到地狱的母亲,好请她再给他们买两个葫芦。死去的母亲见到自己的被后妈虐待的孩子后,在死人集市买了有毒的棕榈仁托双胞胎带给后妈,并“向你们的后妈问好,谢谢她把你们照顾的这么周到。”(210),后妈吃了这些棕榈仁之后就死了,并通过占卜之口告诉世人“要是有几个妻子,其中一个丢下孩子死了,其他人就必须照顾这个亡妻的孩子”(213)。故事中男性角色的缺失,某种程度体现了卡特的女性主义观,但是如果,只如卡特自己所述:只想为了姑娘们把这个收集完整的话,那么她收集的“坏后妈”们却是不幸的家庭的根源,体现女性之间互相斗争与陷害。所以,在这些反复出现的“坏后妈们”故事里,我们更看到了卡特对于孤儿等弱势群体的关心。
三、重复变化节奏与音韵之美
英国文学教授罗杰·福勒曾指出:“有时当大量结构相似的短句和短语连续重复时,文本的音乐结构就会置于前景位置”(转引自徐岱195-196)。《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中的故事存在着三种重复模式:单个故事中段落自我重复;故事集中单个故事间主题重复与新故事覆盖旧故事的重复。正如福斯特所述“有关小说中简单节奏的问题,这么说肯定够了:我们可以将它界定为‘重复加变化,而且可以实例来说明”(E· M·福斯特 159)。第一种重复模式:单个故事中段落自我重复,是本故事集中大部分故事采用最常见的叙述模式,是这部故事集的一大亮点。以开篇故事“寻找运气”为例,主人公——一位老妇人,因为鸡蛋老是被偷,打算问问不死的太阳。在路上遇见了嫁不出去的三姐妹“哦,阿姨(老妇人),求求你,也向他打听一下我们的事儿,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嫁不出去。”(5);之后老妇人相继遇到了一直感觉冷得直哆嗦的老太婆;一条又混又暗的大河;一块硕大的石头,他们的说话内容重复,只是在最后一个诉求有所不同,分别求老妇人帮忙向不死的太阳问问,老太婆为什么老是暖和不起来;大河为啥总是流不顺畅;大石头为啥不能掉下来安歇。老妇人见到太阳,一一询问了太阳三姐妹、老太婆、大河、大石头托付给她的问题。然后她在回家的路上,依次传递太阳的答复给他们。由此故事结构就像音乐的对位一样:前奏——高潮——尾音。重复的内容基础上,又有了不同的答语,循环往复,朗朗上口,深入脑海。第二种重复模式:故事集中单个故事间主题重复,在故事集中也很常见。如“太阳东边,月亮西边”重复“渔女和螃蟹”,“天经地义”重复“鲸脂小伙”,“十二只野鸭”重复“赶走七个小伙子的姑娘”,“阿赫和她的狮子养母”重复“迪拉维克和她的乱伦哥哥”等等。虽然“渔女和螃蟹”搜集自印度部落,“太阳东边,月亮西边”搜集自挪威的传说,但是他们讲述的都是美女与野兽主题。这也体现不同民族之间也会出现共鸣的文化现象。第三种重复模式:新故事与旧故事之间的覆盖重复,则出现在“苔衣姑娘”改写白雪公主,卡特版“小红帽”改写小红帽,“绿鸟”改写东西南北风卡特版“睡王子”改写睡王子等故事中。卡特版本故事按照旧故事的情节发展,但是还原了故事的真实声音,增添了血腥、恐怖的元素。如卡特版“小红帽”,虽然故事讲述的也是小红帽探访外婆的故事,但结局却是“他(狼)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于是一下子扑到好心的老婆婆身上,几口就把她吞掉了”(262)。
三种重复模式有时会交织出现,在原有的基础上累加变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进入故事高潮。这种重复产生的整体性效果会让人联想到当管弦乐队已经停止演奏之时,我们却仍能听到某种实际上从未真正演奏过的东西。此时此地,整個故事层层叠加全都一起涌上心头,相互间延展渗透为一个共同的整体。这个共同的整体,就像作为整体的交响曲。
四、狂欢颠覆与人文情怀
《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中不同人物以及人物和作者之间都存在地位平行的对话交锋,构筑出集合多重观点、多声部混响合唱的小说形态,摆脱了一元叙事的单调独白,创造出灵活多变、开放多元的叙述话语。而从众多独立发声的主体各自不同的声音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也可延展出解读作品的更多维度。女性的话语影响着她对民间故事的热爱,贯穿她的《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可以看到卡特对女性的偏护之情在她的所有作品中燃烧。然而不少故事都像民谣一样循环往复的结构,这使得重复本身带上了狂欢色彩,新故事与旧故事之间的覆盖重复具有摇滚乐的颠覆精神。这种狂欢包括妇女,孤儿,穷人,醉汉,哀悼者,文盲,学徒等弱势群体的狂欢以及他们所使用的“低俗”文化、大众语言、幽默粗俗的狂欢。正如故事集最后一个故事“伸开手指”的结尾“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自己,否则,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不会有人来帮助你,因为你没有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523)。卡特把她的故事毫无吝啬的分享给了她的读者,颠覆世俗压迫与强权,却也突破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维框架。安吉拉·卡特,值得进一步被研究,不能只被限定于女性主义,她强烈的人文关怀,她的视野已经放置全球,她是一位独具人文情怀的作家。鉴于此可以说安吉拉·卡特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此研究也可以为重新看待卡特及其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五、结语
正如福斯特所说“故事是最原始的,它一直追溯到文学的源头,那时候阅读还没有发明呢,而且故事吸引的也是我们身上最原始的本能。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对自己喜欢的故事如此毫无道理地欲罢不能,而且随时准备跳起来对别有所好的人极尽攻讦之能事”(E· M·福斯特 36-37)。我们也应该跳出来为这部被忽视的集子,让它发出应有的声音。故事以其特殊功能确实能够做到,而且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使我们由读者转换为听者。我们可以用耳朵跟随卡特的叙事韵律,用熟悉的音乐体验来照亮对故事这种传统手工艺的解读。细细揣摩之下的进一步深思,对每一部经典作品的每一次阅读与解释都在当下把它重新激活,提供一个再次阅读它的奇迹,音乐叙事体验参与了现世的政治批判,它狂欢与颠覆的摇滚音乐元素激活、包含了包括妇女,孤儿,穷人,醉汉,哀悼者,文盲等边缘人群的开放性人文主义情怀。
注释:
[1]文中涉及《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的文本皆出自安吉拉·卡特:《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郑冉然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此后不再一一标出。
参考文献:
[1]安吉拉·卡特:《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郑冉然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E· 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3]雷茜:《到灯塔去》音乐叙事技巧的认知分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
[4]尼采:《悲剧的诞生》,刘崎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年。
[5]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