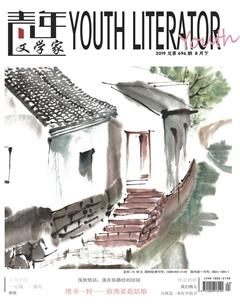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之辩
佟与格
摘 要:报告文学自新文学诞生起就以其即时性和真实性的特征屹立于文学之林,并在一定时期起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近年来以《人民文学》开非虚构文学专栏为起始,非虚构文学这一外来概念成为了文学界不可忽视的一隅。本文将非虚构文学与传统报告文学进行比较并探讨二者的真实性特征。
关键词:非虚构文学;报告文学;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01
就真实性而言,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都继承了文学的真实性精神,但是与传统文学相比,二者之真实具有鲜明的纪实性特点。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于创造,那么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则是记录和刻画,把现实原有的样子通过作者的视角和艺术技巧展示给读者。“非虚构”(Nonfiction)文学与报告文学(reportage)二者均可以视为纪实文学之范畴。但是由于二者产生的话语语境与艺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二者的关系既继承创新又相交相离,加上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占据了一定优势,使得二者的理论范畴研究需要进一步的解决。本文将通过三部分来进行二者有关真实性的论述。一是生活与宣传的真实性之辩,这是从二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角度来谈的;二是个体视角与群体视角的真实性之辩,这是从作者立场和思想的角度来论述的;三是生存困境演化的真实性之辩,这是从二者描述的人物生存发展需求的不同来阐释的。
一、生活与宣传的真实性之辩
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大陆初露端倪是在新世纪的初期,伴随着报刊媒体的宣传和译介书籍的出版,人们对于非虚构文学这种回归生活真实性的文体类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关于非虚构的特质,写作者和研究者都认可它是崇尚真实、呈现事实、寻求真相,但在‘真实观上出现较大争议。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观,显然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来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真实观,而是力求无限接近社会现实本身。”[1]在经济社会的背景下,社会总体态势稳步发展,激烈的矛盾冲突已经较难见到,可是生活中的个体和群体困境依然繁多。非虚构文学便是将目光投入进社会生活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容。很多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对于生活新的认知,如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梁鸿《中国在梁庄》、贾平凹《定西笔记》和李娟《冬牧场》等等。虽然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存在诸多争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非虚构文学面向生活的人文关怀精神。在今天网络小说等虚构文学逐渐膨胀也逐渐模式化的情况下,非虚构文学给了读者更多的现实感和更加真实的阅读体验。它积极地向人们描绘出生活的不同侧面,拓展了读者对于生活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此外我们应当思考,非虚构文学在今天的兴起是否与报告文学的文学基础有关呢?
就历时的角度而言,报告文学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在中国新文学肇始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即时性、新闻性、政论性和宣传性于一身的文学形式受到读者的欢迎。传统中国文学中起到纪实性作用的主要是散文一类,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鲁迅的杂文以短小精悍的匕首投枪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的舞台上。但是和杂文相比,报告文学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与杂文的片段性相比报告文学具有更加完整的线性行文结构,并且报告文学也被广泛地作为新闻稿件来使用。近代报告文学多展示社会大背景相下的群体事件,以体现时代特征和宏大历史视角,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宣传鼓动作用。这是在国破家亡的危机下时代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报告文学,几乎全部的文学形式都是以宣传救亡图存思想为己任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夏衍《包身工》、萧乾《流民图》和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等等。抗战时期涌现出来许多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表现新中国建设的报告文学大量发表。可见报告文学是与时代风云的跌宕同呼吸的,它的题材与社会历史大环境不可分割,具有宏大的叙事特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那就是政治功利性较强、宣传气息较浓和时效性较明显,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了它的弊端。“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仍可以毫不谦虚地说,非虚构写作对于被报告文学所弄丢的文学真实性,对于被虚构文学所弄丢的现实感,是一种拯救。”[2]
二、个体视角与群体视角的真实性之辩
就作者的书写视角的不同,其真实性给读者带来的感受也大不相同。非虚构文学的作者往往采用个人化眼光进行审视和判断,而报告文学则立足于更加宏大的社会历史角度审视描写对象。非虚构文学具有较强的个体体验性,而这种个体性给非虚构文学带来更加真实的触感,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具有毛茸茸的真实感。但是毕竟非虚构文学是以非虚构立足,这一点与需要虚构的新写实小说依然不同。并且与新写实小说冷漠叙述相比,非虚构文学的人文关怀意识是搭建在现实生活与心灵之间的桥梁,如果没有这一点,它将只是记录流水账的新闻稿件,而很难归属于文学领域。
非虚构文学的体验性与调查报告的调查性有相似也有相异。非虚构文学的体验性往往从个人角度出发,强调亲眼所见和真实感受,其动机也主要是个人化的。而调查报告的调查虽然也需要作者进行体验,但是由于作者需要服从于某种更加宏观的目的,其搜集真实的视野是需要经过过滤的,或是为了迎合时代潮流或是为了宣传某种思想意识,调查报告的作者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群体意识,或者是被期望的群体意识。
由于写作视角的不同,带给读者的整体观感也往往不同。非虚构文学的个人视角书写带给读者更加真切的体验感,作者的眼睛就好似读者的眼睛,作者的疑问也是读者的疑问。这种浸入式阅读体验与优秀的小说相似,但是小说究竟是虚构的,读者对其情感来自于故事的跌宕起伏。但是非虚构文学描绘的是真实事件再加上作者的艺术技巧就使其感染力更强带給读者的回味与深思更加丰富。“与传统的报告文学相比,非虚构写作者的姿态也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往往是以个人化视角,用一种朴素、准确的笔墨来描写生活,而不是像前者那样,写作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膨胀的形象,习惯于用夸张的笔墨来表现宏大乃至被极力拔高的文学形象和主题。”[3]
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则往往采取鸟瞰式的视角描述事件,这在真实性上就没有非虚构文学那样带给读者更强的体验感,或者也可以将之论为创作动机与读者接受的失衡。并且基于报告文学长久以来的作用是宣传,其行文模式相对固定化,其标题也具有类型化特征,以引起读者对于所述事件或人物崇高感的蒸腾。崇高感是必须的,但是由于报告文学在一定时期被错误利用,其崇高感和“不及物”的脱离生活姿态会招致一些读者心灵上的反感和抗拒。“报告文学精彩作品的稀少,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与人民的现实关注点的偏离,是作家在纷纭的现实社会矛盾现象面前把握的盲目和无力。”[4]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如今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对于思想意识的消解和对于思考人生的淡漠,而将物质作为自我价值确证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而与报告文学相比非虚构文学更加亲民更加面向生活并且作者情感更加浓烈和真挚,视角也是从个体人的角度出发,这有利于弥补报告文学宏大叙事方式的不足,读者接受感更强。
虽然非虚构文学的个人化视角下的真实性更有血有肉,但是作者对于事件的体验和对人物的寻访仍然难以避免带有个人先验观念。那么作者对于事件的书写是否带有自我价值判断的透析而将读者引导进某种情境之中呢?并且如今互联网十分发达,对于文学而言传播速度更快、受众范围也更广,这难以避免一些无良营销号打着“非虚构文学”的名头行煽动大众焦虑的事实,如咪蒙团队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这篇文章错漏百出,但是在互联网大数据的传播下很多人来不及多思考便跟风转载,而那些草草阅读后发出对人生消极慨叹的网友更是不胜枚举。“作者所提供的‘真实故事足够奇观化,能够赢得读者,获取利益;读者在阅读过程获得猎奇体验;而平台从中收割了足够多的流量。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计较真实与否的皆大欢喜的‘非虚构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流程。”[5]可以说如今的大众在消费着物质而资本也在消费和愚弄着大众。对于“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检验需要更多读者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也需要互联网营销者建立起道德良心并受到法制监管,以帮助非虚构文学免于向虚构堕落从而得到更好的完善和发展。
三、生存困境演化的真实性之辩
报告文学兴盛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时期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第一部分生活与宣传的真实性之辩中我们已经谈到了报告文学具有很强的社会历史性和宣传鼓动性,它主要表现的大环境下的大事件或者是大环境下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就生存困境而言,个人是与民族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了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志愿军战士,这篇报告文学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篇文章将抗美援朝战争与志愿军战士结合起来描写,既有群像描写也有个像描写,这些人物都有着强大的精神感染力,那就是赤诚的爱国主义。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其个人生存困境主要来自于国家和民族的困境。
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被人们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慕容雪村《中国,缺了一味药》中被简单的传销套路蒙蔽的人们追求金钱却无努力,追求成功却毫无远见,这类群体是如今一部分好逸恶劳梦想发财者的缩影。极度的金钱追求使传销者被幼稚的骗术蒙蔽,急功近利的心理被传销者充分利用。非虚构文学对于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与展现带给读者预防针一般的效果,它提示着人们对于自我贪婪和外界诱惑的警惕。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非虚构文学注重挖掘社会问题和揭露阴暗面,为了写作而挖掘为了阴暗面而挖掘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我们需要承认,今日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社会整体是健康发展的。对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应当重视并且解决,但是如果沉迷于此则有可能陷入晚晴黑幕小说的窠臼之中。“非虚构作品经常关注平民、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非虚构的文化职能是让弱势者变得可见。”[6]这是非虚构文学值得肯定的方面,而对社会积极面的调查和宣传,非虚构文学应与报告文学共同发力,走出各自的书写舒适圈向更加广阔和全面的社会各个维度迈进。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非虚构文学的成熟和报告文学的完善,二者存在着殊途同归的可能,而对于二者概念和理论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注释:
[1]宋宁《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史维度与构想》[J].《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2]王磊光《非虚构:它拯救了多少现实感和真实性?》[N].《文学报》,2019年4月25日,第018版。
[3]王磊光《非虚构:它拯救了多少现实感和真实性?》[N].《文学报》,2019年4月25日,第018版。
[4]《把脉问诊报告文学》[N].《人民日报》,2010年3月25日。
[5]信世杰《非虛构与报告文学:互为毒药还是良药?》[N].《文学报》,2019年4月25日,第019版。
[6]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J].《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