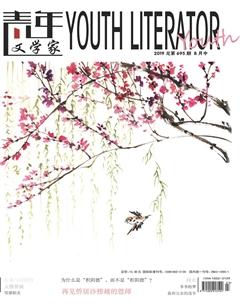《樱桃园》的结构主义解读
蒋兰心
摘 要:《樱桃园》作为现代派戏剧的代表作,融入了契诃夫“戏剧要生活化”的美学观。原本可延伸出激烈冲突的人物关系却在契诃夫笔下消解,流露出脉脉温情。本文运用“符号矩阵”分析剧中人物的多重关系,探析契诃夫对戏剧、对历史、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樱桃园》;契诃夫;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1
《樱桃园》作为契诃夫的代表作,融入了剧作家“戏剧要生活化”的美学观念,对戏剧冲突的淡化使得《樱桃园》成为20世纪现代派戏剧的先驱。原本可以延伸出激烈冲突的人物关系却在契诃夫的笔下得到消解,剧作家淡化戏剧冲突运用了何种方式?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意?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semiotic rectangle)理论对剧本进行分析,我们可将积极投身时代的洛巴辛设为积极生存(X),被时代裹挟但仍开始新生活的丽乌夫与加耶夫设为非积极生存(非X),混世寄生的杜尼雅莎、雅沙设为非消极生存(非反X),被时代抛弃的佛斯设为消极生存(反X)。
在这个符号矩阵里,呈现出多重关系:①买下樱桃园的商人洛巴辛(积极生存)与失去庄园的丽乌波夫(非积极生存),看似有尖锐矛盾,但二者并未站在完全对立的两极,反倒是呈现一种复杂的感情关系。一方面,洛巴辛亲手毁掉了丽乌波夫最后的精神家园,让丽乌波夫不得不继续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但在另一方面,洛巴辛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商人形象,为了让丽乌波夫保住樱桃园,他一直积极的出谋划策,对丽乌波夫充满了爱与感激。这让积极生存(X)与非积极生存(非X)的矛盾得到最大限度的淡化。②非消极生存(非反X)对非积极生存(非X)存在依附关系。杜尼雅莎身为仆人,穿衣说话却一副小姐模样,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生活在樱桃园内;雅沙则一直跟在丽乌波夫身旁蹭吃蹭喝,即使樱桃园不复存在,雅沙依旧恳求丽乌波夫带他去往巴黎,希望继续用丽乌波夫的钱过活。而丽乌波夫虽然贵族做派十足,但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年青一代的仆人们,靠着丽乌波夫的包容,通过寄生的方式继续过着小姐阔少般的生活。丽乌波夫宽厚的性格使得非积极生存(非X)与非消极生存(非反X)之间潜藏的矛盾消解。③洛巴辛(积极生存)是四极中的异类,唯一具有行动力和目标性。与同样出生低贱的年轻仆人们相比,年轻仆人们沉溺于享乐的时候他已经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农奴之子的命运,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当丽乌波夫与加耶夫继续散尽千金的时候,他不断提醒兄妹二人樱桃园已经岌岌可危,并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建议将樱桃园改建为度假村。最后,他花大价钱买下了樱桃园,试图用得到樱桃园消解他农奴之子的自卑感。洛巴辛渴望成为不可阻挡“巨人”,代表资本主义的他在四极中的特殊地位无疑是昭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到来,那个代表樱桃园的时代必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④佛斯(消极生存)作为旧时代的代表,遭到了其余三极的抛弃。洛巴辛(积极生存)作为新兴的商人阶级,他的生气勃勃与佛斯的垂暮形成鲜明对比;在主人尚未回到樱桃园之前,年轻的仆人们(非反X)只知道用恋爱消磨时间,真正在做事的只有佛斯(反X)一人,即便如此,老朽的他还是成为众人口中的“怪老头”;丽乌波夫与加耶夫(非X)失去了樱桃园,虽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去,但仍能选择释然,很快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而佛斯在樱桃园中照顾了四代主人,早已和樱桃园融为一体,他注定要和樱桃园一起消亡。
通过对符号矩阵四极的详细解读,不难发现戏剧冲突正是在“生活流”中消于无形。四极之中的人物形象并不具备典型的戏剧性,他们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虽有性格缺陷,但很大程度上都用爱和善良避免了潜在矛盾。在这一片静谧和谐之中,四极人物之间并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也不存在明显的对立阵营,甚至所谓的阶级剥削、阶级对立都近似于无,所有可能被激化的矛盾都因一种契诃夫式的喜剧性得到消解。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消解,“《樱桃园》外在冲突被淡化,而内在冲突——更具形而上的人与环境和时间的冲突——在另一层面上被深化”[1],才使得该剧更具独特的艺术魅力。契诃夫将樱桃园置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间点,过去的生活以令人伤感的方式结束,而新生活的曙光还未将未来照亮。就在时代给我们短暂的“留白”之中,我们看到了樱桃园的美,丽乌波夫的善良和对美的珍视。然而时代向前推进的脚步绝不会因为樱桃园的美和丽乌波夫的善稍作停留,人在这场抵抗时间的战役里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人终究是渺小的,被时代裹挟而去的园中人只能伤感,伤感樱桃园的陨落,伤感美的陨落——无法阻止美的陨落。时代发展是不可违抗的规律,樱桃园内必然会响起砍树之声,而像丽乌波夫那样懂得诗意和美的人却不是可以拯救樱桃园的人。“人类的进步竟是以失去美为代价,这是人类的命运,是人与时间、环境冲突的结果”[2]。
总体而言,《樱桃园》在悲喜交叠之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哀而不伤的故事。借用符号矩阵,我们可以发现,原本可以延伸出激烈戏剧冲突的双方却因人物自身性格和契诃夫式的喜剧性将矛盾化解,在脉脉动人之中观众更能感受到人与时间、环境的矛盾,进而上升到对美的陨落的探讨。契诃夫对历史的忧郁以一种温和的喜剧表达出来,生活在历史大舞台上的小人物們,偶然回头望去,被砍伐的樱桃园依旧是人类永恒的情结。
参考文献:
[1][2]董晓.从《樱桃园》看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J].外国文学评论.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