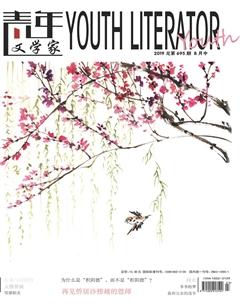莫言作品中的裂变与归宿
刘玥
摘 要:莫言小说中存在某种“裂变”,叙事的裂变对应的是主体以及意识的裂变,但同时这种裂变也各有其归宿。在阅读莫言作品的过程中先需要从宏观角度出发,把握其写作逻辑、了解其写作框架,其次,不能忽视从微观角度下对细节的探究。本文从双重英雄、双重色彩、双重暴力以及双重形态轮回四个方面来分析莫言作品中的裂变表现,并指出其裂变后的归宿以及这种归宿后的审美和伦理价值体现。
关键词:莫言;裂变;归宿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02
莫言小说中存在某种“裂变”,叙事的裂变对应的是主体以及意识的裂变,在裂变的表层下蕴含着作者莫言对作品的期望与塑造,同时这种裂变也各有其归宿。莫言在作品中寄寓了自己的情感,这是作者主体性的体现,作者要想脱离作品是很困难的,莫言在这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想法与渴望,在意象世界的生成过程中,让读者通过阅读去发现“美”感受“美”。在莫言作品的裂变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双重英雄、双重色彩、双重暴力、双重性态与轮回。
一、双重英雄
莫言笔下的英雄人物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来自各个阶层,各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嫉恶如仇,视死如归。根据其走向,我们把其分为两类:政治英雄和民间英雄。这两类英雄虽然最终走向不同,却有着相似的人生遭遇,悲苦是其人生绕不开的主题之一。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广大民众的缩影,而正是底层这种困苦艰难的环境才造就了英雄人物们悲苦的身世和豪迈的气概。莫言诉说着乡村的苦难和英雄们的悲壮,在他的笔下,英雄人物大多都带有悲壮的色彩,但是这种人物与悲苦人生际遇相斗争的过程以及英雄坦然应对失败的情节设计更能衬托出辉煌与悲壮的主题。
《红高粱》前期的余占鳌,因为愤恨和尚沾染女性而杀了和尚,当叔叔强奸了玲子,又大义灭亲杀其亲叔;《檀香刑》中的孙丙为保乡亲性命牺牲自己,侠肝义胆不畏权贵;《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一位勇敢坚强、历经苦难的母亲,她一生都在活在苦难之中,不幸的婚姻,罪恶的战争,人口家族的重担,迫使她带着孩子东奔西跑躲避战乱,她只能忍受着失去亲人、家园被毁、遭人侮辱甚至迫害的多舛命运。这三位主人公对家族命运进行誓死捍卫与抗争,是民间英雄的代表。《丰乳肥臀》中司马库为了保家卫国,抛头颅洒热血,一家十九口被残忍杀害,日军侵略时,他洒烧酒布火龙阵,切割钢梁引发大桥坍塌,并引爆了满载军火的日军火车;《蛙》中的姑姑万心,一生劳碌,双手一共接生了一万多个孩子,坚定地追随党的政策,创造出一部生育的传说,他们是政治英雄的代表。
莫言笔下的英雄有着超脱放达、不受约束的精神气质,虽然人生经历和性格相异,但是其精神气质却十分接近,血液中都浸润着叛逆习气。作家对英雄的理解和塑造主要是从生存与生命活动出发的,生存高于一切,因此他们迫于无奈走向了反抗之路,并由此获得了生存保障。莫言笔下的英雄源于不愿受人欺凌的生存意识,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往往使得民间英雄沾染上政治色彩,带有民族与国家主义情怀,从而精神的高度得到提高,作品的深度得以呈现,这是英雄的归宿。
二、双重暴力
莫言的暴力观念有两个源头:一、人种观念;二、民族国家观念。从两种观念产生两种形态的暴力,即国家式暴力和流寇式暴力,进而又分化为两种异态——生命力的喷薄与兽性的爆发。莫言的暴力观念夹杂着人种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两种意识的相互融合产生两种暴力观念类型:第一种是着眼于生命力和民族精神的暴力,态度是颂扬,第二种是着眼于兽性和吃人制度的暴力,态度是批判[1],这种双重态度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民族国家式暴力呈现出两种状态——其一是对外族侵略的抵御,莫言称之为原始生命力;另外一种是社会与国家的恐怖与血腥,莫言称其为原始兽性。前者属于暴力英雄,后者属于暴力魔鬼。
《红高粱》中集中体现了莫言早期的暴力观念,有一种《水浒传》的味道。“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帝国主义暴行的介入淡化了土匪暴力,甚至转变了其固有性质,使其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暴力经由民族大义的洗礼改变了原有的性质与色彩,与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契合。暴力源于欲望,不仅是本性使然,更有非本性的社会因素推动,暴力只有通过民族与国家因素的介入才能改变性质,才能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才能在伦理价值上为人所接受。《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蛙》反复呈现的莫言的语言暴力因为有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庇护,才有了一定的正当性。
三、双重色彩
蓝色:具体表现人物是蓝脸。蓝在更多意义上更突出一种现代意味与进步气息,似乎还有些梦幻的色彩,在夜里散发着蓝色的幽光,他就像神话传说里英雄一般的人物任务,整体形象是正面的。蓝脸就是土地上的幽灵,他是中国土地上的最后一个单干户,以不变的姿态来回应万变的时代,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象征。
蓝脸之所以单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自由主义思想中针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而是在时代背景下个人情愫的彰显,首先,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地是毛主席给的(土改),主席说入社自愿,其次这里有着蓝脸的个人情愫,蓝脸也经过了自己的一番思考:入社后干活还不如给以前的地主干活,毕竟还有一层养父子的关系在那儿。这是典型的小农思想的体现,是中国封建社会残余思想的缩影,根深蒂固,深深植根于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意识里,但是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又不免怀揣着乌托邦图景式的理想,因此既演奏着保守的主调又伴随激进的色彩。
红色:具体表现人物是洪泰岳,洪=红,名如其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为执着,而且執着表现得异乎寻常。他暗恋白氏,却碍于身份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他一辈子坚信革命,却在生命的尽头之时被定义为革命恐怖分子。红蓝两色相对,他与蓝脸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彼此性格中又有着共通性,那就是倔强,两个人在书中都是倔强的代名词,但是倔强的方式方法却大相径庭。
在作品中,大家很明显能看出作者还是略微偏向于“蓝色”的,对于红色,虽然莫言也表露出些许的赞叹,但是整个故事的走向是“抛”红“扬”蓝,这是颜色的归宿。
四、双重叙事者
《生死疲劳》中设置了两个叙事者,一个是轮回的叙事者,一个是现实生活的记叙者。在每次轮回的时候,故事的叙事者就转换为了西门闹(蓝千岁),而在讲述所有人的故事时,作者又设置了一个现实生活的记述者——蓝解放,他是一种半知半解的状态,在故事中他是不清楚西门闹的身份的,但是在故事外,他是知道的,因此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朦胧感,另外,两个叙事者的身份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两个因为蓝解放的原因姑且可以算作有血缘或者说亲属关系的存在,介于这层关系,两个人的叙事角度表面看起来不同,实则偏向一致。
小说的中心人物西门闹这一人物身份,不仅仅停留在读者阅读意识中一般意义上的故事经历者这一层面上,他的身份在深层意义上更体现为一个故事的叙事者,并由他开启了书中其中一个叙事角度。这种人物身份的界定主要与他的数次轮回有关,轮回的一次次到来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步削弱,这就导致他无法承担起情感和意识的观照和反思的功能,更无法体现其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那种醇厚的伦理道德价值。这其实带有了一种意识流的特色。莫言在两个叙事者中跳来跳去,不仅是为了更好的、流畅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更是一种逃避情感的方式,西门闹是一个情感极其饱满的人,随时随地都有情感的爆发,这是一种狂欢式的自由宣泄,每当作者觉得自己宣泄太过,想要跳出那个语境,就转而来到蓝解放这里,来进行情感的收敛,这正体现了莫言的自律性。同时这种设置也是一种意识流的体现,作者通过口吻的变化来达到自己逃避政治的目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政治无意识是通过动物性的增加实现的,这里有必须说到性态的问题。
五、双重性态与轮回
《生死疲劳》中设置了两个轮回,一个是土地的轮回,一个是生命形式的轮回即性态的轮回。这两个轮回又可以按不同性质进行划分:小轮回,西门闹从人到动物再到人;大轮回,土地所有制的轮回,即私有——共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在这两种轮回中有着一定的辩证关系,小轮回是大轮回的有机组成,大轮回是小轮回的时代表现,大轮回包括小轮回。
在小轮回中,即西门闹从人到动物再回到人这个过程中,形式的轮回蕴含着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首先是具有人的意识,其次是由人的视角向纯粹的动物视角的渐变,是由主体视角向观察者视角的一点点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最后变成蓝千岁这个叙事者,又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其中的形式意味值得深思。其中,不变的是同一个人,地主西门闹冤魂不变;变的是外在于生命的内在形式。从人性到动物性,又回到极端的人性。从人到动物再回到人,完成了一个性态轮回。
西门闹的家乡最终变成了墓地,不长任何东西(庄稼),埋着死人,连在一起,没有分别,死亡在这里是“齐物论”,齐在墓地里,回归墓地。就像文中所说的那样“一切来自土地的终将回到土地”。
《生死疲劳》是一个完整的圆圈,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也是第一句。生死疲劳,生命再堕落,生命也要继续;为了要活着,人可以死亡多次。生是第一性的,死也是为了生。最终的道德结论是: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回到土地,这句话背后的基本意向是死亡,代表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一切事物都会走向死亡,但轮回却要借助于生的力量得以实现,生死疲劳就是在无数次秉持着渴望生的执着下,在舍生忘死、死而后生的逻辑指引下完成的,死让生成为可能。这反映出《生死疲劳》抱负很大,同时也拥有着成熟的结构。其与《活着》相同,都揭示了一个道理:生活高于历史。
莫言的作品是多样性和控制力的双重展现,既具有复杂多变的形式,但是这种复杂中又有着极强的自控性。借用柳宗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句话,莫言是在用审美意象去照亮审美的人生。莫言的裂变就是这样,基于对现实的观照而归于精神的审美,从而有了归宿,这就是莫言作品中的裂变与归宿。
注释:
[1]董外平.莫言的暴力观念及其文学呈现[J].中国文学研究,2015,(2).
参考文献:
[1]莫言.生死疲劳[M].作家出版社,2006.
[2]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3]董外平.莫言的暴力觀念及其文学呈现[J].中国文学研究,2015,(2).
[4]张旭东.作为历史遗忘之载体的生命和土地——解读莫言的《生死疲劳》[J].现代中文学刊,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