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认知”与学术前沿
段炼

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艺术理论中,“形式主义”是个贬义词,虽然80年代初因吴冠中的提倡而一度正名,但随后的后现代和文化研究大潮,却使之再次成为贬义词。到了21世纪初,国内文学理论界有学者欲为“形式主义”翻案,例如赵毅衡欲以“形式论”代之,以洗恶名。对此,我深以为然,愿在本文中借“前沿”议题来讨论当代艺术理论的“形式认知”问题。
所谓前沿,一指研究领域,二指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例如,西方艺术史论界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前沿领域是视觉文化,其前沿理论和方法是图像研究和视觉分析;在中国学术界,这一前沿迟到了10多年。当前沿变成时尚,便不再是前沿,例如国内学术界眼下一窝蜂扑向视觉文化和图像研究,其势汹涌,但前沿是尖端,绝不是大潮。
无疑,中国艺术理论在20世纪深受西方学术影响,今天已基本同西方学术接轨。于是,西方学者的前沿焦虑症也传染给了中国学者:今日前沿领域究竟是什么、何为前沿理论、我们落伍了吗?
在此,本文探讨前沿的话题,首先遭遇了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若依黑格尔历史主义目的论之说,艺术主流的发展有一条类似导弹飞行的轨迹,欲知未来,可回望过去,根据已有轨迹来推导未来的发展。后现代时期的新历史主义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是惯性的,而是变轨的,未来与过去关系不大。新旧历史观的冲突,让前沿研究无所适从,那些拼命想一窥学术前沿的学者们看不到未来,遂生焦虑。
然而,作为人文研究的艺术理论,与自然科学和机械工程不同,轨迹和变轨之说,皆不能阻止我回顾历史。20世纪西方艺术理论的发展,源自四大领域:心理学、语言学、哲学、文化学。所谓理论前沿,是指这四者都各有自身的发展前沿,而所谓前沿理论,则涉及其中谁能在21世纪继续前行,指引未来的新方向。我的观察和思考是:四者相合、取长补短、以一为主、共向未来。那么,这为主的“一”是哪个一?
我先回看四大领域在20世纪的发展。
其一是心理学,以20世纪初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主。二战后英国的温尼科特理论和法国的拉康理论对艺术研究影响较大,一时竟成为西方的主流艺术心理学。同时,形式主义心理学也进入艺术理论,例如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艺术心理学,其影响直至80年代。现在,认知心理学已进入人文社科领域,也开始进入艺术理论,偏向美学研究。
其二是语言学,在艺术界称形式主义。这不仅是20世纪初英国画家理论家弗莱和贝尔的“蕴意形式”理论(可惜被人译作蹩脚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且更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从欧洲到美国的发展,以及新批评和格林伯格形式主义在美国本土的发展。这派理论自二战前崛起,二战后主导了西方艺术理论,发展出现代符号学和现代叙事学,其遗音直至70年代后期,甚至至今犹存,更新为认知符号学和认知叙事学。
其三是哲学,以德国现代哲学为主。这是从现象学到阐释学再到接受理论的步步深入和渐渐具体的发展过程,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先是海德格尔在20世纪前期发展了现象学,然后伽达默尔在20世纪中期推进了阐释学,再后来尧斯及其追随者进一步促成了20世纪后期的读者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与语言学多有交手,例如美国艺术史学家夏皮罗质疑海德格尔对凡·高《农鞋》一画的解读,后来却反被德里达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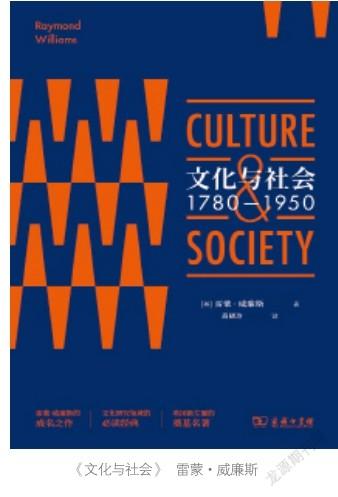
其四是文化學,以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马克思主义起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有理论和实践两者。就理论而言,先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前和二战后都以之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后有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以及再后来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就20世纪末的理论发展而言,文化研究在艺术界衍生为视觉文化研究,并与流行文化和传媒研究汇合,超越传统图像学,在艺术界发展为图像研究,一时成为学术时尚。
以上四者虽相互融合,但只有语言学理论关注艺术本体,属于内在研究,其他三者皆关注艺术以外的方面,属于外围研究。从传播学角度看,在“编码→符码→解码”的传播模式中,心理学主要关注编码,例如弗洛依德理论偏向作者动机或意图研究;语言学关注符码,故有艺术自治的形式主义本体论;哲学研究偏向解码,强调阐释者的主体性存在;而文化学则超越这三者,转而以社会历史语境来覆盖之,也覆盖其中的每一者。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而在100多年前崛起,在21世纪初以意识形态批判而俯视今日学术,有高屋建瓴之功。
一旦到达了21世纪初的时间制高点,我便可以转身看未来。既然过去百年中各种理论已将内部研究和外围研究玩遍,留给21世纪的还有什么?未来还会有前沿理论吗?
我看心理学的未来,前沿是认知心理学;我看语言学的未来,前沿是认知语言学;我看哲学的未来,前沿是认知科学的人文科学化;我看文化学的未来,前沿是认知科学的应用,例如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互补。

我们有“认知艺术理论”吗?西方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相关理论巨著出版,但相关的学术论文却在20世纪末就已逐渐出现,21世纪初则蔚为大观。问题是:艺术研究中的认知科学究竟是大众化的时尚还是孤独的理论前沿?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艺术中的认知科学大有与人工智能实现视界融合的趋势,也就是human intelligence(HI)与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协作。
协作的结果显现为上述传播模式中的符码,即艺术产品,例如奇点艺术。于是,我又来到了本文开头的“形式认知”问题。这时的艺术产品,决不仅仅是自治的图像符码,而是由作者开发并制作、由读者接受并消费的视觉文化产品,是由超越这一传播模式的历史、文化、技术、商业语境所塑造的产品。因此,要言说西方的formalism,我们应该抛弃汉语的“形式主义”贬义词,改用不带褒贬的“形式论”中性词。另一方面,我主张将中文“形式认知”译作英文cognitive formalism和formalist cognitive theory,即中文的“认知形式理论”。
用这样的未来眼光回头再看过去100年中艺术理论的发展进程,我看到了“形式认知”的生成和演进:心理学对作者编码之心理形式的认知、语言学对图像符码的语言形式的认知、哲学对读者解码之主体形式的现象学认知、文化学对外在条件之语境形式的文化认知。
这是本文所言的“形式认知”,不过,我不能确认的是,这一理论在未来的艺术研究中究竟会成为学者们趋之若鹜的时尚大流,还是高冷尖端的小众前沿。
我希望是孤独的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