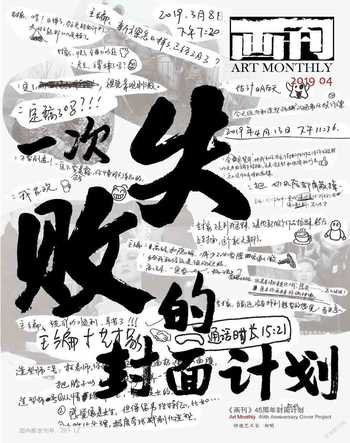梅洛-庞蒂论风格的概念(下)
[美]琳达·辛格
(接上期)
作为一种普遍的本体论范畴的风格,在考察梅洛-庞蒂将风格作为一种本体论范畴来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它被设定用作的更重要的哲学目的。在梅洛-庞蒂努力从观念的领域之内重构知识的根据,并努力阐释于一个有限的拟人化的意识中,意义在世界上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一种语境之中,这个概念就呈现出了意义。我的论点就是:风格的概念对那种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作为透视法(perspectivalism)——梅洛-庞蒂的本体论的核心——的定性关联起作用的。风格是成为一种具体观点的情感表达的或形态上的结果。作为由它们的交织而产生的现世意义的领域,风格穿透了观念及其对象。
在观念的客观阶段,风格作为事物之身份的现象存在。风格在它的本质或世俗的特殊性中揭示了事物。通过它的风格,观念的客体以它是什么和它如何是什么的方式呈现出来。思考一下梅洛-庞蒂对一块木头的描述:
“所有的事物都是通过一种承载了它自己的根本性质的媒介向我们显现的。这块木头既不是众多色彩和有形数据的聚集,甚至也不是它们的完全形态,而是某种散发了一种木的本质的事物。这些“感觉数据”调节了某种主题或者阐明了某种风格,这种风格即是木头本身。这种风格也围绕这块木头和我拥有的针对木头的观念创造了一层重要意义。”[9]
在这个语境中,风格被用来强调,在普通的观念中,这块木头不是作为一组特性或作为一套必需的特征而向我们呈现的。在这里,本质是从气味或芳香的意义上被用来暗示这块木头的木质的独特外表。透过这个例子,梅洛-庞蒂想要证明的是:甚至在自然物品(没有明显被人为目的渗透的物)的例子中,也存在一种内在于物的独特外表、一种物质与性质的融合,这种性质在物的本质中构成了此物。这块木头的木质的构成并不是明确的,它被感觉或被理解为一个需要回应的意义的场域。因此,风格的影响更加戏剧性地给人以一種感知的和暗示的机动回应的感觉,而不是可辨别以命名的某物。风格是处于需要一种感知和机动一致、对我们预期的一个调整,而且需要对物的期待的物之中的。这对使用的对象来说尤为正确。一种器乐的风格存在于那些细节之中,当演奏的时候,音乐家必须调整这些细节。如果我们将这块木头视为一把有扶手后背的椅子的一部分,风格是如何能暗示一种机动的和姿势的调节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晰了。木头的风格如今作为某种允许受限范围的姿态的僵化或弹性来呈现的。在这里,这块木头的木质用来确立一个情感表达的空间或气氛,完全不同于那种垫得又软又厚的扶手椅所带来的那种感觉。
从结构上来讲,基于物在其本质中是可辨认的,风格用来实现一种感知的终结。风格固定了轮廓的和谐流动,从一点观看的物到被看的物,这些轮廓为运动打下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风格发生作用的方式类似于胡塞尔(Husserl)的思想核心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代表了对内在于感知中的透视性的一个回应。因为感知的综合总是在不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发生的,一定存在某种结构能确保流动的外表的凝结。对胡塞尔来说,感知的对象的统一有赖于在意义的核心或内在的终结处徘徊的轮廓。但是,对梅洛-庞蒂而言,物的综合完全是实践的和感知的。对我们来说,物或个体能保持一个持续的存在,因为它是显现的一贯方式,即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转换的。风格是梅洛-庞蒂描述感知统一的突出特征的方式,而这种感知的统一永远不能在思想中被完美地重组。
风格亦是梅洛-庞蒂描述鲜活的身体的统一以及作为一种具体意识的他者的存在的方式。他的部分意图是在鲜活的身体与艺术作品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类比,基于这样的理由,即它们都是能够散发超越它们的意义的表现领域,并且能够与世界中的其他意义发生交织。
鲜活的身体被其风格以一种类似于风格在绘画中实现统一的方式所统一。两者都作为允许进一步显现的定性的情感表达的终结而存在。身体图像具有一种风格的一致性,因为,与艺术作品一样,它是一种观点的表现工具。鲜活的身体不仅仅是部分内容和功能的一种排列,也是被肉体的有意图的映射联系起来的协作的统一。借助于风格,人类行为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姿势——正如加缪(Camus)所暗示的一种“愚蠢的展现”——也是一种观点、一种存在的独特方式的旋律优美的展现。对梅洛-庞蒂而言,具有一种风格是成为一个身体和拥有一段历史的一个相关物:“我是一个心理的和历史的结构,并接收存在作为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风格,我所有的行为和思想都与这个结构相关联。”[10]风格构成了意义的地平线,将他者揭示为一个朝向存在、与我自己的世界相似又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一个存在、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当在什么提及为他人思想的问题的语境中思考的时候,这种思考就呈现出特别的意义。只要深思被视为一种意识的存在的典型证据,他者的存在对哲学而言就是一个难题,因为他者的内在生活就其本身而言是得不到的。相反,风格的概念稳固了作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的他者的直接可达性。他者并不存在于其活动和姿势的流动之后,而是贯穿于它们之中。它的完整性并不是概念的一致性所具有的完整性,而是一个直接呈现出来的存在计划,尽管我不能重构它内在的运作。
个体的风格是匿名的、个人的、继承的和创造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混合之物,它就像个人和他所居住的世界之间的意义的模糊交换。风格是作为自由和真实之间的一个交织,作为一个给定情况和对这种境况的超越的挪用而出现的。一种个人的风格从来不简单地是给定的或被选择的。它是建立在存在和具体化的情况之上的,也是对它们的一个回应。它构成了一种和谐一致性的确立,将存在的元素集合为带有明确方向和特征的一个生命、一个计划。风格确保了我的稳定存在,尽管也允许成长和变化的可能性。
当我们将之与病理学的情况对比的时候,一种风格的整体化功能将会变得更加清晰。在这种情况之中,一种风格将存在与一种有意图的流动性相联系起来的能力主要是不存在的。施奈特(Schneider)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体和世界都被残留在其脑中的弹片(schrapnel)损坏了。这种情况导致施奈特拥有受损的感知功能以及一个从性质上来说极为贫瘠的世界。他有交谈的困难,因为他甚至连一个故事都记不住,除非一次接一次地熟记这个故事。他不能用手势自然地表达,而只能通过营造一个需要那种姿势来表达的情境才能做到。在缺乏有目的的联系——通常为健康的主体呈现——的世界中,施奈特正在实践一种垂死的风格。他的风格是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仪式化存在。在施奈特的世界中,为健康的主体而发生的意义的流动交换是固态的和僵化的。
但是,在通常的观念中,风格渗透了主观的阶段。据梅洛-庞蒂所述,观念“已然风格化了”[11]。观念变得风格化是因为在它是揭示一个不可避免地超越它的世界的条件的同时,它情不自禁地构成并表达了一种观点。并不存在对脱离了透视状况的世界的明确表达,也没有揭示了自在之物的观点。通过给予允许在没有牺牲存在稳定性的条件下进一步展现的终结的承诺,风格将感知的领域作为一个活动的范围确立起来。在人类方面,风格提供了一层普遍的连续性和目的,此目的将这个世界集合为一个意义范围或对它的承诺。在有限的条件下,风格刻画了有关存在的一致性的本质特征。
引起梅洛-庞蒂兴趣的风格的概念所处的最后语境处于认知和思考的领域之中。风格是作为预先揭露(predisclosure)或提前拥有的阶段的过程和理解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过程的暂时性是这样一种事物,即它的客体对象首先将它们自己作为优先的明确阐释、意义的承诺揭示出来,正如梅洛-庞蒂所表述的那样,“每一个概念首先是一个水平的概论,一个风格的概论”[12]。
在我们通过分析的过程透彻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之前,梅洛-庞蒂说:通过同化其风格,我们意识到了它的意义。这位哲学家的作品以一种类似于艺术作品之影响的方式得以为我们所理解。两者都是等值的系统,此系统确立了一个朝向它们阐明的世界的一致方向。因此,梅洛-庞蒂认为哲学是一种本质上的阐述活动,为了交流,这项活动要依赖其风格的前概念的能力。尽管不是在它预先假设的情感表达的语境中前行,而是依赖于作为其主题宣言的一个背景的意义的基本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梅洛-庞蒂将哲学理解为总是参与到其语境的恢复以及对它的超越之中。当他将现象学描述为一种哲学化的风格时,他是在号召我们关注这一事实,即现象学的意义是一个处于生成之中的意义[13]。与在一套普通的信条或原理周围聚集它自己的教条不同,现象学将它自我视为一个从实践发展而来的运动,及其通常的情感表达的依据和目的的一个预先揭露的意识。它作为一种运动的发展表明了按照一套意义——只有在回顾中才变得清晰——行事的可能性。
对于一套现实世界的哲学来说,风格的最终成果是:它使那些稳固了在还未为思想所透彻了解的世界中的意义的可能性结构变得清晰明了。作为人类有限的定性关联物,风格构成了真实性和观点向一种接近生成的模式的转变。风格提供了一套没有深受怀疑论之害的彻底的透视体系的前景。普遍说来,在艺术和人类事业中,风格的多样性提供了关于这一事实的有力佐证,即这个世界将绝不会被简化为一个概念的透明物。通过在小说语境中诉诸风格的概念,梅洛-庞蒂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表现性的领域,而且针对这个世界,将总是存在可以述说的东西。
注释:
[9]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科林·史密斯(Colin Smith)翻译(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
[10] 同上,第455页。
[11]《符号》,第455页;ILVS,91。
[12] 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阿方索·林吉斯(Alphonso Lingis)翻譯(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37页。
[13]《知觉现象学》,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