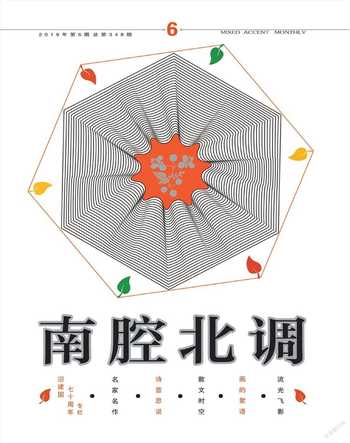好大一棵树
秦越 吕东亮

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旨在“重新评估我们这个民族的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力量”,探讨“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主题,因而具有“寻根文学”的某些意味。李准曾在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代后记中说:“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如果“寻根文学”的最早意向在1979年《黄河东流去》(上集完成于1979年)中开始萌动,那么到了1985年,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响亮的文学口号。李准在代后记中说:“‘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黄河东流去》所呈现出的独特感人的艺术魅力,与其中频繁恰当地使用比喻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比喻中喻体的选择更是生动贴切,形神兼备,特征突出。
郭建宗先生是著名作家李准的外甥,与李准接触较多,由于毕业于洛阳师专中文系,对李准的生平与创作有着丰富的体会和独到的理解。2018年12月27日,我们根据事先的约定,奔赴洛阳,对郭建宗先生进行访谈。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涉及内容十分丰富,这里选取与李准创作紧密相关的一些内容并进行了整理。
秦越(以下简称秦) :郭老师,您好。根据我的了解,现在学界关于李准的传记性的著作,影响比较大的是河南著名评论家孙荪先生的《风中之树——对一位杰出作家的探访》,这本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知道您读过没有?您认识孙荪先生吗?
郭建宗(以下简称郭):我和孙荪先生有过两次碰面,但是没有直接的交往。一次碰面就是1982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后。李准当时正在辉县百泉宾馆写《黄河东流去》。在他写《黄河东流去》的那个时候,我正在洛阳师专上学,然后,我也去了那儿。当时,孙荪和文艺界的好多人也都在那儿,这是第一次会面,还照了一张合影相。第二次见面就是在李准的铜像落成的时候,有个活动他也来了,但是我们之间并没有交往。他的《风中之树》,我看过,而且看得比较细致。我觉得写得不错,但也有我不认同的地方。
秦:李准的文学纪念馆为什么会放在洛阳理工学院?当时是如何考虑的?我们觉得洛阳理工学院是一所工科院校,学生们对于李准可能缺乏了解和认识。如果放在洛阳师范学院,会不会更合适一些?
郭:是这样的。当年,李准常回洛阳,也常去洛阳大学,洛阳大学后来与另一所高校合并为洛阳理工学院。洛阳大学的校长焦金山当年聘请李准做名誉校长,李准就经常到洛阳大学去讲学。因此,李准和洛阳大学就有了这个关系。到后来,洛阳大学换校长之后这个关系也一直在。李准生前,曾表示自己身后可以回归洛阳,叶落归根吧。李准去世以后,骨灰的存放是亲属们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李准的长子李克勤就想把李准的骨灰到底安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找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屯村的祖坟都考虑过,但是因为当地开发的原因祖坟的环境已经不行了。而当时洛阳大学和孟津县都提出把李准的骨灰放到他们那里。最开始李准的家人也有把骨灰和铜像放置在洛阳师范学院的想法,但是当时洛阳师范学院的校长叶鹏先生不大情愿这个事情,具体原因就不说了。因为洛阳师院当时没有这个意愿,而洛阳理工学院对这个事情非常热情,所以到了2003年清明节前后,李准铜像在洛阳理工学院落成之后,就把李准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到了洛阳理工学院,就放在了李准铜像的下面。这个事情好多人都不知道,后来我的舅妈董冰(李准的结发妻子),去世以后也合葬到了那里。
秦:在之前我与您的电话联系中,感到您十分注意文学界对于李准先生的评价。孙荪先生在《风中之树》中评价李准先生既有“猴气”也有“憨气”,属于“外表憨厚,内心透亮”,十足的河南侉子形象。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个评价?您印象中的李准先生是什么样的形象?
郭: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浅表,没有深入到作家的灵魂深处。他说这个“憨气”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李准的外表以及他对外的一面,也就是外表所表现的。他说的“猴气”,是内心透亮的意思,是说李准爱在内心里面琢磨一点什么事——我要怎么做,然后策划怎么做。实际上,孙荪先生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浅表,他只是从一个外观来看,并没有深入到李准这么一个作家的内心深处。从新时期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对李准这种批评是很多的。这些年来,对李准的评价,不管是好评差评,很少有人说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李准写《黄河东流去》的那几年时间,还有《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热映的时候,文艺界对李准的批评非常多,我耳朵就能听到好多这种批评,这种批评会影响到孙荪先生,当然他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这种看法。实际上,他们批评李准的是什么?就是他跟形势,作品图解政策。到了《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轰动的时候,文艺界的人,包括评论家和一些作者都认为李准又跟上了一个新的形势。这里面当然不乏有同行中的人,看到别人的热闹有一些不舒服的缘故。同时也有的人认为他是从那时(十七年时期)跟形势一直跟到现在。关于李准跟形势这个事情,我是有我自己的看法的。当然对于文学来说,我不是一个行内人,但是我对李准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在那个年代不是谁跟不跟形势的问题。我曾经说李准是有双重的悲剧的,第一个悲剧就是,在那个年代,你比如说李准手里有一支笔,李准的笔是自己拿着下面,上面还有一只大手在拿着。所以说,上面的大手拎着那个笔头是不动的,作家所能活动的只有在他以笔杆为半径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要么你可以不干创作,要么你当作家就必然要跟形势,而那个形势也非跟不可。第二,就像李双双、韩芒种这样的农村新人形象,这个不是李准要写的,而是从上到下、从党中央到老百姓,都要求要写这种人物,当时这种人物写出来以后走到哪响到哪,那个时候谁批判它?到后来分田到户了,有人才说,哦,那是集体的,假如我们回到分田到户那个时代,再看李双双、韩芒种这些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价值观依然是值得肯定的。现在如果有集体了,有人拿集体的东西,偷集体的庄稼可赞,还是韩芒种、李双双的这种打破情面维护集体利益可赞?如果说,这样是跟形势,那么我说这种形势是该跟的,不该批评。还有一条,李准并不跟他无法认同的形势,这一点很少有人说,但这是我的看法。文学史里面提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文学有一种说法叫“8亿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说的是浩然,浩然这个人就才气来说,从《艳阳天》来看,绝不逊色于李准,他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如弯弯绕、马小辫儿等都鲜活得很,但是这些形象所存在的问题都是跟形势跟坏了。具体说都是跟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因为跟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才引出马小辫杀了萧长春的孩子等有些令人惊异的情节。而在那个时候,李准没有跟,没有跟阶级斗争这个形势。不知道在文艺评论界有没有人提到过李准这个问题,李准在那个时候写了《冰化雪消》《春笋》,没有跟阶级斗争的形势。《艳阳天》大概是在1962年、63年写的。(秦越按:《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实为1964年)就是在那个时候,李准还有自己的坚守。还有一个例子,关于李准不跟形势的,这是别人不知道的而我知道的。《大河奔流》这个剧本是在1975年创作的,当时那个32开本的《大河奔流》的剧本拿到过我家,我都看过。到了1976年的时候,就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前的那几天,毛主席是9月9号去世的,我是8月31号和我妈到郑州的,在李准家住。这时候,《大河奔流》这个剧本已经写出来了,当时就是上头掌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也知道有这么个剧本,他们也非常想重用李准为他们那个意识形态服务。有《大河奔流》这么好的题材,派了导演来和李准说想拍《大河奔流》。这个导演就是李文化。李文化是当时《春苗》《反击》两部电影的导演。(秦越按:《春苗》的导演为谢晋等人)那时候《反击》等电影,都是反映造反派与走资派斗争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回潮路线斗争。李文化来,李准就是不跟他合作。等张瑞芳她们来的时候就同意合作。如果说跟形势,当时这些掌控意识形态的最高层派了导演来要拍《大河奔流》,李准却拒绝了。还有一个事就是《新松赞》这个事,孙荪先生也写了这个事。我希望你们研究李准也不要回避这个事。我说一下《新松赞》,就是说它跟形势还是不跟形势的这个问题。那时候李准住在省干休所,一楼一套房子,顺门洞上去,三楼有一个套间,在那里面写作。我和我妈去的时候,就在那个套间里面多加了一张床,我和我妈住在那个套间里面,当时那个《新松赞》剧本还有曲谱,还是油印的本子,双页钉起来,加上曲谱这些是很多的,厚厚的两本就在他桌子上放着。我就是在桌子上面看了《新松赞》的剧本。当时是魏云演了造反派的头子。有一天我们在吃饭,李准吃了饭上去之后下来了,非常紧张地说,谁拿了那个《新松赞》的剧本,问了大家大家都说不知道,李准说害怕是克威拿了,克威这时候在工厂上班,李准说赶紧跟他打电话问问他,看看是不是他拿的,然后他就去打电话了,去打电话的时候,我妈说,你舅舅到底在找什么?我说我舅说他厚厚的两本书不见了,我妈说,哎呀,我嫌枕头低,放在枕头下面了。我赶快跑出去把我舅舅喊回来,我舅舅才算松了一口气。为啥呢?实际那几天李准对《新松赞》的心情我是很清楚的,上面的人让他写,给他定的就是要写一个反对走资派的豫剧剧本,这个正面的主角要是个女的,還要是个造反派,因为1974年造反派突击入党,提拔了相当一部分造反派分子。上面要求写走资派要写到地市级领导,他刚开始写的是乡镇级。你看《春苗》里的领导是乡镇级,这时候我看的时候走资派还是县委书记,没有到地市级。李准说我就不把这个剧本拿出去。但是对外呢并不说我不愿拿出去,只说我在修改,其实这个东西当时放在家里并没有进行修改。具体他在等什么呢?就是他说的,毛主席现在身体很弱,到“那一天”他也算有个盼头。李准的堂哥也就是我的三舅李如汉,是301医院的,他参与了最高层的医疗队,所以知道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李准说这个东西拿出去,80%的群众要骂我。根据这个事儿,你想想,说李准跟形势这个评价确实很委屈李准。

秦: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看,李准在上世纪50、60年代写的作品,一方面确实是跟形势,另一方面他塑造的人物对老百姓来说也是有益的,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老百姓也很欢迎。并不是说李准为了跟形势而创造出一些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形象,比如李双双、韩芒种这样的形象,他是上面的意图也贯彻了,老百姓内心的声音也表达了,就是说结合得很好。不是说单纯地贯彻上面的政策,却不顾下面老百姓的感受。
郭:再说到跟形势,我们可以看李准的作品《大河奔流》和《黄河东流去》。通常是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同一个题材,都是先有小说,然后再有电影,这里头是啥呢?这里头是先有剧本及电影,然后有小说。《大河奔流》,我说是1975年就有的剧本,这个题材很感动李准。但在那时候,只能写《大河奔流》那样的作品。但《大河奔流》应该是在1979年春节前后公映的,79年大家的这种审美趣味都已经提高了,已经认为《大河奔流》中李麦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不对劲了。这就是李准为什么认为这么好的题材被《大河奔流》给浪费和糟蹋了的原因,所以才要重新写《黄河东流去》。在百泉宾馆那个时候,他把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跟我讲了,他原本在电影《大河奔流》里面还写了一段李麦年轻时候的一个爱情故事。因为那时候文艺界和社会上关于爱情的禁锢还没有完全消失,79年公映电影《大河奔流》,片中把人物内心的感情尤其是爱情压下去了,这里头就有李准无奈的地方。在《大河奔流》中他要塑造李麦,写李麦的爱情,给电影里的李麦形象抹上几笔桃红色,那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是那时候的样子,不是这样就不行。这就是一个作家在那种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之下的委屈和无奈。李准的作品,比如《老兵新传》,我觉得从改革开放前那个角度、改革开放前那个意识形态来批,没法批,按现在的意识形态来批,也没法批,没有可批的;所以说上世纪70年代批李准,就没有一个人提《老兵新传》。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一直到《老兵新传》被人遗忘了。我是60年代上小学时候在《春笋集》里面看到《老兵新传》的剧本。没上学的时候我是在那期《上影画报》中看到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影画报》的“上影”是什么意思。在那期《上影画报》中刊登有剧本《老兵新传》,还有剧本《三八河畔》,看那个剧本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电影《老兵新传》我大概是两个月前才从电脑里面看了。这就是说,你给他一定的自由,他就会出好作品。《大河奔流》他没有这个自由。对于说他跟形势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样看的。
秦:郭老师您是哪一年出生的人?您在洛阳师专读书是从哪年到哪年?

郭:我是1954年出生的人,79年考上洛阳师专,82年毕业。在这里待了8年,当时在中文系。
秦:您读这个中文系是不是也跟李准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李准对您读中文系有没有影响?
郭:没有关系。我是从小十几岁就开始学中医,一直到现在,学中医时候我还上着小学和初中,后来各村都办了个戴帽初中,两年制,我读了两年。我是在72年春节前初中毕业的。毕业以后,那时候是推荐上高中。推荐上高中,我的家庭成分根本不符合条件,我们村里边这一届初中毕业了40来个人,一般只能推荐5个人上高中。我根本连被提名都不可能,我就回家当农民了。一边当农民,一边学中医,一边给人看病。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教育部门有个中医带徒招生考试,我就去考了。然后到报志愿的时候,中医带徒被取消了,就78年的这一年,中医学院不收文科生,就把我挤兑到了中文系了。要说李准在文学上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一,我的舅舅就是作家,我从小看他的书,可能在意识上对文学更关注一些。第二,李准严令我不准搞文学创作。他说你们可别弄这个,这个可不好弄。其中包括他受的委屈,他说这个可不好弄。他说他的成功是极其偶然的。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我在洛阳师专中文系读书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有作品,我没作品。这里有几个因素,一个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向往文学,很想当作家。为啥呢?他们没见过作家,都觉得那作家如何如何。我呢,跟一个名气这么大的作家有零距离的接触,作家对我来说没有光环。但是他们觉得作家有光环,所以很痴迷。另一方面是这里头这种凶险、这种委屈他们也更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努力要出书,把文章变成铅字的时候,我其实很冷静!我非常冷静。为什么冷静呢?因为我知道,一个作家真正成一个大作家,他得要一个什么样的底座,如果这个底座呀没有那么大,他的尖顶恐怕也尖不到哪去。我自己呢,第一,對作家这个光环没有羡慕;第二,对作家那种凶险、那种苦衷、那种委屈啊深有了解,不去向往那个东西。从另一方面说,政治家或者说官家,印把子、枪杆子,对你这个笔杆子的这种影响是无所不在的。
秦:当时您所阅读的李准的作品是李准亲自给您拿过来看的,还是您自己主动看的呀?
郭:都有。最早看的时候是在大队文化室,那时各个大队都有一个文化室。60年代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看过《春笋集》连环画,那时候很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连环画,比如《冰化雪消》连环画,《春笋》那么短的小说也被改编成连环画。张瑞芳的剧照,精装、绿皮的《李双双》电影剧本,是从郑州拿回来的。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我手里,然后被同学撕了。也有直接是从我舅舅那里拿回来的书,也有他寄给我的书。
秦:李准一有什么好作品,会不会急着与别人分享?
郭:他有这么多亲属,亲属也要看,他也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下。
吕东亮(以下简称吕):我去年9月份,到北京
参加青创会(“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中宣部黄坤明部长在讲话当中提到一些作品,改革开放前的作品提了七八部,其中就有我们河南的两部,《朝阳沟》《李双双》。从文学史上考察,可以说,在上世纪50、60年代,李准的农村小说在国内是顶尖的,对很多作家的创作都有影响。您如何看待李准先生作品的影响?
郭:在我看来,解放以后成名的作家,再没有比他高的。周立波是在解放以前成名的,包括孙犁、赵树理都是。李准在当时很火,他能火到什么程度?60年代,我妈去郑州,到郑州下了火车,那时候有蹬三轮的,我妈说去工人新村。人家问工人新村在什么地方?我妈说是去省文联。省文联这个词我妈是用洛阳话说的。那蹬三轮的听不懂,最后也说不清楚,没法交流了,我妈说,我兄弟是李准。人家一听李准就知道要去省文联。那时候李准作为一个写书的作家,是家喻户晓的。
秦:说到李准创作之路的成功,您是怎么看待他在创作上取得的这一系列的成就的,包括李准先生说他的创作之路不可复制,充满了很多偶然,您怎么看这个偶然性?
郭:首先,我认为李准这个人艺术天赋是很足的。天赋很足,這个条件很难学,因为天赋是天给的。从容貌上来看李准,李准的长相非常聪颖,天庭宽阔。
吕:李准后来说自己是蒙古人,他是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蒙古人吗?
郭:知道,以前知道。因为他家有家谱。他们整个李氏家族的家谱是非常厚的一本书。李准小时候看的家谱大概是在上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编的。家谱最后的序言就是李准的爷爷李祖莲写的。这就是你们说的条件,他家里有这个文化底蕴,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天才还是第一。你从李准这个容貌上看,他是不一样的。李准的艺术表现力,有几个地方可以说那是非常顶尖的,大家都说《不能走那条路》好像没有什么艺术含量,好像就是跟了当时那个形势,那个时候其实并无形势可跟。那时候还允许买卖土地的,还没有集体化的政策,你要说那是跟形势,也只能说是形势跟了李准。只能说李准具有超前意识,所以他想的问题恰好和高层想的问题想到一块去了。这也是他的天才之一,不是谁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能走那条路》有人就觉得整个作品里面也没有什么华丽的用词,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立意,就是平铺直叙。但是,《不能走那条路》里面有一个情节是世界一流的,就是宋老定去步步人家张栓家的地,宋老定就是在步地的过程中精神崩溃了。就这个情节非常厉害,可是我没看见任何评论说到这个。你也提到李麦和海青牛那几段对话。那几段原话我不大记得,但是艺术水平特别高。李麦意思就是说我嫁给你海青牛了,可是海青牛那么大年龄的一个光棍,他不敢娶我。然后李麦就说我这么大个闺女,难道我还能去要饭吗?这句话的思想高度是非常高的,在那种情况下就有这种爱情语言。还有海老清,就是保长派他差那一段对话。海老清在和保长争执中,那个保长说那保长你当吧,海老清接下来这句话特别厉害,我屁股下没坐那两顷地。特别厉害。
秦:我们刚才谈的基本上都是李准的一些文学作品,但是其实他的影视作品也非常多,而且很多都不逊色于他的文学作品。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李准在创作了《黄河东流去》之后,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影视创作中。是因为什么呢?他对影视创作是不是有一种偏爱?
郭 :不是的。到了80年代《黄河东流去》出版以后,李准在创作上是有规划的。这也就涉及了我之前提到的李准的双重悲剧的第二重——李准的身体不行了。85年左右李准得了脑血栓,到2000年初去世,这中间跨了15个年头,身体不行了。他是84年春天回到洛阳,到秋天才回到北京的。从春到秋这半年时间,都在洛阳。当时我舅妈的妹妹是洛阳自来水公司的,人家那边给他找了一套房子。夏天的时候,有一次,我爸,我,还有我舅舅我们三个人,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一直相处在这谈话,也谈文学,当然什么都谈。那时候他谈他的小说创作的规划,他说原来那些东西我以后不做了,我要做大的东西。其中,他说过一个我现在印象比较深的作品,说得比较多,题目是《天宝遗事》,写唐玄宗和杨贵妃。他说那么多写唐玄宗、杨贵妃故事的人,他们都没有弄懂杨贵妃和唐玄宗是怎么回事,唐玄宗他会缺女人吗?为啥唐玄宗就偏偏喜欢杨贵妃?他就说从史书上或者是从资料上看到的,说杨贵妃好谑浪。他就分析出他们俩之间互相愉悦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天宝遗事》应该是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后来大概是一个字也没写。但是他有规划。
吕:从1985年到2000年这15年里,他的病一直非常严重吗?
郭:他的病也不是一直很严重。他2000年2月份不在了,不在之前那一年是比较严重,行动很困难,到最后是偏瘫了,话也说不好。
吕:李准去世之前的14年当中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关于李准80年代以后的情况文学界和学术界目前拥有的资料都比较匮乏。
郭:首先是他自己身体坏了,他不太敢写了,家人也说别写了。据说,90年的时候,上边曾经有让他做文化部长的意见,前头文化部长是王蒙。一方面,李准对这个省部级这样的级别不是很在意,另一方面我大舅也不让他做,主要还是身体原因。所以李准去洛阳大学当名誉校长来讲学这些事情都是在这个时段里头。为了身体,为了保健,他就写书法。李准还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李准书法选集》,书名还是原来那个书协主席沈鹏给他题的字。
秦:李准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那应该是个副部级的实职。他是在哪一年离职?
郭:这个我不太清楚,李准还说过一句话,说巴金在世,谁也别想当主席。哈哈。再者他也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代文学馆也是个副部级单位。
秦:李准是“文革”之后就在北京,后来几乎没有再回河南,就是说没有在河南任职吗?
郭:他是在“文革”之后到北京的,但76年写《大河奔流》的时候还在河南,他的编制单位还都是在河南省文联,他应该是80年以后才调到北京中国作协的。
秦:李准晚年从这个作家身份转换到这种领导身份,他自我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郭:他表现出来的是对这个领导身份实际上是不在意的。他就是作家,只是说根据他当时的那种名气和影响,给他一个现代文学馆馆长职位或者是让他担任作协副主席,这实际上都是作家身份的一个副产品。
秦:李准在创作《黄河东流去》时,上下两册是时隔5年之后出版的。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其中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创作的《女贼》被批判,还有就是李准与李克威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清凉寺的钟声》也受到了批判。然后,李准还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陈情,不知道这个对李准当时创作《黄河东流去》是否有影响?政治形势的变幻对李准80年代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郭:这个政治方面的问题对他的创作没有啥影响。李准晚年作品不多主要还是身体不太好。一方面是不能继续进行写作了,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文化部长也没有做成,都是身体的原因。所以我说双重悲剧,这个身体确实是很大一个因素。我常说如果不是85年的脑血栓,现在我们看到的李准绝对不是那样,他可以用更多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如果不是脑血栓,像84年他说的关于唐玄宗、杨贵妃的题材的创作,要写的大部头的作品现在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李准呢,可不是现在我们已经盖棺定论了的李准。他的才气可以创造出来、喷发出来许许多多精彩的东西,这个可能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
秦:李准现在的家庭状况如何?他的文学创作对他的孩子们有什么具体影响?
郭:李准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是克勤,大儿媳妇是曹宝琴。这个老二叫克都,与妻子离婚了,没有再娶。老三是克威,他的第一个妻子就是严歌苓。后来他们分别出国了,到不同的国家之后离婚了。离婚以后,克威在澳大利亚娶了一个还是中国的妻子。这个老四就是小六(李克坚),小六的妻子叫廖威,也离婚了,小六在香港。大女儿叫李小品,小女儿叫李笋子。
秦 :李克威、李克勤、严歌苓他们也创作一些作品,您怎么看?
郭:是这样的,这个首先要从创作条件这个表面的东西来说,他们都比李准强,他们都是作家的儿子,有这么好的生活待遇。但是,我跟你说,天才条件不够。李准那个天才条件他们没有,包括克勤都说,唉呀我爸那个我们可弄不了,我可达不到。李克威的《女贼》当时是很轰动的,但是,现在李克威好像也在写什么东西,也没拿出什么很精彩、很热闹的东西来。要说李准对他周边人的影响,就是说在这个创作里产生的促进作用,我觉得是严歌苓。严歌苓亲口跟我讲过。我问过她一些创作前的准备,她就提到李准那个家庭,包括在李准家做儿媳妇的经历。这个家庭对她创作的影响是一种促进性的东西。不过对我是促退性的影响,李准不让我搞创作。
秦:您和严歌苓有交往吗?可否谈谈您对她的创作的看法?
郭:我和严歌苓的交往还是比较多的。后来,严歌苓与克威离婚后到我这里来过好多次。最早她来的一个原因是啥呢?她听李克威说的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老头被说成是反革命、老地主,就被儿媳妇藏在红薯窖底下,这个后来被发现了。她觉得这个故事、这个题材很值得发掘,很值得写。2002年秋天,她从国外回来,找到我舅妈董冰,董冰说这个事就是在洛阳发生的。严歌苓就表示要回洛阳找这个故事,说你跟老家那些人联系一下,给我帮帮忙。我舅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歌苓现在回来就是要挖什么什么故事。她回去了,你给她帮帮忙。这之后,她是做了非常非常充足的准备,连野营的东西都准备有了,她拉上廖威,就是小六的媳妇,她们都是好朋友。然后,俩人从北京开了一辆汽车,廖威开着车回来的,车上带着铺的铺盖。为了挖这个故事下这么大功夫,准备野营。这俩人都当过兵。她们到洛阳后我接待了她们。后来我就问回来啥事,她们就说是为了进一步挖掘这个老地主的故事。我说你算是找对人了,你要是想找到这个地方,我现在可以给你说,一个小时我就能找到。我说这个地方在伊川县,一个叫怀庄的村,当时非常轰动,还被辟为阶级教育展览馆。后来她们在洛阳住了一段时间,我和我家属我们一块去找到那个地方,正好当时那个阶级敌人的儿子还在,我们对他做了个采访。这就有了后来的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婦》,事实上这个人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是咋回事呢?这个伊川有个彭婆镇,出龙门石窟南就是彭婆。那个地方民性强悍,陕西人说河南的刀客来这边拉票子(绑票勒索钱财),来这边抢,实际就是彭婆镇那一批人。我大伯都被他们那边人拉票子拉去过,另外就是李准写了他的三叔被绑票,也是那里的人绑的。他们自己很剽悍,然后拿刀动杖。当然,他们刀客各家之间也会有矛盾。那叫打野,说打野两个档次,第一个档次是千门杀绝;第二个档次,所有男丁,哪怕是满月的小男孩也被杀光,就剩女的。这个所谓的阶级敌人老地主什么的,就是一个绑票大户,他跟另一家绑票的有大仇。洛阳这个地方人把解放军叫八路军,把共产党也叫八路军。到后来这个八路军来了以后,另一家绑票的参加共产党了,土改时人家就是农会的人,解放以后人家就是村里边合作社里的社长,大队的书记。人家一靠上共产党,他们就不敢留了,然后就背井离乡跑了。跑到山西,具体什么地方不知道,在那落户了,这边也不知道他们到哪了,他们也不敢跟家人联系,一直到了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当时为啥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在这个阶级队伍里,凡不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全要清除出去。这个运动搞的啥呢?全国几亿人,所有人都要过一遍筛子,所以,开会是18种人登记,这18种人包括国民党时期当过兵的、当过宪兵的、当过特务的、当过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等等,哪怕是在乡里当过乡丁的,当过地主、狗腿子、日本便衣队的。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曾经清理出陈永贵当过日伪办事员的事。这样清理阶级队伍,他们在山西那边,就有人问你是从外地哪里来的?你说说你解放前后表现怎么样?你说了以后人家要内查外调。你说你是洛阳的,你说你是郑州的,到郑州找不到你这个地方也不行,所以他必须得说我是洛阳伊川的,这事情包不住了,然后就跑回来,跑回来到这边不敢露面,就藏在红薯窖下头。但是这个红薯窖冬天可以下人,夏天不能下人,人会闷死。他在夏天不能下红薯窖,就住在那个地坑窑。他夏天就白天躲在地坑窑的窑洞里头,夜里就出来在院里坐坐。但地坑窑上头是路,来回过人的,就有人看见夜里地坑窑里有这么个人,觉得不对劲,然后把他举报出来,那正好,现在就是他那原来的对头家当着干部,一下子被抓起来,这就一下子轰动了。那时候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阶级斗争的典型也就出来了。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故事原型就是这么个情况。这是我跟严歌苓的一次比较重要的交往吧。最早是啥时候交往的?是克威他们刚结婚不久。铁道兵部队有个创作组,实际就是由严歌苓和李克威组成的,她后来写的那个《补玉山居》,里头实际上是写了三个故事,其中就有这个部队大院,实际是他们在铁道兵部队的故事。我们见面那时候是在83年,也是“五一”劳动节前后,我们是结婚的时候旅游去北京。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云南前线采访,准备改编电影剧本《高山下的花环》,家里只有严歌苓和李克威,还有小六夫妻俩,我们三对夫妻都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有接触。后来就是她回来挖故事,我们第二次接触。后来严歌苓再次回来,回来以后她还想挖故事。我说我跟你说个人,这个人不仅有故事,而且有非常多的故事,这个人就是我爸。严歌苓在洛阳除了收集那个故事以外又住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主要就是在跟我爸聊天,再回来的时候很大程度是来见我爸的。我爸的故事也是富有传奇性的,充满沉浮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本文作者:秦越,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201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吕东亮,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系秦越的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任红.赵光农场与电影《老兵新传》[N].黑河晚刊,2019-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