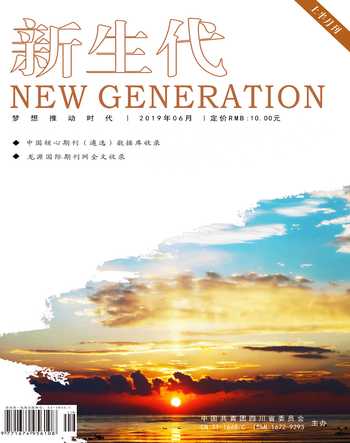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与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
【摘要】:布罗代尔提出,社会的发展受到长时段因素的制约。拉铁摩尔提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发展,和地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
【关键词】: 长时段理论 边疆 拉铁摩尔
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提出了独特的长时段理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布罗代尔主张社会实践的多元性,他将历史时间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三种时段在历史运动中所处的层次、特征、作用各不相同。
“长时段”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格局、生物现实、气候变迁、生产率限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这些因素在几百上千年的时间中,几乎看不到运动,因此布罗代尔将它称为“结构”的历史,它对人类和社会的制约性最为显著。“中时段”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波动,以10多年,25年,50年为周期,中时段的历史包括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国民收入等内容。中时段是一种“局势”的历史。“短时段”的历史,也就是事件的历史,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宣扬的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它认为社会的进程不由人的活动直接决定。长时段解构的重要性,甚于中时段的态势和短时段的事件。重视结构、局势,贬低事件,是长时段理论的重要特征。“这种做法的最终效果是把历史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将历史事件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事件”。【1】
布罗代尔提出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给研究者带来更宽广的视野。但布罗代尔对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不同重要性的强调,也是一直存在争议的地方。
二、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
拉铁摩尔是中国边疆史绕不开的一个学者,他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后世的边疆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拉铁摩尔非常重视自然地理因素在历史中的意义和作用,这与布罗代尔强调的长时段因素不谋而合。在拉铁摩尔看来,自然状况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地貌、水文条件、适应农业的类型,从而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对自然地理的强调,尤其体现对东北地区的论述中。拉铁摩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东北地区分为三部分:南部是耕地,西部是草原,东部和北部是森林。满洲是指东北地区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和黄河流域相似,作物和农业条件也一样,环境有利于精耕、储粮和低价的水运,文化上受中原影响大,东北南部是中国本部的延伸。农业的势力没有办法越过山地,进入到东北地区的草原和森林地带。历史上,中原汉族势力和生活在森林草原地带的渔猎民族,对农耕地区不断展开争夺,东北地区各族群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因此,在满洲地区崛起的势力,常常既熟悉农耕社会的治理模式,又具备了草原森林社会的军事优势,拉铁摩尔认为这是清王朝最终能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为何源起于黄土高原地区时,他特地用了一节“古代中国文化与黄土地带的土壤气候之关系”来阐明黄土高原的自然气候状况对中国古代文化形成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拉铁摩尔指出,一方面黄土高原地区有着适宜的降水:旱季时,植物不会干涸;雨季时,又不至于发生洪灾。另一方面,黄土高原地区的土质疏松,很容易耕种,加之降雨充沛,从而这一地区的农耕可以获得相对多的收获,这就为黄土高原地区发展起相对发达的农耕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草原地区相对平坦的地貌以及丰富的草场资源则为游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优良条件,于是草原地区也就自然而然的以游牧作为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起了游牧社会。
在草原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狭长的过渡地带。胡焕庸人口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半湿润区域半干旱区的界线在这里重合。随着纬度的逐渐增高,农耕播种后的收获越来越少,最终达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同样的,游牧社会放牧的草场,随着纬度的降低,草场的质量下降,承载量也降低,最终成为不宜畜牧的地带。两者之间出现了的可以间杂两种生产方式的地区,就是边疆地带。
中国的中原地区因为自然条件的适宜,发展出了农耕的生产方式,建立了农耕社会。而北方的草原地区,则不能开展大规模的农作物耕种,因而只能通过放牧来维持生活,由此建立了游牧社会。两种社会模式基于自然地理因素形成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在这一地带的两侧,分布着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两种社会模式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将影响通過过渡地带扩展到对方。
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处于各有所长所短的情形,这决定了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不会停止,也导致了边疆地区不稳定状态的持续性。边疆地区物产量较之农耕区来说并不是很多,因而减产对于农耕区的冲击作用就比较大,草场在降水偏少的年份,其承载力也会下降,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时间往往是灾年。
三、小结
中国边疆的形态,受到地理特征的深刻塑造。自拉铁摩尔之后,还有诸多著作从地理特征、生产方式等长时段因素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如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于逢春的《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等。
布罗代尔认为,决定历史的是长时段因素,而不是历史事件。按照这种逻辑,则由地理特征决定的草原和农耕的差别永远无法弥合,二者的对立将一直持续下去。拉铁摩尔在《中国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也强调这种对立,但在著作的最后,拉铁摩尔提出,随着工业化在草原的推进,铁路网在全国各地的蔓延,这种对立最终将被打破。
方铁指出,“由于边疆专门史与历史地理学均较重视贯通时段的研究,亦较注意研究对象与相关领域及相关问题之间的深层联系,致使在中国边疆史的某些领域,研究者较多采用源自长时段理论的中长时段研究方法,相关的研究也较明显地体现出总体史观。”【2】
尽管各家著作对长时段因素的强调各不相同,但长时段理论对中国边疆研究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徐浩.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方铁.中长时段视野下的边疆史研究[J].文山学院学报,2012,25(01):39-45。
作者简介:向钰芳(1995-),女,汉族,湖南湘潭人,在读硕士,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方向:边疆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