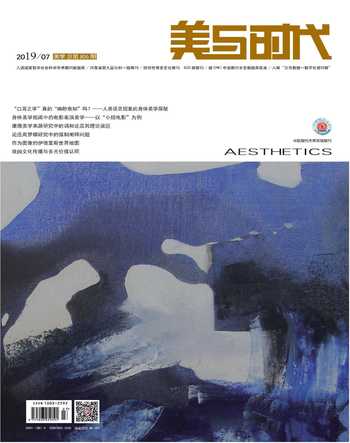“怪异者”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边缘化

摘 要:以朱迪斯·巴特勒为首的怪异理论家们在借鉴了米歇尔·福柯“知识-权力”和“性”的话语建构的基础上,重构了“怪异者”和“怪异理论”。朱迪斯·巴特勒用性别表演来重新解释了性别身份的确立,并力求达到推翻、颠覆“性”的先决条件,以此来实现质疑权威和去边缘化的目的。然而其理论本身的开放性却也带来了述行性上的问题。
关键词:怪异理论;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表演;述行性;自我构建;自我边缘化
一、从性别身份焦虑到
认识“性的性质”(sexuality)①
在明确地划分出LGBTQ(Lesbians,Gays,Bisexuals,Transgender,Queer)群体之前,人们对于非异性恋者,甚至包括同性恋者自身,都坚信非异性恋是一种生理或心理疾病,当然这绝非仅凭医学就能解释得通。过去人们总是更多地谈论“性”而非“性的本质”,前者比后者显然更富有“色情”色彩,因而被自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拿来批评非正常的性,成为了统摄传统道德和制裁“肮脏”的同性性行为的话语武器。福柯清楚事情没有如此简单,他在被围困的(be leaguered)话语(discourse)中发现了“性的性质”这一语词将会给像福柯本人一样深陷性别身份疑虑的人带来帮助他们进行反抗的思考,所以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福柯所总结的不是人类性行为的历史,而是有关于“性的性质”和“性”的话语建构的历史[1]。
在福柯那里,“性的性质”被看作是身体渴望和经历的某种快乐(pleasure),它具有一種不可侵犯的真实性(inviolable authenticity),同时也被权威、知识-权力所监控。社会中同时存在联姻部署(deployment of alliance)与性的性质部署(deploymeng of sexuality),前者指在被纳入它要维护的社会身体的一种内环境稳定状态(homeostasis)[2]301,也即一种规则化(regularization),它与社会的法律及传统道德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体现在对社会家庭组成的规定上,即在生物学角度上家庭存在的意义在于生育和繁衍、不得乱伦以破坏生育质量,同性恋之间不能组成家庭来破坏生育率的稳定;后者则指的是人们谈论性行为、性征的方式,它并非受国家机器的掌控,而是受社会流行的舆论控制,它由自身流通的意见趋势塑造而成,被部署为具有分配快感的功能[3]。二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成为了“怪异者”②在争取同性恋合法权益时的武器。
尽管有许多同性恋活动家和怪异者们把同性婚姻以及同性恋制度化视为联姻部署对“性的性质”部署的强加干预,把二者视为对抗关系。然而,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看来,“性的性质”这一概念本身不和任何事物构成二元对立关系,因为人们不能准确并肯定地说自己是具有某种特定的、不可改变的“性的性质”的。尤其像“假小子”(tomboy)、“娘娘腔”“中性人”这些概念都是不稳定的、无法下定论的,这正如德里达所说的漂浮的所指(free-floating signified)一般,这些概念的意义从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滑动的(shifting),它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如何运用和建构语言[4]284。就如同尽管一个人的生理性别(sex)看似是确定的,但实际上它同社会性别(gender)的意义一样是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滑动产生的,是被建构的。也许这就是以朱迪斯·巴特勒为首的怪异理论家们为人称道之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男女同性恋及其研究者对于性别和身份认知的焦虑和疑惑,讨论和争辩具体的生理性别和一个人内心认定的自己的性别、或者自己爱慕着的同性的“性别”这本就是十分荒诞和诡异的事情。就像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当然其他怪异者也如此会不停问自己:“我是男的,我喜欢男的,那么我究竟是男是女?我喜欢的人又到底是男是女?”没有人可以在情感的参与下来理性回答这个问题。
怪异理论家们意识到了性别身份问题的荒谬和悖论,他们的身份和性质就不是固定的或者说稳定的,所谓的预先能决定人类的特性和生理性别的条件根本就不存在。传统的生理性别的划分是基于人类从古代开始以两性结合为繁衍生息的理念而建构的,它令两性划分和异性恋拥有了特权、走向中心,成为了一种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而在怪异理论的视角下,异性区分的中心注定是要被解构和推翻的。每个人的生理性别、身份皆不相同,讨论做一个男人还是做一个女人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不同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个体都是由社会建构的,个人的性别身份不是由自己来决定的。生理性别自然也不例外,它和社会性别一样是由话语建构的而非先于社会话语而存在,人们认为自身有某种“本质”的性别特质,实际上来源于权力或者说社会规范对我们的规训结果,它潜移默化地强迫人们对自己的性别有一种期待、认知和默许,以使得人们的行为去符合某种性别规范。
朱迪斯·巴特勒在《至关重要的身体:论“性”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中特意提到性别的话语建构是通过某种“要求说明”(interpellation)达成的:“医学的要求说明把一个婴儿的指称从‘它’变成‘他’/‘她’;通过性别的要求说明,女孩子‘被成为女孩’(girled)从而进入语言和亲属关系之中,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类似的要求说明会不停地被其他权威重复,且不断地质疑性别的自然化的结果。通过命名划分性别的界线,亦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5]那么问题来了,在传统的权力,或者说社会规范中,异性恋被规定为原始的、正统的、人类应有的两性形态,同性恋是次一级的、摹仿的、劣等的、非自然的,可是这个世界的开始绝非《圣经》中记载的只有亚当和夏娃。“异性恋”这个词的产生绝对不是先于“同性恋”的,最起码也是同时产生的,如果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的存在,谁又能想到“异性恋”?两个概念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对方的存在。巴特勒对于性的性质的有力假设就是二者没有先后,并且共同存在于人们用来辨别“性的性质”的心理过剩(psychicexcess)中,即一种无意识的释放和过剩[2]299,性别表演的概念据此提出。
二、“怪异者”的述行性(performative)
与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tivity)
同“异性恋”与“同性恋”这两个概念无法分离相类似,性别与扮装(drag)同样也是一组相互的概念,扮装是对性别的一种展示也是一种戏仿,这种对性别身份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嘲弄了性别本身就是一种表演:“在社会性别的表达方式背后并不存在性别身份一说;那些被称作社会性别的结果的表达方式,表演性地组成了身份。”[6]正是因为性别像表演一样连贯、完整、循环往复、充满节奏,具有服装、姿势、体态声音等可加区分的象征符号(symbol),所以它更可以被扮装所摹仿。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朱迪斯·巴特勒说到扮装体现了表演者生物学或者说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与被表演的性别之间的差别,这恰恰证实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必然的。在扮装这种自我表演的过程中,身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恰恰是灵活多变的。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丹麦画家,也是世界上首位变性人,埃纳尔·韦格纳,当然从精神病学角度来分析他也许是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性别认知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患者,但他也毫无疑问是公布自己身份的怪异者先驱。他的角色扮演,即性别表演,是出神入化的,他既是一位合格的丈夫也是一位先锋派的伟大“女艺术家”。他的性取向看起来是没有变化,因为他对妻子的爱始终如一,那么他的变性则更像是对某种东西的颠覆和终极挑战。在我们熟悉的《断背山》的故事中,恩尼斯和杰克都“知道”自己不是“怪人”,他们在第一次的“意外”之后回归了家庭,有了正常的婚姻,扮演着丈夫的角色,但当他们重逢,他们的角色第二次变化了,并且更加彻底、决绝、不可收拾。两个白人男性牛仔,特别强调一下“白人”“男性”,这其中自然有什么是要被拿出来反抗的。巴特勒本人作为如假包换的女同性恋者,她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男性的身份,然而毫无疑问她不可能会对自己所扮演出来男性身份感到舒适、自信和有安全感,她这么做是为了自我建构,稳定她特殊的身份,同时又带着身份的焦虑一刻不停地表演下去。社会性别是表演性的,它没有也不需要一个预先规定的身份作为标准来进行比较和衡量,它从来不是固定和稳定的身份,而是不能脱离时间和地点的流动性的、实时的表演。性别和欲望是灵活多变的,性别同时也是欲望的化妆表演,而性则是文化、道德规范对人身体的物质化的表征,性别表演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将生理性别从自然化的表象中解放出来[7]。
怪异理论这种挑战自我身份的固定的观念带有明显的反本质主义理论(antiessentialist theory)的色彩。人的人性之中沒有什么是能作为一种本质来决定人为何生而为人的,正像巴特勒所认为的那样,世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人们没有必要让社会和规范来塑造自己的身份,也没有什么预先决定的二元对立或偏见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差异不应该被拿来利用,而应得到接受和相对公平的对待。那些被边缘化的怪异者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谁并去挑战性别身份、社会性别和性别差异是先天决定的观念。因此对于怪异理论来说,只有那些能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来讲述自己的人才是“怪异者”,也即“怪异”所指向的述行(performative)行为[4]286。一个人的身份和他做什么以及他是什么有关,而不被他预先被设定的本质所确定。由于怪异理论的这种诉求,使得怪异理论家们坚信怪异者的身份是怪异者述行的效果(effect),他们希望自身永远不会被二元对立来界定,或者被传统规范所抹杀,希望自己的身份是不确定的、未完成的、总是在建构中的(under construction),这意味着保持身份的述行性(performative)是怪异理论家们不懈的追求。
从这种角度来看,怪异理论毫无疑问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的,但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怪异理论拒绝界定自己,并认为自己是不断地、自由地变化,这便必然会导致它是没有界限同时又可能是无所不包的,且不论它是否会走向某个方向的虚无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性的开放和多样性必然要给它带来新的冲击。怪异理论本应被期待成为一种指导现实的理论,但由于它根本上不能规划自己的发展图景,在某种程度上它面临着被现实遮蔽或被歪曲的风险。
三、时髦的LGBTQ群体与自我边缘化
尽管怪异理论家们拼命反抗着自己身份的“被界定”,然而当LGBTQ群体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摇旗呐喊的时候,彩色的旗子和飘带成为了他们最显眼的固定符号和象征,甚至在输入法中敲出这五个字母的时候也会自动弹出彩色的符号。怪异理论在被更好地用于指导现实之前就已经经历了残酷现实的打击,LGBTQ群体激进的活动的确引起了足够多的关注,但这些行动并没有使更多人去试图理解和同情这群人,尽管他们也没指望更多的人去同情自己,反倒是造成了多数人的不适和以政府为首的社会权力的排斥。
怪异理论是不去下定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其述行性出现问题的原因。LGBTQ群体中本来就对自己的身份是否应该得到关注而分歧不断,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身份和存在应该得到重视,他们也因此极力向公众去暴露自我;而有些人则不希望自己被打扰,甘愿做被世人遗忘的一类人。这也就是关于“出柜”与“深柜”问题的思考,对于不同身份的LGBTQ个体而言( close /out) ,“沉默的螺旋”有不一样的表现,那些未出柜的LGBTQ个体容易被主流的异性恋规范和准则所遮蔽进而“沉默”;那些已经“出柜”的个体则会运用网站提供的特殊情境发声,分享关于LGBTQ的议题,其目的在于表达自我queer的身份,使主流群体“沉默”[8]。对于非LGBTQ的普通人群来说,支持LGBTQ维护自己存在的权力,其真实目的为何实则尚未可知,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还是别有用心?对于他们的疑问集中在“你又不是LGBTQ中任何一种,你为什么帮他们说话?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种现实情况的纷繁芜杂使得怪异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当代社会中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是畸形。网络的私密性为同性恋人群寻找性接触对象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增加了HIV感染的风险。亚洲国家的同性恋议题公开化,往往遭遇来官方和民间的强烈反对,但HIV对于这些国家的显著影响使得这一问题不得不受到官方重视。同性性行为人群使用APP交友方式比过去的同性恋酒吧和派对更易操作和富有效率,这促使了危险性行为以及HIV高感染率的发生,网络空间的性行为和现实生活中的性接触使得同性恋便捷化、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追去刺激、时尚、发泄欲望的行径[9]。此外,部分女性热衷于看到耽美的男同性恋,认为那是美好与时尚;男性崇拜并憧憬于女同性恋,认为其中暗含性的刺激与吸引;大人诱引青少年儿童像中性风格或异性风格穿衣打扮,甚至后天强制性地把强少年变成“美丽的同性恋者”;还有人热衷于在双性恋之间来回自由转换,以彰显自己的独特品味和魅力;西方国家不少人力主取消公共卫生间、澡堂。更衣室的男女之别,他们虽然打着拒绝某种歧视的幌子,但做法着实荒诞不经、不切实际。这些人群本身并非天然的同性恋者,甚至绝大多数都是异性恋者,这些新潮人群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很“酷”的,那么他们对“怪异者”的肆意解读究竟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之上?他们的确看起来是非常怪异的,但他们有资格或者说能够自我建构起这种怪异吗?
毫无疑问,怪异理论是为了抵制主流的力量和体制的束缚而诞生的,它当然是希望让人们注意到怪异者们被边缘化了的位置。然而,怪异理论本身也是极易受其叙述者的影响而变化,易被意图叙述“怪异”的权力者所收编。因此巴特勒对于身份类别的分类显得极为谨慎而坚决,她拒绝让身份加入到某种特定的类别中:“目前,(它)只能保持决不把自己完全交给哪一方的本色,永远并仅仅只是重新配置、扭转和破坏先前的用法,朝着紧迫而扩大的政治意图前行,而且,也许它还要被迫去支持那些使政治工作更为有效的法律条款(terms)。”[4]359怪异理论述行性的问题也在于它可能被固有的话语权力者利用某些看起来怪异的人重新夺回话语权。
新潮时髦的LGBTQ群体过分自我,他们的性别表演有更多的含义是在显示自己身份的特殊,作为一种炫耀来建构自己的怪异身份。他们过度强调自己的不同,以自己和他人的区别作为值得骄傲之处,这在某种“政治正确”的社会舆论之下乍一看无可厚非甚至值得鼓励,但是他们在诱导之下,极为片面地展示了怪异者们肮脏的、龌龊的、疯狂的、病态的、非理性的部分,这种做法反倒成了可以自己把自己给边缘化了。特瑞沙·德·劳拉提斯认为,怪异理论的那种批判穿透力可能已不复存在,它的开放性时刻让它面临着被歪曲和被时势裹挟的危险。那么既然它是开放的,也许一种拉开距离的立场可能会使这一理论的现实实用性得到重塑。“谁”,什么样身份的人来走入叙述“怪異”的这个位置将是值得思考并极为重要的选择。
注释:
①“性的性质”即sexuality, 也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性态”(也有译为“性征”),其英文释义为“The involvement or interest in sexual activity”,牵涉与性欲、性行为、性征等等与性相关的事物,由于“-ity”意指具备某种性质,故译为“性的性质”。
②“怪异者”即“Queer”,又译作“酷儿”,最早源自低地德语,即布伦瑞克方言“queer”,释义为:“Something strange or odd”,也有“oblique”(倾斜的、躲藏的)和“off-center”(离开中心的)的意思.1922年作为同性恋(homosexual)的同义词记录在案;直到1994年Queer Studies 的兴起。尽管广为人译为酷儿研究、酷儿理论,但后文中认为正是对“酷”的追求使得这一理论面临困境,因而本文将与“Queer”相关的术语全部译为“怪异”以作区分。
参考文献:
[1]秦静.权力与身体的双重拷问——福柯《性史》解读[J].史学理论研究,2002(4):81-87.
[2]Fry. Theory of Literature [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301.
[3]Foucault. Volume 2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York:Random House,1985:119.
[4]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五版)[M].赵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84.
[5]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93:232.
[6]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37.
[7]都岚岚. 论朱迪斯·巴特勒性别理论的动态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2010(6):65-72+78.
[8]Fox,Warber.Queer identity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self-express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A co-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piral of silence[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5(1):79-100.
[9]王雪.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认同”——媒介与LGBT研究的路径与转向[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85-89.
作者简介:高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