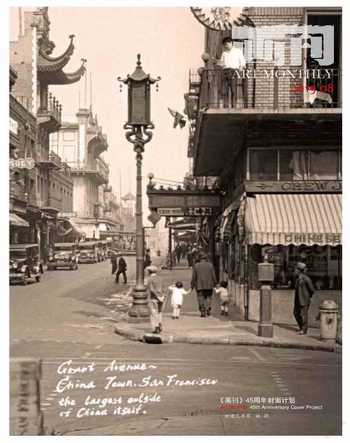“爱拯救生命”:向戈雅致敬!
徐跋骋

当我还是浙美附中学生的时候,就翻看着老旧的戈雅画册,爱不释手。
戈雅一直对画面中光的驾驭十分着迷,他后期的画面几乎都是黑乎乎的,特别是他的画面中的光,好像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老辣的笔法中一种无法言状的神秘气息随之而来。他的用笔行云流水,仿佛刀光剑影,急速地捕捉着对象的神韵。在他的画里,西班牙这个民族的那种挥霍、奢华之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丢勒一样,也是能为自己民族定性的画家,这样的大师屈指可数。
戈雅一生经历了不同的王朝,画了无数的纸上作品,这些素描的气质和他的油画一脉相承,浓郁的质感和饱满的专注力刻在画面里。你看第一眼就会安静下来,并被那奇幻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所折服,随后内心激起千層浪。
戈雅的这种绘画方式也像一盏明灯,时常指引着我。我在构思一张大画之前也会画不同的素描小稿。这张甲壳虫素描是我下乡时画的,当时床头就趴着一只甲壳虫,我就把它请来作为我的“模特”。我盯着它,看着那巨大的触角和闪亮的眼睛;它同时也张望着我。我开始兴奋起来,迅速地记录下这只肥硕的甲壳虫。从此,这张素描的影子一直根植在内心。我一直想把这张画放大成油画。
直到有一天,我回看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感觉戈雅在我心目中就是那只甲壳虫,它虽渺小但生命力顽强。戈雅一生颇受皇室恩宠,绘画生命延绵不绝,但在皇室的更替过程中和宗教裁判所统治的阴影下,戈雅也有他的无奈和纠结。戈雅可以称为一代宗师,每一代画家都能从他身上汲取养分。马奈肥阔的笔触就来源于戈雅的用笔;培根也深谙其精髓,把那种神经质癫狂发挥到极致。戈雅的感染力就如夸父逐日那般热切,画面仿佛飞蛾扑火那样炽烈。我看着这张甲壳虫的素描,想象着《变形记》里的甲壳虫面临不同亲人的境遇,陷入误解和惶恐的深渊,直到甲壳虫生命的尽头。而戈雅也有一张弥留之际的自画像,他被旁人扶着,举着药瓶。画面透露出一种莫名的神秘感,这也让后世画家慢慢品味其中的意味。
那晚,强烈的欲望驱使着我,一整夜,到天明就诞生了这张油画“甲壳虫”,我心目中复杂而又神圣的戈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