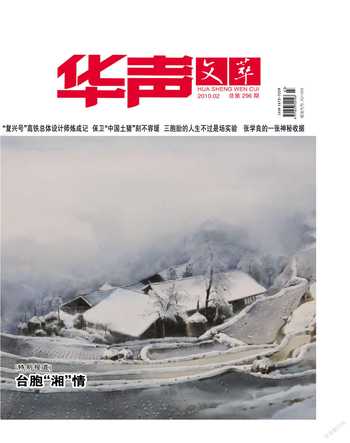敲钟老人的学问
张汝林
1970年,我刚从“牛棚”里出来重新走上讲台,就又因背后对“副统帅”的极端言论提出非议,被赶下讲台。我被送到学校的小果园里,一边劳动一边反省问题,造反派怕我不老实,让管理果园的费师傅负起监督我的责任。
费师傅是学校附近农村的一位老贫农,当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是我任教那所中学的管校“代表”。熟悉之后,我们就无话不说,他不再是我的监管人,反倒成了我的朋友。他对我说:“我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哪会管中学?这年头净出怪事。”他冷笑几声接着说:“但吃着公家饭光待着不行,我挑了两样活计:一是管果园,二是管敲钟。”說着扔给我几个刚熟的果子:“吃吧!别上火,听肚子叫唤还能种地?”
有个星期天,下起连阴雨,果园没法干活,我俩躺在看果园棚子的地铺上闲聊起来。“费师傅,你一天敲二十多遍钟,我听着每次咋不一样呢?有时快、有时慢,有时大、有时小……”
费师傅不紧不慢地说起其中的奥秘:“干啥悟啥,卖啥招呼啥。比如早上六点敲起床钟,学生们睡得很沉,你猛劲地敲,孩子们突然惊醒,会伤害脑筋;于是我先小声慢敲,再一点点放快速度加大声响,让学生从睡梦中慢慢醒来。晚上九点敲熄灯钟,学生累一天了很疲劳,但必须慢慢入睡;于是钟声由大到小,由快到慢,让学生在微弱的钟声中渐渐入眠。上课钟要清脆响亮,让学生抖起精神,集中听讲;下课钟要匀速缓慢,因为有的教师压几分钟堂,别催老师,给老师留点余地。”
费师傅吸口旱烟,缓了口气,转了话题接着说:“这几年整天批斗成分不好的老师,天下没了公理。每次造反派头头命令我敲钟开批斗会,我都慢敲轻敲。造反派说‘钟声没有火药味儿!’我心想,你们一个个发高烧,我这是用钟声给你们降温哩!批斗会没开完,到放学吃饭的时间了,我快敲猛敲!走读生坐不住了,住校生也想去吃饭,会场乱了,批斗会只得草草收兵。”
费师傅的话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读十几年书,有了文凭是有学问;像费师傅那样,在实践中摸索出做事的规律,用钟声倾注对师生的深情,传递着人世间的爱与恨,同样是有觉悟的高深的学问。
(摘自《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