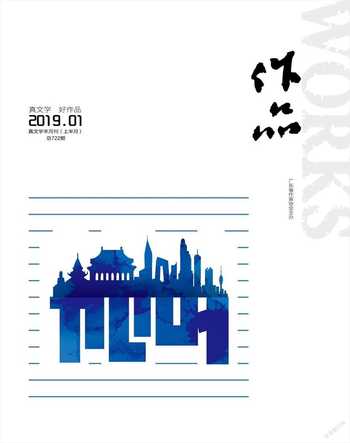为历史寻找诗意
王梦迪
除去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和新疆的《玛纳斯传》作为口头文学代表着民间文学意义上的史诗外,汉民族并没有作为叙事传统的史诗记录自己的历史。在当代诗人中,張况的写作体现出对日常性与自我关照的超越,这种致力于建立史诗版图、为历史寻找诗意的实践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诗学意义。
众所周知,抒情传统将历史作为叙述背景进入诗歌,而且往往是琐碎的片段。张况不满足于片段式的记叙,当然他追求的也绝非简单的线性时间线索。在张况的诗歌疆域里,几乎所有历史细节都是鲜活的,他凭借奇特大胆的想象,将所有历史故事、人物化为他言说的对象。显然,他的目的并不在于书写历史本身,而是希望重构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记忆,让历史与当下产生关联性的对话。当诗人自由驰骋于历史时空,其实并不是记录时间,而是让“时间在他的诗行中行走”(郭小东语)。
时间无疑是张况诗歌文本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意味着时间即是进入诗人内心的密码,无数时间节点以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方式散点布置于他的诗行,借助一面“天空之境”“激活亿万斯年的记忆”(《照见:天空之镜》)。于是,《楚辞》的章句、格萨尔王的叹息、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一带一路”这些符码穿越时空,以极为怪诞、和谐的方式取得拼贴的效果。诗歌是朝向过去的,无论是历史还是刚刚过去的瞬间,诗歌以自身之力抵抗时间的有限性,这些古典元素因为其附着的文化记忆而一再被激活,召唤起拥有共同文化记忆的读者内心的认同。诗人与历史,读者与历史,都在此刻获得交流的可能,线性的时间不再成为阻隔,在诗意发生的那个时刻,读者成为了历史的同代人。
古典符号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记忆正是张况与历史对话的入口,他不铺排历史,却能让历史以鲜活的姿态呈现在他的诗歌中,借助的正是这种理想读者共有的古典文化记忆。比如《端午,在一座古城怀屈子》就一直贯穿着“粽子”的符号,随着望穿江水游走城墙的一路奔忙,每个人都能理解端午在不同时代所负载的想象,最终通过“《离骚》只有一首/谁读,都是国殇和深愁”完成同一个民族的心灵共识。在组诗《时间的涟漪是谁人来不及逃亡的心跳》里,写梅的就有四首之多,足以显示“诗坛四公子”所倡导的文人精神,而在《香雪海读梅》中,诗人不断提起四公子及自己的朋友,颇类似传统诗歌的“用典”技法,可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文人心性。梅花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内涵无须多言,张况将自己的抒情建立在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古典文化内涵上,使诗歌完成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的表达功能。
语言是存在的家。诗人对于精神家园的寻找,就是置身于语言实践的动力。当以追寻个体独立人格以及自由为本的现代新诗遭遇现代文明的异化,诗人怀着回望家园的心为自己寻找生存之地也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张况经常通过诗歌返乡,生于广东五华的他从未掩饰对家乡热土的热爱,他的诗歌反复书写南朗、崖口这些岭南小镇,他笔下的自然风物,即是他无法割舍的家园。或许在他看来,史诗的建构不只是记录历史,还要以当代人的身份记录自己感知的当下,而这些当下终将化为历史的遗存。他曾说自己的诗歌要“写胜利者那三分之一历史,写失败者那三分之一历史,和普罗大众那三分之一历史”。既然日常中的诗意被日常所书写,那么历史与诗意是否有共生之可能,张况或许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诗歌中的历史固然求真求实,然而最后的书写却遵循着自身的抒情逻辑。从诗人的书写角度来看,与其说张况在尝试一种书写历史的新途径,倒不如说他在为历史寻找诗意转化的可能,唯其如此,历史及其土壤才展示出常说常新的魔力。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