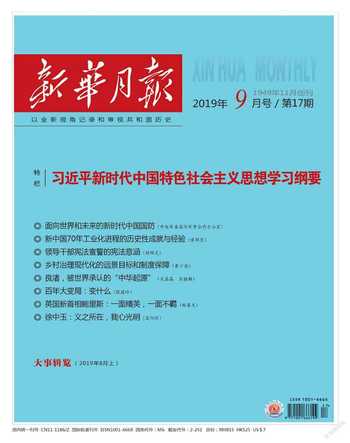法律与文明的交互关系
徐爱国
文明是人类社会改善自身、摆脱野蛮状态的过程和结果。人类活动的每一步改善,都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法律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法律是人类行为的规则,更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法律史有时候也被称为法律文明史,法律文化则是将法律纳入社会史后法律与社会的综合考察。从学术史上考察,法律文化研究成果丰硕,法律文明研究相对薄弱。
文明与野蛮具有相对性。汉人自称为文明,把夷族归为野蛮人;希腊人自许为文明,将马其顿归为野蛮人;罗马人号称为文明,将日耳曼人归为野蛮人;基督教自以为文明,把异教徒归为野蛮人;文艺复兴颂扬古希腊罗马为文明,将基督教会归为野蛮类;西方人以自我为文明,将东方社会视为野蛮。文明无所不包,文明是礼仪,是人本,是制度,是教化,是科学,是进步,是理性。无论文明从哪个意义上去理解,都能说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法律功不可没。或者说,法律与人类文明同步前行。
法律在文明发展中的功绩,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总结得最为完整。启蒙学者将人类历史区分为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称为自然状态,后一个阶段称为国家或政府阶段。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就是民族国家、政府和法律的产生。
在国家与法律产生之前,人类按照本性生活,或者相互猜忌、怀疑和竞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或者没有规矩、没有执行力和没有公正裁判的无政府状态,或者依人类善良本性、脆弱神经和感性敏感而生活的原始状态。没有安全、没有食物、没有繁荣、没有航海、没有科学、没有公正、没有制度,这是一个短暂的、龌龊的、贫乏的、混乱的时代。人类的本性和良知呼唤着文明的到來。用卢梭的比喻来说,当一个人拿起一根棍子在地上画了个圈宣布“这是我的”的时候,人类开始进入文明的时代,这个拿棍画圈的“骗子”就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人。从野蛮步入文明的方式,就是社会契约。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把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超越每一个个体的存在,这就是国家。国家体现了公共的意志,公共意志的外在表达就是法律。国家通过政府运作,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政府是主权的执行者。在政府和国家之下,法律权利取代了野蛮状态下的自然权利。
以法律的角度解释,人类文明出自于法律的规定。法律或者确认权利、或者撤销权利、或者判定权利。一只野兔在野外奔跑,谁逮住它,它归谁所有,这是确认权利;一只家兔在郊外奔跑,不管谁逮住它,它依然归原主人所有;一只野兔在野外跑,张三射中了兔子,李四抓到了兔子,野兔归李四所有。“无主物归最先占有者所有”“占有必须是充分的和完全的”和“所有权具有对世权”,三条法律规则划定了野兔在野外逃窜的财产权界限。贯穿于三条规则中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文明”。以法律的方式而非野蛮武力的方式定分止争,这才是文明。法律会制约人的行为,按照规则行事会妨害自己的随心所欲,这也就意味着,文明也会约束人,也会让人失去一定的自由。但是拿洛克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政府,是因为政府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障,在“被狮子吞没”和“被狐狸骚扰”之间,文明选择了国家、政府和法律。
从法律的哲学回到法律的历史,结论一样,那就是法律与人类的文明同步增长。文明如何演进?法律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是什么?没人给出明确的答案。至少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仁慈悲悯的唤起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西汉时代的仓公,是个地方钱粮官,也是个名医,他治好了不少人,也得罪了不少人。他被人举报,要被押赴京城受审。仓公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押赴京城时抱怨,生女不生男,危难之际不管用。女儿缇萦只好陪父入京,给皇帝汉文帝上书。她说她爹很是无辜,如果被判有罪,按汉刑受肉刑,既痛苦又羞耻。抹不去肉刑留下的记号,叫他以后如何重新做人?要不让缇萦去官府当女奴,免了她父亲的罪?文帝悲悯心涌起,赦免了仓公的罪,废除肉刑。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文帝废肉刑的典故。从墨劓、宫剕、大辟的肉刑体系到笞杖、徒流、死的自由刑体系,被称之为刑罚的进步。从炮烙、车裂、腰斩、枭首、凌迟、点天灯到斩与绞,再到枪决,最后到注射,死刑执行方式的每一次转变,都与科技的进步和减少受刑者痛苦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财产法的历史也折射了人类文明史。古代社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债务人欠债不还,或者无力归还,依照古罗马早期法律,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杀掉,按照欠债的比例各个债权人分配其肢体。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要割下基督徒胸前一磅肉,历史渊源即在此处。往后,出现了债务奴隶,如果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向官府举报,要求剥夺债务人的自由。债务人被关进监狱,失去自由身份。或者,流落他乡,远离债主,即使如此,一旦回到自己的社区,债权人随时可以追偿债务。再往后,英国人发明了商人破产制度,商人破产可以免除其债务。其中原因,按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说法是,商人破产不是他道德上的败坏,而在于他命运的不幸。商人本身就是财富,若继续在商场上打拼,可以重新创造财富。破产法由此诞生。再往后,即使是债务人,他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也要得到保护。债权人野蛮逼债、精神恐吓,可以构成侵权,要承担债务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从对债务人的刑事惩罚到侵权法对债务人的保护,从对财产权的重视到对人身权的尊重,同时体现了法律进步与文明的增长。
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其一,文化的性质决定法律的性质,法律是文化的一种折射。其二,反过来,法律也可以改变和提升特定的文化。法律与文明的关系,也是如此。法律既是文明的一个面相(向),又是衡量文明的一个尺度,同时还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但是,法律与文明的关系也有独特性。其一,法律文化学者通常不对法律文化作出价值判断。文化只是描述,不同文化之间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但是,文明却有价值判断。专制主义的法律是野蛮的,民主自由的法律是文明的;一夫多妻的婚姻法律是野蛮的,同性恋合法化的法律是文明的;家长权下的法律是野蛮的,个人自治的法律是文明的。其二,法律文化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通常是静态的,空间纬度居先,而法律文明学者的方法,则多是动态的,时间纬度居先。如若对法律存在价值的判断,就会相信法律的进化,就会相信法律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当属黑格尔。他认为,法律有自己的历史,它不同于纯历史的编年史,而是体现法律发展的辩证法。法是客观精神的外在实现,经过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之后,法哲学进入世界历史之中。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文明从中国、印度和波斯的东方文明,演化为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最后达到日耳曼文明。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哲学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人类也从原始达到高级。
把黑格尔的历史观应用到法律史研究,成果显著的当属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他区分了静态的东方社会与动态的西方社会。他说,历史对于法学家而言,如同地壳对于地理学家那么重要。在法律发展的早期,东方与西方法律同步发展,依次经过了个别判决、习惯和法典三个阶段。然后,东西方法律发生分野,东方法律发展停滞了,西方法律继续向前发展,依次又经过了拟制、衡平和立法三个阶段。法律的发展是进化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法律上的表现,便是“从身份到契約”的发展,即由人身依附关系的法律走向个人自由独立的法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黑格尔主义法学,则从法哲学的角度提炼了法律与文明的关系。德国法学家科勒说,法律过去是文明的产物,当下是文明的表现,将来是促进文明的手段。这种将法律与文明联系起来,寻找法律发展逻辑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法学教授庞德。法律与文明关系史,构成了法律史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文明内涵着价值判断,因此,不同人群的文明判断不尽相同。假定法律促进文明的进步,不同的文明观会对法律的取舍决然不同。一群人眼中的野蛮,被另外一群人视为文明。或者,当下野蛮的行为,将来会有利于文明的进步,这也为法律带来困境。这可以称之为法律与文明的冲突。法律规定处理更有利于人类的文明,会演变成法律的难题。
经常引起争议的一个议题,就是法律如何协调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冲突。医学人体试验,对于受试者来说是一种恶,对于社会来说是反文明。未经患者同意,在他身上做医学试验,本性上讲是反人类的罪行,是违背文明的行为。但是,人体试验的成果,将来可以用于全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它又有利于提升人类总体的文明。对医学研究中的人体试验,法律该禁止,还是该放任,还是该提倡?反文明人体试验带来的医学资料和治疗方式,是否可以用做当下的医学诊断与治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纳粹出于军事目的,希姆莱曾命令纳粹医生在达豪、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等群体做了大量人体试验。以冷冻试验为例,受试者被放置于冰水罐中,连续几小时,直至颤栗至死。德国军方的目标设计是,当德国飞行员被敌方击中、弃机落入北海后,能在冰冻海水里存活多久。试验医生是纳粹医生西格蒙德·拉舍尔,他在达豪集中营模拟这个实验,启用了300位囚犯,详细记录他们从暴露于冰水到最后休克的过程。其中,有80—90位受试者死亡。集中营里的人体试验,后世在法律上的争议是双重的。其一,战后军事法律审判如何对待人体医学试验?其二,纳粹集中营里人体试验的医学资料和数据,如今的医生是否可以参考和应用?
前一个问题催生了医学伦理法典,就是《纽伦堡法典》。“二战”后,盟军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其中就有对德国纳粹医生的审判。1946年10月25日提起诉讼,12月9日审判开始,1947年8月20日审判结束。23名被告人中,7人被宣告无罪,7人被判死刑,余下的被判处10年到终生监禁不等的自由刑。审判过程中,医学伦理被提交到盟军战争犯罪委员会。三位法官在回答医疗专家证人时,提出了10个要点,这就是后来的《纽伦堡法典》。其中包含如下原则:知情同意和免予强制;合理设计的科学实验;有利于实验参与者。这意味着,未经过知情同意的医学人体试验,本性上是反文明和野蛮的行为。如果在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或者未来长期利益的前提下,人体试验也可以有条件地进行。换言之,在保护病人的前提下可以实施医学实验。试验之前,试验者必须征得受试验者的知情同意。这项原则后来为《国际人权公约草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赫尔辛基宣言》《欧盟议会2001指令》《国际生物医学研究人体试验伦理指南》等系列医学伦理国际公约所确认。
后一个问题引起更激烈的法学争议。现代医学也研究人体低温,研究的目标是救助那些濒于致命低温点的病人,帮助搜救和援助人员判定海难落水者存活的概率。但是,临床医生缺少科学的依据,所使用的数据都是来自动物试验,而动物和人的低温生理反应存在着很大差别。巧合的是,“二战”时期纳粹的人体试验有详细的数据:纳粹让囚犯处于零度以下,或者冷冻于冬天野外。当囚犯排泄粘液、眩晕和失去意识的时候,纳粹医疗人员详细记录受试者的体温、心率、肌肉反应和尿液的变化。拉舍尔医生甚至还发现了快速的和主动的再暖“技术”。这些资料和数据对于现代医生具有直接的参考性。现代医生为了全人类未来健康这一文明的目的,是否可以使用反文明的纳粹的研究成果?法律并没有给出答案。一些医生参考了纳粹的数据,更多医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纳粹的医学数据沾满了六百万犹太受害者的鲜血,其医学价值不能淡化纳粹的反人类和反文明的行为。在科学和文明冲突的情形下,文明居先。法律的态度是,当文明与野蛮出现冲突的时候,好的法律可以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遏制野蛮对文明侵害,将野蛮转化为文明之用。
文明与野蛮贯穿于人类的历史。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法律陪伴着文明向前推进。法律与文明交互作用,过去记载了文明的成果,现在维持着文明的演进,将来促进着文明超越。当文明战胜野蛮时,法律忠实地记录着文明的点点滴滴,充当文明的载体;当野蛮扰乱文明时,法律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节奏,将野蛮导向文明。
(摘自《民主与科学》2019年第2期。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