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长歌

冬婆坐在屋门口,一动不动,眼里泛着幽暗的光。
有那么几回,我好奇地打她跟前过,故意将身子在她眼前来回晃,她居然看都没看我,眼光呆呆地投向远处的狮子山,仿佛自己是一只孤老的隼,只在心里向往着远方的天空。
狮子山埋着冬司供,坟头正是朝向她家的方向。坟地是冬婆亲自挑选的,冬司供走后,没事的时候,她总喜欢朝狮子山远眺,像是有好多的话,要对那个冷冰冰的墓碑诉说。
在月塘村,司供算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世代单传,专门为人料理身后事,被尊称为护灵人。
冬司供走后,月塘村就再也没有司供了。
应该说,冬司供曾经是月塘村顶顶受人尊敬的人,这种尊敬超出了我惯常的理解范围,比如说,我对长辈的尊敬,无非就是见面打一声招呼问个好,但村里人对冬司供的尊敬,却是一种仪式化的大恭大敬,上他家请他主事的人,无论老少都得叩两个头。也许由于规矩太过苛刻——你想想,谁没事愿意去给别人叩头——一般情况下他家都不会有人走动,过路走到他家附近的,也都尽量绕道而行。冬家两口子没事的时候,也从来不往别人家跑,二人独来独往,默默地上山下地,出起入居,他们只关心死去的人,活人的家长里短,与他们无关。
司供必须有把好嗓子,那是吃饭的家伙。冬司供歌唱得好,这是公认的。不仅如此,冬婆的花扎得巧,也是妇孺皆知。天气晴朗时,冬家院门洞开,冬司供唱着一种听不清歌词但旋律极其婉转悠扬的歌子,顺带把青竹竿削成篾条,冬婆则拿削出的软篾条编织形态各异的胎,胎上糊上花花绿绿的纸做成漂亮的花圈,那些散发着篾条和糨糊清香的花圈个叠着个,排挨着排,把冬家门前的晒谷场装点成花的海洋。
那一天,不知是冬司供的歌声惊起了梁尘,还是冬婆的纸花拢乱了春风,反正,我和阿桂一个没忍住,踏破禁忌,踱到了冬家院子里。那里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我和阿桂被深深地吸引了,不自觉间,我俩就坐到了冬家的门槛上,当然,我俩谁也没给谁叩头,很多时候,我俩在村子里见谁也不打招呼,进谁家也不敲门,来去像一阵风,随性得很。
冬司供其时已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见我们到来,专门停下歌唱,冲我们微微笑了一笑,额头上的皱纹堆成一座山。
“你的歌子可以教我吗?”我仰起头,满是新奇地看着冬司供,平常里听冬司供唱歌,都是在葬礼的现场,人来人往,外人吵吵闹闹,孝亲哭哭啼啼,从来没听清他唱的是什么。
“你想学这个?”冬婆停下手里的活计,满是疑惑地看着我。
“嗯。”我笃定地朝冬婆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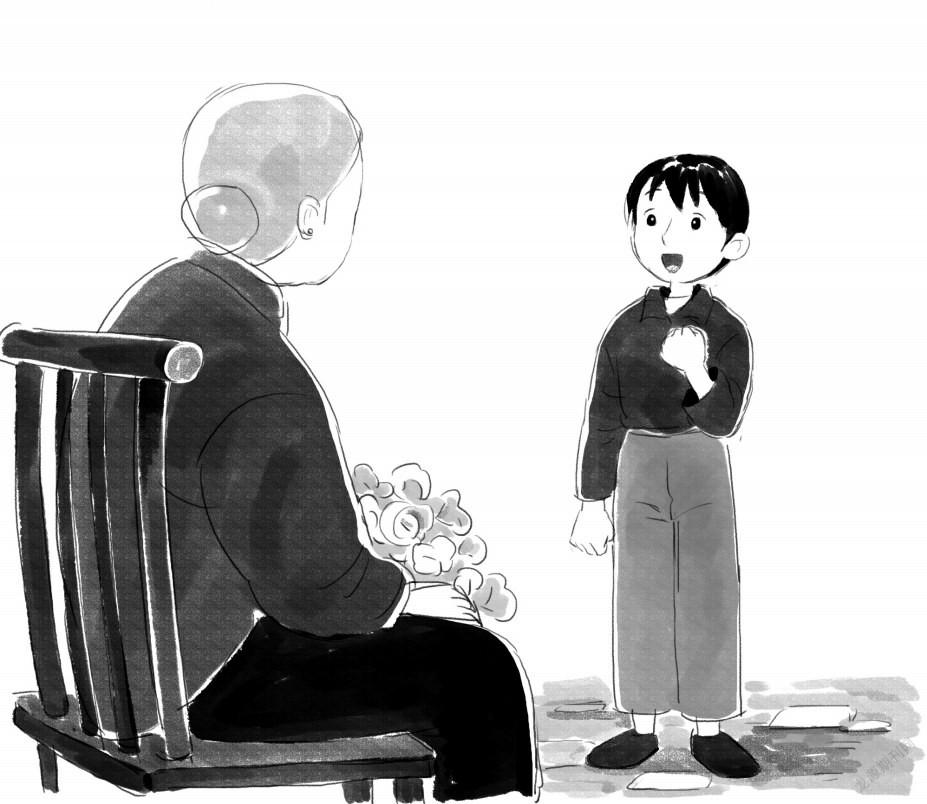
冬司供丢下篾刀,搬把椅子坐在我对面,试探着问:“你爹娘可知道?”
他问得可真好笑,学唱个歌哪里还要爹娘同意哦,我跟着电视广播唱歌,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从来没说要爹娘同意。
“就是唱歌嘛,哪个爹娘还管这事?”阿桂也在一边表示不解,但他更多的是喜欢冬婆的纸花。
“拣几句唱可以,可不能轻易学。”冬司供说着,跷起二郎腿,掏出旱烟壶,抽一口,咳嗽两声。
我诧异于冬司供为什么抽烟的时候咳个不停,而唱歌的时候却气息舒畅,一声不咳。
“不教?”我失望地看着他。
“可不敢乱教。”冬司供又说。
我有点儿失望地在院子里到处乱瞅,这时候,冬司供拿烟斗敲敲凳子腿,清清嗓子唱开了:“我劝堂前儿女们,莫忘父母养育恩。十月怀胎娘辛苦,黄皮刮瘦不成人。儿女出世多可爱,把你当为母肝心。千辛万苦拉扯大,挡风遮雪避雨淋。等到一朝儿女大,蝶自纷飞花自零……”
我听得出神,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还没记住几句,歌子却戛然而止。我正想问个明白,却见院外远远走来两个人,刚进门,就扳着门槛扎扎实实叩了两个响头,随即将一个装满供食的竹篮捧到冬婆面前。为首那个愁眉苦脸地说:“恭请老神仙为张家主事。”
“哦,”冬司供四平八稳地坐着,“不知,苦主是哪位?”
“张家奶奶,昨日夜饭还吃得好好的,清早……”那人说。
“哦,”冬司供摆了摆手,“告诉孝子,下午三点起场。”
那人领了冬司供的话,退了两步,鞠躬,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两人走远了,冬司供侧着身子对我说:“想听孝歌,到场上去,那里敞开了嗓子,尽管唱。”
说话间,冬婆已经打开了那篮供食,就在我坐在冬司供身边说着什么的当口,阿桂手里已经多了一只油淋淋的大鸡腿。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想数落阿桂几句,冬婆麻利地把另一只鸡腿扯下来,递到了我手里,然后将竹篮挂到屋檐下,忙开了。
不一会儿,冬司供便拎起一面黄铜锣,用木锤咣当一敲,起身往外走。冬司供的家本来就在村口,他从村头的大槐树下起步,每过一家就敲一下锣,嘴里拉腔作调地喊:“各家各户,仔细听呢,下午三点,张家起场,吊丧一天,各家收拢人员,壮劳力全都要到场啦。”冬司供喊到哪里,哪家的门就会打开,探出一个头,不出声,就静静地望一望,算是回应。
我和阿桂晃晃悠悠跟在冬司供身后,在各家各户默默的关注下,步子迈得啪啪响,觉得自豪无比。等走到自家门口时,阿妈探出的脑袋顿了顿,想说什么,没有出声,等冬司供走过,一只手牢牢把我抓住往后拖,转身一看,阿爸一脸冰霜,恶狠狠地瞪着我。
“给我滚回去。”阿爸咬着牙,沉沉地喊。
刚进门,阿妈迅速把门掩上,捶胸顿足地说:“祖宗,可不能跟着瞎跑,晦气呢。”
“晦什么,没听冬司供喊嘛,送张奶奶归山,全村都要去的。”我不服气地反驳道。
“归山是归山,莫跟在他身后,你知道他是干甚的?”阿爸这时也进屋来压着嗓子训我。
“那,守夜、吊丧去不?”我不放心地问,生怕错过了跟冬司供学唱歌。
“当然去,跟我一起,莫要乱跑,小心惊着。”阿妈说。
那天我早早就吃完了晚饭,隐隐听到张家方向锣鼓声声,唢呐齐鸣,感觉百爪挠心,但因为有阿妈警告在前,又不敢擅自前往,终于等到阿妈把家里的活忙完,拿起锁头锁门,这才蹦蹦跳跳地跟在阿妈身后,往张家赶去。
冬司供的吹打班子还有三个伙计,负责敲锣鼓的两位面前挂一面黄澄澄的铜锣,架一大一小两面红皮小鼓,吹拉的一位身边木凳上摆着好几条长短不一的唢呐,还有二胡、笛子,都是好玩的东西,三个人拉开架势,没休没止地吹打起来。屋场上摆满了花圈,花圈上的白字条都签了名,看得出,有些花圈是冬婆扎的,也有的花圈是从镇上买的,镇上买的花圈千篇一律,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冬司供和着吹打班子的乐曲,一边唱着孝歌,一边领着张奶奶的子子孙孙,从前屋钻进去,又从后屋钻出来,从张家奶奶灵前出发,转个大圈,又到灵前结束,结束时大喊一声,孝子叩头,身后的孝子们便规规矩矩地跪下来,朝着张家奶奶的遗体叩头。
灵堂外人来人往,整个村子几乎都搬到了张家屋场,不仅仅是人,还包括各家的生活物什。在月塘村,但凡有人亡故,全村人齐上阵,男人杀猪宰羊,搬桌扛凳,把一村的生活设施都汇聚到一起,女人则架锅洗菜、端茶倒水,忙前忙后就跟做自家家务一样。米面肉菜、油盐酱醋,都管先生能准备的早就准备好,敞开了摆着,供大家使用,准备得不够的,也没人管都管先生再要,谁家里有的,跑回家去拿过来,一起使用,谁也不去计较。每回丧礼开始,冬司供都要清点一回人数,除了读大学的和当兵的,其他劳力都得到场,读大学和当兵都是为国家做事,不能耽误。青壮年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抬棺,村子里路弯山陡,要把棺材稳稳当当抬到山上,绝对是个力气活,不是身强体壮的年轻后生,可不敢让他拢前。
像我这样的年纪,当然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我四下张望,发现转圈的人群里竟然藏着阿桂,阿桂像模像样地低着头,跟着队伍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喊磕头的时候也老老实实地磕头。我一边赞叹阿桂的机灵,一边趁人不注意,一猫腰也钻了进去,与阿桂并肩而行,这样,我就能绕过身后那些鼓吹喧阗,真真切切地听到冬司供唱歌了。
这一回,我完完整整地听清了冬司供的歌词,腔调凄凄惨惨,从张家奶奶嫁过来那天说起,说她一辈子如何独守空房,如何养育儿女,如何忍受流言,如何撑起偌大一个家业。冬司供那一声一调,都唱在了孝子们的心坎上,勾起伤心往事一幕幕,人群里哭声此起彼伏,实在不忍描述,连我和阿桂也跟着流下了眼泪。
也许是受了冬司供丧歌的感染,那些一时得闲,不用帮工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队伍里来,转圈的人越来越多,前头的进了屋,后头的还在往外走,首尾相连如龙蛇般蜿蜒,每个人眼里都满含着泪水,一边缓缓行进,一边还零星诉说着张家奶奶在世时的种种,丧礼一时间变成了大家对张奶奶的追忆。
后半夜的时候,人转累了,走不动了,后厨的夜宵就该上了。冬司供和敲打的伙计也停下来,默默地坐在桌前吃消夜。悲伤归悲伤,吃东西的事情不能耽误。那个夜晚,张家大奶奶的屋门前后洞开,偌大的宅子变成了透明的世界,谁都可以在里面自由穿行。堂屋里,吊丧的人啼哭声声,堂屋外帮工的人忙前忙后,各得其所。
第二天清早,张家奶奶如期上山,出发前,冬司供拿着一份名册,挨个点名,点到名的壮劳力,腰上扎块素白毛巾,摩拳擦掌地站在梨木寿材前,听候调遣。冬司供挑出十六个人,分成两拨儿,头八个站在寿材四周绑好的桑木杆下,一人扶一根杠头,后八个人各扛一把长木凳子,跟在寿材后面,等前八个人抬累了,后八个人迅速把木凳垫到寿材下,就势接过杠头,人歇棺不歇,一路平平稳稳、缓缓朝山头走去。
冬司供一袭长袍,先是站在寿材前鞠躬,算是请张家奶奶起程,然后,铜锣一敲,转身领着八個后生,抬着那口寿材浩浩荡荡就朝张家祖坟走去。冬司供挑平坦的道路,绕着村子满满地转上一圈,尽量让张家奶奶在村子里的最后一程,能够走得远一些,久一些。待一轮红日爬出云头,那寿材已稳稳当当地落在山中。
那场丧事,每个人都怀着无限虔诚,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张家上下感恩戴德,十分满意。丧事结束时,张家人披麻戴孝地给冬司供跪下,磕两个头,便把头上的孝布摘掉,挂在坟前的青松上。冬司供再面向前来送行的全村老小,代张家后人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张家后人给全村老小深鞠躬,丧事便算圆满了。正在众人准备散去时,冬司供站在坡头,清了清嗓子,竟然还有话要说。
转身要走的人于是回过头来,不知道冬司供还要讲什么。
只见冬司供一脸严肃,喊道:“今天张家奶奶的丧事,有劳大家出力,圆满顺利,但有句话还是要说,就是村头李家、村尾王家的两个劳力没回来,这里点一下,以此为戒。”
李家和王家的人一脸黑霜,嘴里嘀嘀咕咕地不知说了几句什么。
我和阿桂跟着人群往山下走,便听到人们议论纷纷。
一个说:“这两家也太不像话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除了读书和当兵,其他劳力雷打不动,都要来抬丧。”
另一个说:“怕是他家有事。”
又一个说:“他们两个在外挣大钱呢,耽误一天,得少挣不少钱。”
人群在山下路口四散,各回各家,村子里又恢复了平静。
我和阿桂回村后,直接钻到了冬司供的院子里,到底还惦记着那些供品呢。待我们从屋檐下钻出来时,见到王家爷爷正和冬司供争论着什么。两个人都直愣愣地站在屋场,冬司供身上的长袍还没有脱去,衣襟飘飘,仙风道骨。
我们侧耳听去,两个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祖上传的规矩就是规矩,要是有一个人破了这规矩,今后谁想不来就不来,谁来抬棺上山?”
“我们家劳力外面活紧,耽搁不起呢。”
“钱可以去挣,但根在这里,该回一定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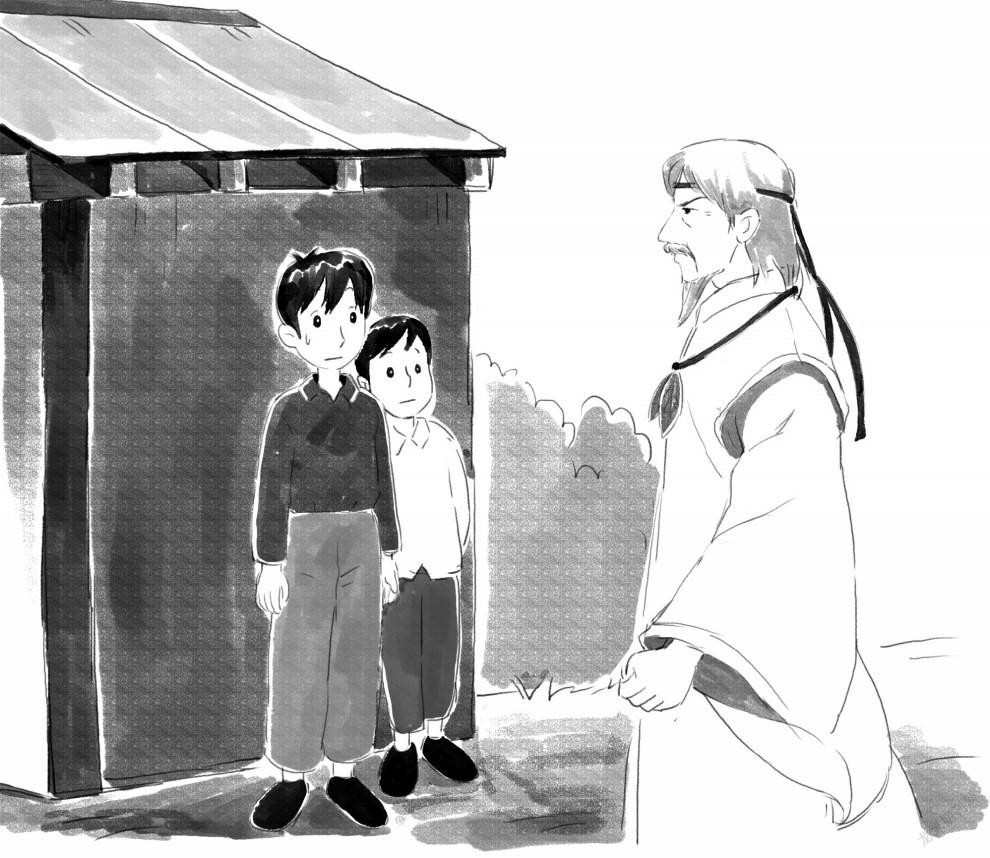
“那恐怕由不得你,你看如今,那打工的人一个比一个走得远,到时看你能叫几个回来。”
“回几个是几个,都不回来,靠我们老把式能把棺材抬山里去?”冬司供表情激动,脸涨得通红,又说,“谁家不回,我都记着账呢,将来有事莫来找我。”
“不找就不找,封建迷信,等我家有事,不用你费心。”王家爷爷一转身走了。
冬司供宽袖在风中发抖:“我一不供鬼神,二不敬钱财,供的是苍生,敬的是亡灵,什么封建迷信……”
院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和阿桂定在屋檐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冬婆见到我俩,阴云密布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意,招了招手,示意我们过去,把那些糖果糕点,摊到一个盆子里端给我们。
我原本是想请冬司供再教几句歌词,但确信当天冬司供一句话也不会说,于是也就作罢,好在还有零嘴可吃,也算没白来。
说来也巧,过不了一个月,王家就真的出事了,王家太奶奶一不小心睡过去,再也没醒来。
一切如同王家爷爷当时摞狠话说的一样,他果然没来找冬司供主事,去城里挣钱的劳力赶回来,几通电话,呼呼啦啦招来一辆中巴和一辆四轮货车,中巴上塞着一个西洋乐队,男男女女都穿着齐整的礼服,抱着亮闪闪的洋乐器,乐队从村口下车后,走一路,吹一路,浩浩荡荡到王家,一下子将全村人都招呼了过去。这一回,王家的子孙也不在村里借锅借凳,四轮货车径直开到屋场,车上的桌椅炊具应有尽有,还有人拿钢管架起一个风雨棚,披上油毛毡,堂屋门口还搭了个舞台,涂脂抹粉的演员拿起话筒唱起了歌,唱的第一首便是“红烛摇,摇来好消息”,紧接着又唱了一首《荷塘月色》,围拢来的人们纷纷鼓掌呐喊,直说唱得真好,跟电视里一样。
村里嫁出去的女儿被娘家召回来,一直要住到下个节气,远房不常走动的亲戚也赶来了,明说这回要住个三两天。后半夜,王家白事上的演出尤其精彩,几个露着肚皮、只穿着短裤胸衣的女子在台上扭来扭去,跳着一种奇怪的舞,乐队的吹奏也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喇叭声。我和阿桂跟着在台下起哄,被阿妈一把拖出来,直喊:“小孩子看不得,看了眼睛要长肉钉。”
两天后,一台扎着花、放着哀乐的灵车直接把王家太奶的寿材运到了狮子山脚下的坟地,连挖坟的劳力,都是外地来的掘墓人,不仅坟坑挖得方正,而且据说还是专挑风水宝地,可保王家家业兴顺,子孙富贵。乐队走前,挨家挨户留下名片,服务标准、价格,一清二楚,先服务,后付款,保您满意,省您奔劳。
这样一来,村子里便刮起了一阵风潮,但凡谁家有丧事,都会努力把乐队请来,有钱的连演三天,没钱的也要演个一天半天,实在不行,东借西借,也要照最低的标价,把乐队请来走个过场,这不是对逝者尊不尊的事,而是事关后代面子的事。面子问题,兹事体大,砸锅卖铁也要办,因此,在这件事情上,谁家都不愿意含糊,我听说村里的王二家,本来日子就紧巴,办了一场丧礼,勒紧裤腰带足足还了三年债。
但即便如此,村里也没有人再来请冬司供主事,仿佛谁家找了冬司供清唱几句,就是对死者不尊,也是顶顶没面子的事。一两年里,冬婆不再在屋前扎花,冬司供也不再唱歌,每每想起冬司供那优美的旋律,我心里还有点儿不舍。冬司供和冬婆把那堆家什用麻袋装好,挂到了屋梁上,老两口安安分分地耕云播雨,不再去管东家长西家短,也不用操心谁的一辈子怎么用歌子唱出来。
全村人的这种忽略对我而言,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连我的阿爸阿妈,也对我时常往冬司供家里跑的事不再忌讳,只是,要让冬司供随口唱几句,就变得很难了,除非拿上好的米酒,把他灌得半醉,起了兴致,但我那时囊中羞涩,自己又不敢喝酒,要哄开冬司供的喉咙,可真不容易。
有一天,我对冬司供说:“要不,我拿支笔,把你的唱词写下来,省得以后,你老了忘记了。”
冬司供笑了一笑:“本就没有词呢,词都住在各家各户,要进得了各家门,才见得到各家词。”
冬司供的话,等于最后拒绝了教我学歌,我也就不好再提了,但这并不影响我和阿桂时常在他家屋场出现,因为尽管没有供品可尝,但冬婆做的红薯干、油巧可依然好吃。
岁月像梓溪河的水一样慢慢流淌,在小河边、山坡下,总有人呱呱坠地,总有人凄然离去,而冬司供的锣已生锈,不再光亮,鼓已斑驳,声音嘶哑,当年跟他一起敲打的三个伙计,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一个盛夏的黄昏,正值我小学毕业,准备转到更远的镇子上去读中学,中学需要住宿,這意味着,我将暂时离开我的村子一段时间。就在那天傍晚,行人行色匆匆,来到冬司供院子里,没有磕头,只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来的是村上的干部,支书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主任、会计,还有生产队队长。
冬司供正躺在摇椅上歇凉,我和阿桂帮冬婆收拾采来的酸枣,酸枣洗净了,煮熟,和着红薯浆做枣糕,冬婆答应把做好的枣糕给我带到学校去。
老支书开门见山:“还得请老先生出趟山呀。”
冬司供应该是听见了,眼睛闭着,却一直没睁开。
良久,冬司供缓缓地说:“这月塘村,除了村口的狮子山,就没有别的山,我还能到哪座山去?”
村支书涩涩一笑说:“五保户刘大喜刚走,你知道,他身边无子嗣,身后无财产,我们村委会,也拿不出钱来请乐队,再说,那也不符合规矩。”
冬司供一听这话,腾地站起来,环顾一下屋梁上的两个麻袋,那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那就麻烦你们,把那两个麻袋取下来。”
“要得要得。”村干部们笑吟吟地搬来梯子,把两个麻袋取下来,扛在肩头就走。冬司供背着袖子,在屋场里来回踱两步,模样像个重掌兵权的大将军。
当晚,冬婆的纸扎搬到了刘大喜的破烂屋子里,在刘大喜身边,冬婆领着阿桂扎了两个硕大的花圈,本来还想多扎一个的,但家里存的彩纸就那么些,最后几朵花,还是一些边角纸料拼凑上去的。
来吊丧的人很少,当年帮冬司供吹打的三个伙计,只有一个年长的过来,其他的,都在外地打工,一时间赶不回来。冬司供望着跟在他身后的我,说:“小子,今天老头要唱一回,你可听好咯。”

那一夜,少了人来人往,锣鼓喧天,冬司供的唱词十分清楚,悠扬清脆,声声入耳,唱的是刘大喜的一生,原来刘大喜年轻时还在上海跑过码头,壮年时还给国家修过铁路,这些事情,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但我相信那些唱词不能生编,一腔一调勾勒的,是刘大喜的人生轨迹。我一边听着一边跟着哼唱,竟看见冬司供的眼里闪着浑浊的光。
刘大喜的丧礼,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丧礼,没有乐队,没有宴席,没有孝子围着灵堂转圈,有限的几个邻居陪着遗体坐了一晚上后,第二天,村委便雇来一辆拖拉机,把那具薄木寿材送上了山。倒是冬司供,唱了整晚,那情绪气场,跟几年前没有两样,但因为环境过于空旷,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送完刘大喜后,冬司供便一病不起,在床上足足躺了半年。等我寒假回到村子时,床上的冬司供已经认不清人,连我也不认识。我试着给他唱了几句他教的歌子,他目光呆滞,毫无反应。
一个天空飘着雪花的清晨,冬司供安静地走了。他走的那一晚,曾經跟着他的三个伙计都赶了过来,坐在他身边吹打了一晚上,因为没有人会唱孝歌,丧礼显得少了些什么。冬婆在屋中间堆了一堆柴火,毕毕剥剥地烧了一晚,我曾经使劲回想冬司供教过我的那些歌词,本想唱给他听的,但因为从来没有跟吹打班子合作过,总是对不上辙,胡乱唱了几句,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几个伙计干脆也停下来,开始一点点跟我讲起冬司供漫长的一生。那个年长的说,冬司供当年跟刘大喜一起跑过码头,后来还参加了修三线,所以,那天冬司供唱的刘大喜,很多地方当作他自己。我一时间神情迷离,冬司供坐在刘大喜灵前唱歌的音容历历在目,恍惚间,冬司供坐到了自己灵前,为自己唱歌,守护自己在这世间停留的最后一晚。

第二天,在家的村民都赶到冬司供门前来送他一程,说在家的人,其实也就几个老弱病残,壮劳力都不见了踪影。几个年纪稍轻的老头儿,为冬司供抬棺,由于他膝下无后,找不到扶灵捧相的人,我和阿桂斗胆站了出来,我给他捧起了遗像,阿桂举着引路幡,两个人走在棺前压路,一行人摇摇晃晃,把他送到了狮子山。
月塘村,从此再也没有了护灵人。
冬司供归山的那天,冬婆没有出门相送,只是静静地坐在家门口,眼睛呆呆地望着狮子山。
从那一天起,凝望那座山,想念那个人,变成了她余生的全部。
选自《儿童文学》2019年第8期
谢淼焱,1979年出生,湖南益阳人,现居长沙。2013年前在军内外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通讯若干,女儿出生后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儿童文学、校园文学年选,出版有长篇小说《沧水谣》,曾获第四届儿童文学金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