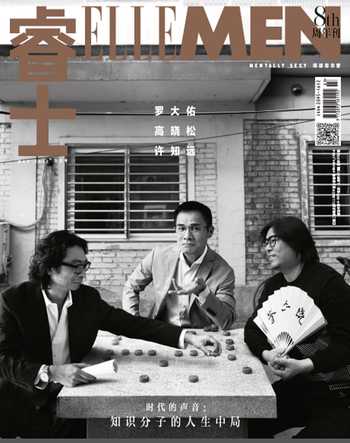爸爸有言:家庭秘密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我确实希望是儿子。不是重男轻女,也不是为了性别平衡的儿女双全,而是我不太习惯家里只有我一个男性和太太女儿在一起,回家
就是轻轻的欢笑,不吵闹,然而总有个女人持续在说话,卧室是紫色的。
我自己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很少有我熟悉的那种女儿含着眼泪不说话,或者和妈妈你一句我一句争吵的时刻,都是打架和教训。现在,二哥还在,大哥去世十多年了。去世时他在市委办公厅担任副职,他年轻时是戏剧学院毕业,在宣传系统工作,因为笔头好,被时任市委书记看上了,调任文字秘书十年,很亲近。这种情况里,倘若省长高升,他也会跟着走的,然而书记是老人了,没有再向中央移动,退休于人大常委会任上,到回嘉兴颐养天年以后,又受牵连查出在任时的问题。没有追究,不过大哥就始终是写材料,不大有仕途的机会了。
大哥去世后,我父母叫开锁匠来,打开两只上锁的书桌抽屉,发现了一本厚手稿,是他的字迹,钢笔誊写在顶头印有“市委办公厅”的红格原稿纸上。那是一部电视剧本,他写到第38集,已经完成的部分应该是定稿了,只有少数圈圈点点的改动。这么厚的稿子,想必他写了很久。我们没一个人在他生前曾听说过他在写剧本这件事。同一只抽屉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三篇打印出来、没有署名的小说,一篇像片断杂记,另外两篇很完整,长度应该说是在短篇和中篇之间,我上网搜索,没有搜到相近的文章,应该也是他写的。
保险柜里倒没什么。也没有日记。没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东西。
大哥去世时是48岁,正是本命年的年初,还没来得及在艰险来临之际系红腰带辟邪,就遇上了一生最大的艰险。胰腺癌这种东西,用大夫的话说,是“很恶”的,来了就要死人,坏处是很疼,人走得快,好处也是走得快。他常有疼痛感,但他总加班,时常住在单位办公室,慢性病也多,头痛胃痛之类的话,我父母都听习惯了。直到单位体检,查出胰腺癌晚期,四个月即告去世,我母亲多年为疏忽而自责。生前,他业余偶去钓鱼,更多时间是和早年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两位朋友下围棋,都是很安静的爱好。他和我大嫂没有孩子,感情也比较疏远。他去世时,我太太刚和我谈恋爱不久,还是小姑娘,没经过什么世事,偷偷问我,“他们是自由恋爱吗?”她还以为只有指腹为婚或者许配过去的夫妻才会不亲密。现在她应该明白了。
有些人说上海男人常常是这样,有自得其乐的爱好,修钟表,看老电影,收藏唱片,跳国标,据说现在还有爱好自己编程的老头,也算与时俱进。当年把大哥的电视剧本和小说读下来,我父母为他骄傲,我父亲说,“他是有精神世界的人”,又深恨自己在他身前不够了解他,我母亲说,“他心里藏了多少话啊!”
我则忍不住为他哭。那剧本和小说写得太差了。不是不熟练,是平庸,又俗气。剧本写的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故事,一位官员,在繁重的工作外,认识了一位下属单位招待他的女孩,又在采访中认识了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电视台女记者,产生了情感纠葛。读起来我觉得有现实中的痕迹,不过没有和父母交流过,当然更没问过大嫂。他写剧本说明,“XX露出酥胸,皮肤雪白”,也写政府由于土地出让而起的一场明争暗斗,开会,出游,溜须的疲惫感与成就感。小说中那两篇长一些的也是官场故事,杂记是写下围棋的几个人物,中间提到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向往,但读起来还是像官场,下棋的人都像在参加锦标赛,勾心斗角。
我没法不去想他花了多少个耗在办公室的深夜,写完文件后拼命写着这些,在单位写完一稿,拿回父母家来藏着。
然而他里里外外都是個官员了,套中人,困在他想记录的那些东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