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绿绸衬衣
[德]海因里希·伯尔

我按照别人教的那样,不敲门就径直走进屋里。然而,当我看到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在她的脸上,我看到了一些很难见到的东西:健康、自信、安详,还有美妙的色泽。
女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冷漠。她在桌子旁边择菜,桌子上放着一个盛有吃剩的蛋糕的圆盘子,一只大肥猫在盘子边闻来闻去。房间又低又窄,空气十分混浊,弥漫着一股油腥味。畏缩的我,目光在健康女人的脸、猫和蛋糕之间来回打转,一种呛人的苦涩涌在喉间,噎得我十分难受。
“什么事?”她头也不抬地问。
我颤抖着双手,费力地拉开手提包的拉链,取出了东西:一件衬衣。“一件衬衣。我想……一件衬衣……也许……”
“我丈夫的衬衣已经够他穿十年了!”说完之后,她好似偶然将头抬起,牢牢地盯着那件柔软的绿衬衣。我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突然出现的、无法克制的欲望,我想这件事十拿九稳了。女人连手都没擦,就拿起绿衬衣,提着衣服的肩部,来来回回检查每一道接缝,最后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
我不安且不耐烦地看着女人又去把洋白菜收拾干净,然后走到灶台旁将嘶嘶作响的锅盖掀起。霎时,香喷喷的热油味在狭小的空间里散开。油在沸腾。即使锅子盖着盖儿,我相信自己还是听到了猪油块噼里啪啦的蹦跳声,因为那段遥远的记忆告诉我:那是猪油,锅里是在炼猪油。她还在削洋白菜。不远处,母牛在“哞哞”地叫,手推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还站在门口,而我的衬衣在那把肮脏的椅背上轻轻摇晃,那件柔软的、我心爱的绿绸衬衣,我曾向往了它七年之久……
犹如站在烧得正旺的炉子上,沉默憋得我喘不過气来,有种难受的窒息感。此时,蛋糕上黑压压一片全是懒洋洋的苍蝇。饥饿和极其难受的恶心,化为一种呛人的苦涩,生生把我的喉咙塞住。我开始冒汗。犹豫不定中,我终于伸手拿起衬衣。“您,”我的声音比刚才更加嘶哑,“您……不要吗?”
“你要换什么?”女人冷冷地问道。洋白菜已被她削干净,接着她将菜叶装进漏勺,用水冲洗,然后掀开炼油的锅盖将菜叶倒进去。让人垂涎欲滴的声音和香味再一次让我想起往事,想起好似一千年以前的往事,而我,现在也只有28岁……
“喂!你想换什么东西?”女人不耐烦地催促道。
虽然去过克拉斯诺达尔到格里内角的所有黑市,可我……可我不是商人。我瞠目结舌道:“面包猪油……或许面粉也行,我想……”
她第一次抬起头,用那双冷漠的蓝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在目光对碰的一刹那,我知道没有希望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知道猪油的味道,它对我来说,将成为永远让人痛苦的回忆……她的目光射向我,穿透了我。现在我的内心空空如也,对一切都已无动于衷。女人哑然失笑。她用讥讽的口吻说道:“这件衬衣,它值得我用几张面包票去换?”
我一把夺过衬衣,用它拴住这个大声嘶吼的女人的脖子,将她像淹死的猫一样,吊挂在那巨大的黑沉沉的耶稣受难像下面,那画像就在她头上方的黄粉墙上……当然,我只是这样想象。事实上,我抓起心爱的绿绸衬衣,将它团成一团塞进手提包,转身朝门口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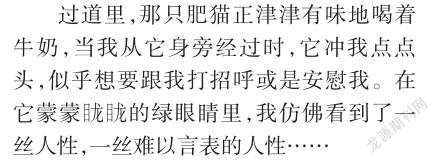
有人跟我说过,要有耐心,于是我决定再试一次。为了躲避明朗得让人压抑的天空,我一路奔跑,跑到一处不认识的地方,越过苹果树下的臭水坑和正在啄食的鸡群,来到了一座古老椴树庇荫下的农家院落。我猜肯定是喉咙里的苦涩让我的眼睛变得模糊了,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看到房前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身强体壮的农家小伙子,他正在跟两匹吃食的马儿亲热地攀谈。小伙子看到我,透过一扇打开的窗户笑着朝屋里喊道:“妈,十八号来了。”说完,他十分开心地拍拍大腿,开始往烟斗里装烟丝,而回答他的是一阵响亮的咕咕声。一秒钟后,窗框里闪现出一个精神饱满、脸膛棕红的女人,她的面孔就像一个热乎乎、油亮亮的煎饼。我立马转过身去,经过嘎嘎乱叫的鸭群、鸡群,还有水坑,向后跑去。我把手提包紧紧地夹在手臂下,像疯了一样跑得飞快,直到看见直达村子的道路才放慢脚步。我从半个小时前登上的这座山上又走了下去。
当我重新踏上这条两边长有可爱树木的银灰色蛇形道路时,我的脉搏跳得平稳了;当我坐在那个荒芜、多石、霉味弥漫,却是由村中道路通往康庄大道的岔路口时,喉咙间的苦涩味道退去了。
我大汗淋漓。
突然,我莞尔一笑,点燃烟斗,将身上那件又脏又旧、浸满汗水的衬衣脱掉,迅速换上柔软凉爽的绿绸衬衣。一股舒适、透爽的感觉油然而生,贯穿全身。于是所有的苦涩全都化为乌有,彻底从我身上消失了。我沿着公路重新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去,我的内心深处燃起一种憧憬,渴望看见城市里那些贫困、丑陋的面孔,因为在那些变得难看的面孔之下,我还能看见困难中的人性。
选自《第一次的茉莉》,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1月版
海因里希·伯尔,德国著名作家。20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伯尔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巅峰。代表作有《女士及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等。海因里希·伯尔曾多次获得国际重要文学奖项,被誉为“当代德国的歌德”和“国际文坛巨匠”,197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