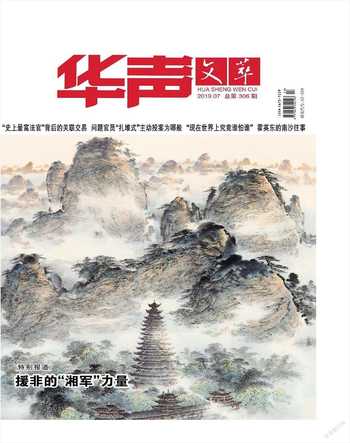美妙得无法解释
2019-09-10 07:22:44熊培云
华声文萃 2019年7期
熊培云
我上大学那年,弟弟只有六岁。第一次放寒假,我带回了一台单放机和几盒磁带。有一天早上,弟弟钻进了我的被窝。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听《梁祝》,于是就取下耳机罩住他的耳朵。那是弟弟第一次听世界名曲,他满脸的惊喜之情,我至今未忘。雖然弟弟只会说“真好听啊!”,但我知道,在那一刻,这幼小的生命被美好的东西打动了。
《梁祝》为什么好听?六岁的弟弟答不上来,现在的我也一无所知。这世界上有些美妙的东西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怀念某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或者黄昏。人生如寄,所幸还有音乐。音乐是我在人间感受到的最奇妙的东西。虽然我没有真正创作过或者拥有过任何一首歌曲,但那些动人的音符一直在精神上滋养和丰富着我。那些源自心灵深处的寂寞、牺牲与欢喜,直接通向的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正是基于深藏于人心中的美的激情。
而就在此刻,当我开始写作这篇文字时,耳畔交替响起的是阿炳的《二泉映月》和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几十年前,小泽征尔曾说过《二泉映月》这支曲子他必须跪着听。而《如歌的行板》也让托尔斯泰潸然泪下。有关这两部作品的经典诠释是,它们演绎了人类苦难的灵魂。然而,即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人物,也列不出一个公式来向读者解释,他为何会热爱这种悲怆之美。
人终究是一种美好的动物,这是我唯一可以断定的。所以,人总是沉浸于搜集并赞美各种美色、美音、美景、美酒、美好的人格……而如果有志同道合者,他还要追求美丽新世界。
(摘自《慈悲与玫瑰》)
猜你喜欢
特区文学·诗(2022年4期)2022-05-30 19:03:07
祝你幸福·午后版(2017年5期)2017-08-07 18:35:55
中国音乐教育(2017年3期)2017-05-20 09:19:52
唐山文学(2016年2期)2017-01-15 14:03:59
——二胡曲“二泉映月”演释[1]的多元化与一元化辨析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6年1期)2016-11-26 02:29:57
知音励志·社科版(2016年8期)2016-11-05 05:07:46
时代青年(上半月)(2016年4期)2016-04-14 18:36:04
意林(2016年2期)2016-03-07 18:46:33
读者·校园版(2015年24期)2015-05-14 13:11:48
阅读与作文(初中版)(2014年10期)2014-10-28 05: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