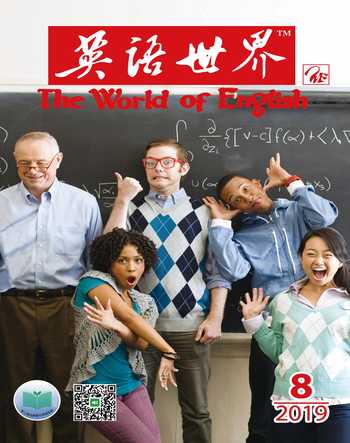从余光中的译论译品谈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七)
金圣华
伊尔文·史东著的《梵谷传》(Irving Stone, Van Gogh, Lust for Life)是余光中翻译的另一部力作。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史东“以小说来还原梵谷破画而出的生命故事”1,因此,译者的首要之务就是如何在译文里再现画家这种“腹内蠢蠢欲动”“气蟠胸臆”2的感觉。
此书翻译之初,余光中和夫人范我存尚未共谐连理,情侣俩在一人翻译、一人誊写的紧密合作下把全书译完,因此散文家张晓风称之为两人“婚前所生的孩子”3。然而随着余光中年事渐长、功力渐进,这本于1955年翻译的作品在1957年由重光文艺出版社出版;1978年重新修订,由大地出版;2009年再度仔细校订,交由九歌隆重刊行。《梵谷传》由最初的版本到最后的定本,译程历时逾半个世纪,内容修改近万处,这种努力堪与翻译名家傅雷三译《高老头》相比,因而此书不可不谓余光中在翻译版图上呕心沥血、千锤百炼的传世之作。
《梵谷传》最精彩的莫过于对色彩的描绘。由于主人翁是梵谷,所以作者笔下形容的色彩也是浓烈激越而非淡雅素净的,译者一不留神,就可能把梵谷翻译成莫奈。且看以下的片段4:
But it was the colour of the country-side that made him run a hand over his bewildered eyes. The sky was so intensely blue, such a hard, relentless, profound blue that is was not blue at all; it was utterly colourless. The green of the fields that stretched below him was the essence of the colour green, gone mad. The burning lemon-yellow of the sun, the blood-red of the soil, the crying whiteness of the lone cloud over Montmajour, the ever reborn rose of the orchards…such colourings were incredible. How could he paint them? How could he ever make anyone believe that they existed, even if he could transfer them to his palette? Lemon, blue, green, red, rose; nature run rampant in five torturing shades of expression.
再看下面的几种译文:
1. 可是使他伸手翼蔽自己愕视的双眼的,却是四野的色彩。天空蓝得如此强烈,蓝得硬朗,苛刻,深湛,简直不是蓝色,完全是没有色彩了。展开在他脚下的这一片绿田,可谓绿中之精,且中了魔。燃烧的柠檬黄色的太阳,血红的土地,蒙马茹山头那朵白得夺目的孤云,永远是一片鲜玫瑰红的果园……这种种彩色都令人难以置信。他怎么画得出来呢?就算他能把这些移置到调色板上去,又怎能使人相信世上真有这些色彩呢?柠檬黄,蓝,绿,红,玫瑰红;大自然挟五种残酷的浓淡表现法暴动了起来。(余光中译5)
2. 郊外风光颜色缤纷,把他弄到目眩神迷。蔚蓝天空是一片酷蓝,蓝至无底,令人不见其为蓝,而变为柠色。平原绿地是一种绿色,成为惨绿。太阳的柠檬黄,焦土的血红,芒马苏岗上片云盖顶,化为奇白,花圃中有常开的玫瑰花……各色呈现,真是不可思议。教他如何下笔呢?纵使他能够入画,又有谁相信呢?柠黄,蓝青,碧绿,血红,玫瑰;大自然在怒吼了,表现着五种悲昂的色调。(林继庸译6)
3. 不过,促使他伸手去摸自己被迷惑的双眼的却是乡间的色彩。天空是如此浓烈的蓝色,那样凝重,深沉,竟至根本不是蓝色而全然成了黑色;在他下面伸展开去的田野是最纯粹的绿色,非常非常的绿;太阳那炽烈的柠檬黄色;土地的血红色;蒙特梅哲山上寂寞的浮云那耀眼的白色,果园里那永葆新鲜的玫瑰色……这样的色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如何能把它们画下来呢?即使他能把这些色彩搬到他的调色板上,他又怎么能让人相信它们的存在呢?柠檬黄,蓝,绿,红,玫瑰,大自然信手把这五种颜色摆在一起,形成了这种使人难受的色彩情调。(常涛译7)
上述的三个例子,可以看到译者的翻译手法大有分别。这是原著第六章“阿罗”(Arles)中的一段。话说梵谷来到了法国南部小镇,准备潜心创作。该处风景如画、阳光炽热,使画家创意勃发、精力旺盛。作家此处描绘的郊野,并非只是彩色绚烂、花团锦簇,而是生气勃勃、动态毕呈的。原文中形容色彩而采取的一些特殊詞汇,如intensely blue、hard、relentless、mad、rampant、torturing等,余光中都紧贴原文,如实翻译成“强烈”“硬朗”“苛刻”“中了魔”“暴动”“残酷”,因此形成了一种骚动不安的情绪,跟画家内心蠢蠢欲动的感觉里应外合,互相关联。
例2的译文,由于成文颇早(1955年),所以并没有太多目前恶性西化的译文腔,然而把“蔚蓝”形容为“酷蓝”,再转而为“柠色”,把torturing shades of expression翻译为“悲昂的色调”,实在跟原文相去太远,再说,“郊外风光颜色缤纷,把他弄得目眩神迷”一句,也太流于笼统,无法传达出原著意欲表现的风格。
例3出版于1983年,凡是余光中执意避免的译文腔,几乎都罗列齐全。例文一开始长句中的“的的不休”和被动句法、代名词的重复使用(如“它们”的一再出现)、句法的冗长、选词的不当(如“令人难受的色彩情调”等),都使这段描写色彩的译文念来冗长累赘、毫无生气。
一个称职的译者,必须能挣脱原文句法的箝制,就如杨绛所说,翻完跟斗,要立起身来;而翻译的过程中,面对原文,何者重要、何者次要,要能知所选择,从而紧贴文气,在译文中从容道出,如原文长句中的the crying whiteness of the lone cloud, 余译把lone cloud译为“孤云”,而不是例3的“寂寞的浮云”。译文中面对原文,何时拉长、何时缩短,这松紧得宜、舒展自如的手法,正是营造创作空间的妙方。 □
——意群—动态对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