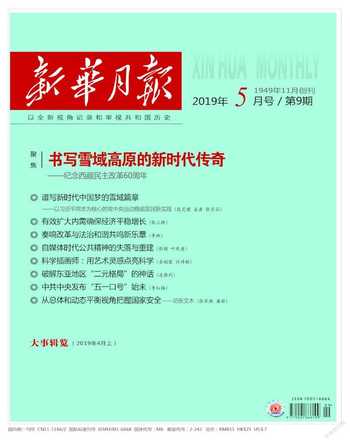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胡建淼
1801年12月,威廉·马伯里(William V. Marbury)等4人,在他们的律师查尔斯·李(Charles Lee)的协助下,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了诉状,郑重请求法院判令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向他们送达哥伦比亚特区治安法官的委任状。由于马伯里是首位原告,被告是扣留他们委任状的国务卿麦迪逊,联邦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是1803年,因而在历史上被简称为“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该案的发生与美国的政党制度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坛中党派斗争的产物。经过6年的反英独立战争,美国终于在1783年脱离英国赢得独立。1787年9月,经联邦制宪会议制定通过,在美国费城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即美国联邦宪法。1789年3月4日,宪法正式生效,联邦政府同日宣告成立。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军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被推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尽管美国宪法并没有确认政党制度,而且开国元首华盛顿总统又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但是党派从那时起已埋下种子。华盛顿在任期间,内阁中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两人政见对立,逐渐形成了两大派系。华盛顿退休后,美国政坛中的两大政党终于正式形成。拥护汉密尔顿的一派正式组成了联邦党,拥护杰斐逊的一派自称为民主共和党。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属于联邦党人。他在第三届总统选举中将让位于属于民主共和党人的托马斯·杰斐逊。亚当斯在其任期(1797—1801年)的最后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经即将换届的参议院批准,突击任命了42位“清一色”的联邦党人为治安法官。后人把这批法官挖苦为“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s,又译“星夜法官”)。按照法律程序,治安法官任命应当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委任状,发送给当事人后正式生效。在亚当斯突击任命的42位治安法官中,其中有17位虽然经过了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等环节,但其委任状留在既担任国务卿又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的办公室。
当时正是新旧总统交接之际,约翰·马歇尔一面要作为旧一届的国务卿向新国务卿交接,另一面又作为首席大法官要主持新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在忙乱中因疏忽而将其中的17份委任状,在卸任国务卿之前没有及时发送出去。继任的新总统,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对于联邦党人在权力交接前夜大搞以党划线、“突击提拨”的损招早已深感不满。当听说有一些联邦党人法官委任状滞留在国务院之后,他立刻命令新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扣留了这批委任状,并示意麦迪逊将它们“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掉”。
在这17位由前一届总统任命又被新一届总统下令扣留委任状的治安法官中,威廉·马伯里就是其中的一位。马伯里是华盛顿特区乔治城一位41岁的富商。他虽然家财万贯,但对治安法官这个七品芝麻官情有独钟,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马伯里拉上另外三位同病相怜的拟任治安法官,聘请曾任亚当斯总统内阁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也称“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为律师,把国务卿麦迪逊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他们要求最高法院下达执行令,命令麦迪逊交出委任状,以便完成治安法官任命的法律程序。控方起诉的根据是国会制定的《1789年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条中d款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惯例保证的案件中,有权向任何在合众国的权威下被任命的法庭或公职官员下达执行令状。被控方麦迪逊便请杰斐逊总统内阁总检察长莱维·林肯出任自己的辩护律师。两位总检察长担任了两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使得事件颇富戏剧性,一场催生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诉讼也由此拉开序幕。
这一棘手的案件恰恰回到了上一届国务卿、现在依然是首席大法官的约翰·马歇尔手上。在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的体制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严格区分、相互独立,且无高下之分。而且在这一体制的背后,又是浓厚的党派之争。这样,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使马歇尔大法官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他不判决麦迪逊扣发委任状行为违法,不符合正义性;但若依据《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签发执行令,命令麦迪逊按照法律程序发出委任状,麦迪逊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的杰斐逊撑腰,肯定不会执行……这种结果,不仅会愧对同一阵营中的联邦党人战友,而且会使最高法院颜面扫地。
审还是不审,以及怎样审,成为一个令马歇尔极为头疼的大难题。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思冥想,本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他,运用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智慧,作出了一个令后人拍案称奇的绝妙判决,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经典判例。1803年2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以4比0的票数(有两位大法官自行回避)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作出裁决。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主持宣布了法院的裁决书。整个裁决书的内容提出和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马伯里是否有权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裁决书指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对他拒发委任状,不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而恰恰是侵犯了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这里首先确认了麦迪逊扣留马伯里委任状的违法性。
第二,原告马伯里的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法律救济?关于这一问题,马歇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论证说: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治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为任何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法律救济,否则就配不上“这个高尚的称号”。
第三,如果政府应该为原告提供法律救济,是否该由最高法院来下达执行令,要求国务卿麦迪逊将委任状补发给马伯里?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上述两个问题答案的思路和逻辑继续推论下去的话,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也将是肯定的,理所当然地就该由最高法院向国务卿麦迪逊下达强制执行令,强制其发送被扣留的对马伯里的委任状。可是,马歇尔到此突然一转,引证宪法第3條第2款说:“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一方当事人的一切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辖权。对上述以外的所有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具有上诉管辖权。”言下之意,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当事人既非外国使节,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所以最高法院没有初审管辖权。马伯里应当到地方法院起诉,然后逐级上诉到最高法院,不能一开始就起诉到最高法院。但控方申明,他们直接起诉到最高法院的法律依据是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
针对这一点,马歇尔又解释说:《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是与宪法相互冲突的,因为它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执行令时,实际上是扩大了宪法明文规定的最高法院司法管辖权限。如果最高法院执行《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限。他最后说:“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而马伯里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耗时太久,他最终撤回了起诉。
马歇尔的判决既表现出司法部门的独有权威,又避免了与行政当局和国会的直接冲突,为确立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这个分权与制衡体制中的重要权力奠定了基石。从此美国确立了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体制,最高法院拥有了解释宪法、裁定政府行为和国会立法行为是否违宪的权力。在以判例法为主的美国,立法和行政部门无权推翻最高法院对马伯里案件的判决。相反,按照英美普通法系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原则,此判决将作为宪法惯例被后人永远引用。据统计,在最高法院以后的判决中,马伯里案高居被引用案例之首,达数百次之多。
根据这一经典判例逐渐确立的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权随后不断获得清晰:1.联邦法院是联邦立法和行政部门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合宪性的最终裁定者;2.联邦法院是州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合宪性的最终裁定者;3.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审查州法院的刑事与民事程序法规,以确定这些程序法规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要求。
一百多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赞叹道:“马歇尔在美国宪法上深深地烙下了他的思想印记。我们的宪法性法律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形式,就是因为马歇尔在它尚有弹性和可塑性之时以自己强烈的信念之烈焰锻炼了它。”马歇尔传记的作者史密斯(Jean E. Smith)赞扬说:“如果说乔治·华盛顿创建了美国,约翰·马歇尔则确定了美国的制度。”
时隔216年后的今天,我想评论的是:马歇尔在1803年创设那个判例时,或许并没有后人所评价的那么伟大。他用一种“不伟大”创造了一种“伟大”。他当时仅仅是为解脱党派之争对最高法院司法权威提出的挑战想出的一种“滑头”做法。这样的判决既维护了他同党派战友的利益,又不使最高法院威风扫地,相反为最高法院争取到宪法本身不明确的权力。随着这一判例的反复引用,判例的价值得到清晰并发扬光大。我以为,这一经典判例的意义在于:
第一,将权利救济列入法治国家的衡量标准,确立了司法最终原则。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权利救济的法律途径;司法对一切纠纷的最终裁决,应当具有最终效力。否则,就称不上法治国家。这为美国法院于2000年对小布什与戈尔选票之争的最终裁决打下了理论和制度基础。
第二,确立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行为都是无效的法治精神。这一美国宪法原本没有明文表达的精神,通过这一判例得到确立和发扬。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文本中明文规定了宪法的最高地位、最高依据和最高效力,确立了“违宪无效”的最高法治原则。
第三,阐释了为维护宪法权威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道理。为了保证宪法在一个国家中的最高地位,保证一切立法和行为与宪法相一致,就必须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美国所建立的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机制,在美国发挥了理想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模式。目前世界上除了由普通法院作违宪审查之外,还存在由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和议会等作违宪审查的模式。
当前,我们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了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憲法权威。”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借鉴国外有用的经验,立足本国实际,建立和推进合宪性审查机制,如期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法治目标。
(综合3月27日、4月3日、4月10日《法制日报》。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