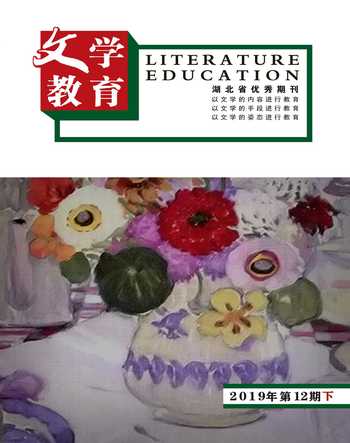文化断裂时代的文学教育
国庆70周年,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一时刷屏。不过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的许多年轻人,尽管他们唱着“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可是打开他们的微信名,所看到的地址一栏里,却有好多并非标注着他们的家乡或是他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城市,并非中国,而是冰岛啦、芬兰啦、直布罗陀、马尔代夫之类“充满诗意的远方”。显然,这个现象如果深究,那么得出的结论肯定令人不大愉快。但是轻轻放过,那么一面给微信头像打上国旗标志,一面却在微信资料上将自己登记为“外国”的居民,这总还是让人觉得有些违和。我们是否可以认定这样的一大批的年轻人,他们实际上内心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视为某个外国的“精神国民”呢?
这些为年轻人所热衷的外国,一般都不是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之类与我国存在国力与意识形态竞争关系的西方大国,而是一些风景优美、生活闲适、偏于小众的国家。所以,年轻人自我标注的那些“外国”,并非是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表达,而是出于生活方式层面的向往。我毫不怀疑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忠诚,这种热爱与忠诚是国家民族利益层面上的,是政治意义上的热爱与忠诚。但是同时我也看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年轻人,在享受着大国之强大的地位与尊严的同时,也承受着大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生活在一个大国,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空间、感受着社会科技进步与时尚变化的主流,但同时也不得不为社会资源的紧张及其分配的竞争性而感受着越来越多的焦虑和疲惫。所以每逢周末、假日,城里的人便跑到乡村,飞向海岛,寻找高山、沙漠。这或许正是年轻人在微信上将自己的地址标注为外国的精神内因。这看上去有点像“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赋予了这句话以深厚的内涵。但是很难因此就说我们的年轻人真的“生活在别处”。因为他们分得很清楚,他们会在城市/乡村、工作/休闲等等不同的生活方式中自由地切换。在现实中,他们是理想的;在理想中,他们无比现实。
如果要说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相比,在文化上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根本的不同倒不在于其所拥抱的文化本身有什么不同,不在于过去的年轻人以西方主要发达富裕国家为自己国家发展的对标,而现在的年轻人却喜欢小众的海岛休闲浪漫小国。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的年轻人你可以根据其所拥抱的文化将他们分群归类,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却让你一言难尽、并不彻底。不否认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可是这热爱不彻底,因为私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自己的微信名注册的地址是外国。当然因此就说他们不爱自己的国家显然也批评得太重,他们不过是好玩,一时的寻求新奇,渴望远方,和那种拿外国护照却歌唱祖国的两面人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对于这个多少有点令人尴尬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去描述,去尽量接近这个现象的本来面貌,但是却无法为之做出一个定性的阐释。就好像你既不能因为年轻人选择了大城市的生活而说他们只不过是追求功利的机器,也不能因为他们同时又向往着乡村与海岛的闲适就说他们都是怕苦怕累的好吃懒做之徒。
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的出现与繁荣,激发了年轻人潜在的自我表现的欲望。是的,这是自我表现,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让别人看看我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然而,如果就此定性,卻又与真实情形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究竟是强化了我们的自我表现呢,还是使得我们更倾向于去迎合?因为最纯粹的自我表现是不需要顾及别人的观感的。就好像唯美主义,就好像先锋派艺术,重要的不是你觉得,重要的是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懂不懂,重要的是我表达了。然而,点赞、转发与分享机制的确立,却促使一个表达者同时去关注反馈效果。适当的反馈确实可以刺激进一步的自我表达的欲望,但是这种自我表达却悄然变味而成为迎合。于是就有了“人设”,要让自己显得是个什么样的类型,从而让自己更受欢迎。自从“人设”意识产生,自我表达就开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所以,自媒体到底是自我表达的新工具,还是迎合公众的新途径呢?你同样无法定性。
当代传播技术导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媒介向终端的转化。媒介是公共的,对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内容和观点。当然媒介也需要通过终端才能到达用户,比如一份报纸,比如一台电视,但是每份报纸上都是同样的内容,每台电视都播出同样一组频道的同样的内容。而自从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之后,伴随着大数据、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公共”的媒介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每个人手里内容各不相同的终端。不同的内容组合、不同的内容设置,不同的内容推送使得既往传播生态中统一的中心消失了。每个人的终端都建构了自己的朋友圈、生活圈和信息圈,每个人手里的信息终端都是不同的世界,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手里的终端或被动或主动地构建自己的世界。巴赫金所说的复调世界,原来只是存在人们的感受体验当中,现在,它已然物化为人们手里各自的终端了。人们日益地不是生活在由媒介构成的公共世界中,人们日益生活在由终端构成的自我世界中。尽管这个自我世界的几乎所有材料都是来自于外部世界,但是它们实际上已经重新组合和转化,就好像构成生命的材料其实都来自于外部世界,但最后它们都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
这个“终端”日益智能化,不仅仅是智能手机,还可以是智能语音聊天器,乃至于智能机器伴侣,或其他生活、穿戴设备。我们会感到,和这个终端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要轻松愉快得多,而且它还可以解决我们的生活便利问题。在发达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不仅结婚率、生育率下降,连恋爱率都在下降。有了这样的终端,似乎没有伴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现实的伴侣需要两人之间磨合,需要两个家庭之间磨合,实在是麻烦。而有了这个终端,游戏娱乐、聊天慰藉、生活购物,一应俱全。由于它通过算法,迎合使用者的喜好,所以它就是另一个自我。我们常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是最理想的恋爱。现在,终于找到了。不,不是找到了,而是终于造出了自己的另一半。
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这样一种传播生态下,人们本来应该更自我、更加具有精神独立性,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资本、商家前所未有地尽情地制造着各种焦虑、各种生活价值观、各种消费时尚或是鄙视链,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利润。终端,究竟是另一个自我,和你相互创造共同成长,还是为你量身定做的电子精神锁链?终端,到底是让我们更加独立,更加完整,还是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这同样是一件无法定性的事情。
2016年,英国牛津字典将Post-truth(后真相)作为年度词。所谓“后真相”,本意是事实和真相日益虚无化,情绪和心理日益主导公众的意见。许多西方传播学者认为“后真相”意味着一种情绪的操控以及对事实的情绪化包装和歪曲,由此将导致偏见。所以这个词汇的本义是贬义的。然而在我看来,“后真相”是一个无关褒贬的描述,它更多意味着一种暧昧,或者说就像物理学中所说的“量子叠加态”,在同一时刻,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同时拥有波和粒子两种不同的状态。就如同范冰冰在宣布她和李晨分手时说的那句话:我们已不再是我们,我们仍然是我们。如果你非要寻求一个确定,一个本质,一个纯粹,如果你非要寻求一个“是”,那么你一定会“测不准”。
由此,阐释的链条将开始断裂。按照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所说,“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阐释者说,瞧,你没看见X其实是——或其实意味着A?Y其实是B?Z其实是C?”(见【美】苏珊·桑塔格著《反对阐释》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而这种转换所依据的基本方法正是为古典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所共同遵循的规则——阐释学的循环,即根据个别、部分、具体解释整体和永恒,以及根据整体和永恒解释个别、部分、具体。
正是依赖于阐释,不断的阐释,不断将新的现象纳入到既有的经典和思想的普适性中,同时也根据新的现象对经典和思想适当调整以维持其普适性,思想和经典才得以流传和接受。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经典,都是通过阐释建立其思想形态的权威地位,并实现其传承的。比如在中国儒道思想的传承中,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都是最有影响的阐释著作。除了这些专门的阐释著作外,还有大量的诗词文赋、诗话词话,都在对这些经典化的思想进行各自的阐释。而各种现象作为个别、部分、具体,通过阐释,也和经典、思想的整体性、永恒性相互印证、适当调适。
可是如今我们却无法确定我们自己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中,某一个行为,比如发朋友圈,用美颜相机来个自拍,这个X,究竟意味着自我的确认,还是向着流俗低头?这个X,它到底意味着A,还是B,还是C?无法确认啊!终端代替媒介,究竟是自我建构的开始,还是自我沉沦的开始?听着乡村民谣的年轻人——他们的灵魂皈依究竟是在那些民谣所歌唱的乡村,还是一线城市的中央商务区?而城市里那些特别的文化产业创意园,它的真正归属是盘踞于中央商务区的资本,还是盘旋在乡村暮霭里的炊烟?我们无法确认!所以,阐释的链条开始断裂!
阐释的链条断裂,也就意味着文化、思想的传承断裂了。这两年我上课时越来越突出的感受是,现在的学生和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学生相比,对于过去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越来越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年轻一代立足当下,重新来过,重新描绘他们的精神文化的图谱。他们不断创造,不断丢弃,以和过去断裂来成就自己的成长。这就是所谓“后喻时代”的含义。这个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著作《文化与承诺》中提出。与“后喻时代”对应的是“前喻时代”。“前喻时代”的知识和文化在继承中前进,经验的积累与传承意味着年老者和年轻者相比拥有更多的优势和权威。年轻人要向长辈学习。而到了“后喻时代”,由于文化、技术都是断裂之后的重新来过,所以年长者所拥有的大量的过往知识、文化与经验成为无用,而需要向掌握了新的当下技术与文化的年轻人学习。
瑞士杰出的心理学家荣格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说过,外向直觉型个性适合于当今许多革新领导人物。所谓外向直觉型个性,是荣格提出的八种基本心理类型之一,其核心特征就是见异思迁、好高骛远,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又忙于解决另一个问题。这种性格显然,相当“不踏实”,在一个讲究继承的时代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在一个断裂的时代,它却意味着对新事物的极度敏感,意味着不纠结于既往事物的完善,而不断另辟蹊径。许多现代技术的发展思路正得益于断裂而非继承。比方说信息的输入,最早是拼音,后来觉得拼音慢,又有了五笔字型。拼音输入法中又发展出诸如联想输入等新的改良手段,总之,核心都是对输入代码的改良,都是一个技术路径延续下来,而且都需要输入者对学习、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可是到了后来的手写输入,思路就变了,再到语音输入,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不是原有基础上的完善,而是重新发现新的路径。
包括文化的发展,事实上,现在最具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作品,或者说文化产品,已经不是诗歌、小说、戏剧,而是大型情景网络游戏、是动漫、是时尚、是文创产品、是综艺节目和广告。自然这些文化产品中包含着过去文化的一些因素,比如今年暑假热映的动画大片《哪吒之魔童降世》,本身就取材于传统文学,但是它得到普遍欢迎的关键却不在于它再现了传统,实现了传承,而是它颠覆了传统,形成了断裂。太乙真人的仙风道骨变成了一个说着四川话的胖子,而哪吒形象之丑,一开始也是让我倒吸一口冷气,他和龙王三太子敖丙之间的故事完全颠覆原作,甚至产生了一些耽美的感觉、效果。正是与传统的断裂而非继承形成了这部影片的卖点。甚至于本世纪初的人们如果在当时就穿越到现在,恐怕也无法理解现在的综艺节目、真人秀之类到底有什么好看,那時候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娱乐节目还是以歌舞曲艺的表演为主,那时如何能想象这个既不唱也不跳,不知有什么值得看的真人秀如今竟是这样火爆。总之,类似的断裂式的变革真是不胜枚举。这种断裂不仅标明了现在和过去的关系,同时也意味着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它意味着未来人类生活、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预测的。因为我们不再沿着线性的逻辑的阐释的链条前进了。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变得越来越不可定义。
社会、文化的变革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和断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来反观我们的中小学,包括大学的文学教育,真是恍如隔世。现在的文学教育和学生们真实的文学、文化世界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疏离。这种距离和疏离,越到高年级越明显。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过去文言文的教育所形成的文化世界和世俗文学、白话文学、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另一个文化世界之间的脱节。学生们和文学、语文课堂教给他们的课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这是我作为一个教师这么多年来上课感觉到的变化。这种日益的疏离和教师的授课艺术无关。最根本的疏离我觉得就在于文学教育一直以来所遵循的那种阐释的链条,那种寻找归属和归宿的核心理念,和当下的文化、生活世界的精神是脱节的。比如说吧,过去,一句很精彩的话,一句名人名言一定是让我们觉得深刻而有教育意义的,我们会解释它、引用它。而现在一句很精彩的话却一定是能让我们去改写、变形的,而且可以随时插入我们的日常表达,形成趣味,比如“蓝瘦香菇”。你可不能说这四个字的前世就是“难受想哭”,不然,为什么“难受想哭”没火而“蓝瘦香菇”却火了呢?但是你让我们的老师不去教“难受想哭”,而去教“蓝瘦香菇”,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可不是一点两点啊!
在这样一个后喻时代,这样一个后真相时代,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我们作为教师曾经拥有的优势已然不再是优势,我们作为教师的合法性正在弱化。文学、语文教师的角色或许需要重大的变革。在这里,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带来更多的有关当下文学、语文教育的命运及其发展路径的思考。
金立群,文学评论家,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