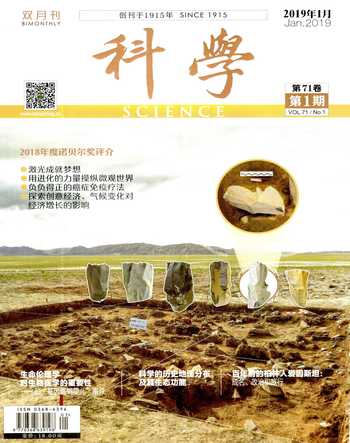《科学》的科学救国思想传播及其特色
陶贤都 张贺维
1915年创办的《科学》是中国近代发行B寸间最长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救国思想贯穿干其传播过程。《科学》的科学救国思想传播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展开,分别对应着科字知识与科学观念的传播,科学救国主张与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传播科学》的科学救国思想呈现出整体性、包容性、渐进性等特征。
1915年,“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科学期刊《科学》在上海问世,开创了科学传播的新时代。《科学》杂志是中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办到1950年停刊,到1957年复刊后又停刊,再至1985年复刊一直出版至今。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这个主题下,中国人从多个维度寻觅着“救国”方略,“科学救国”即其中重要方略之一。《科学》作为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媒介,“科学救国”理念贯穿于科学传播之中。“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及其《科学》杂志的刊行,是科学救国思潮形成的标志。”[1]探讨《科学》期刊中的“科学救国”思想传播,能够从一侧面呈现“科学救国”思潮的脉络,认识《科学》期刊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科学》的创立及科学救国思想传播的概况
《科学》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914年6月开始筹备和编辑,1915年1月在上海出版。《科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与其背后的科学组织——中国科学社密不可分。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团体,最初是为了编辑、发行《科学》而组成,后成为《科学》发展的坚强后盾。《科学》是中国科学社的机关刊物,是贯彻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意图,进行科学传播的媒介。
“科学救国的思潮发端于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设计思想之一。”[2]但是“科学救国”的思潮高涨时期,则是在民国初年。所谓“科学救国”,就是主张通过提倡、研究、发展科学和技术达到救国的目的,它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所表现出的理性觉醒,是近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
“科学救国”思想贯穿于《科学》杂志近代的发展过程。1915年1月,《科学》月刊第1期出版发行,任鸿隽、杨锉、胡明复等科学社成员纷纷著文立说,大力传播科学知识及科学救国思想,在国内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主要创办者之一的任鸿隽在《科学》第1卷《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这完全是一份科学救国的宣言。中国科学社成立后,以五位董事名义刊登在《科学》第2卷第8期的《本社致留美同学书》,再一次发出了“科学救国”的呐喊:“科学为近世文化之特彩,西方富强之泉源,事实俱在,无特缕陈。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莫由。”
《科学》杂志在近代发展的过程中,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队伍,为《科学》的出版和发行奠定了基础。在人数众多的作者队伍中,核心作者群体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发起创办《科学》杂志并成立中国科学社的理事和会员们,如任鸿隽、杨铨、竺可祯、秉志、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他们不仅仅谋求《科学》杂志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而且直接为《科学》撰写文章。
《科学》传播了大量的科学知识,为促进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林文照这样评价《科学》的传播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及其他学科,有许多重大发现,在技术科学上也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基本上都是在《科学》月刊上作了详略不等的介绍和评述,诸如伦琴射线、镭的放射性、原子结构学说、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电子管、无线电技术等等。”[3]
《科学》中科学救国思想传播的三层面
“科学救国思想是一个富于理性、匠心独运、思路清晰,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其中,科学本体论、科学精神论、科学价值论和科学应用论构成了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4]从传播的角度,科学救国思想应是以救国为目的的一种主张的传播。《科学》的科学救国思想呈现出来一个完整的,以科学为核心手段的救国方略、以传播对象划分,《科学》中的科学救国思想传播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展开。
个人层面:科学知识、科学观念的传播
科学救国思想的传播必须先以读者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科学观念的培养为前提。《科学》倡导科学救国的首要任务是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科学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知识,如在创刊号上刊登的胡明复的《万有引力定律》、杨孝述的《歐姆定律》,任鸿隽发表于第5卷第11期的《爱因斯坦之重力学说》;科学知识方面,涉及生理卫生、口常保健、天文地理,如竺可祯发表于第3卷第9期的《论早婚及婚属嫁之害》,唐钺的《雷电说》和《食荤与食素之厉害沦》等。
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还要使读者拥有正确的科学观念,全面认识科学的本质在《科学》创刊号的第二篇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中,就提到:“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任鸿隽在1916年《科学》第2卷第!期发表的《科学精神论》一文,对科学及科学精神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有助于旧人更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内涵:“利一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真理者,绝对名词也……真理之为何物,无不在也‘科学家之所以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念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任鸿隽认为,中国不仅缺少科学,更缺少科学精神,中国若想发展科学,必须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社会层面:科学救国主张与科学文化的传播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全社会都在寻求富强复兴的途径,器物救国、制度救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利学》倡导科学救国,必须要拿出充分的论据说明科学对于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的促进作用,从而使读者相信科学发展之于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使崇尚科学,坚持科学救国主张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
《科学》刊登的关于科学救国主张的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人手来说服读者。一方面从发展利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严重压抑和摧残中国科学事业的社会政治桎梏进行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就是竭力宣传科学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希望用世界近代和现代科学的理性之光,为黑暗中的中国社会找到一条走向强盛的光明之路、例如,秉志1932年著《科学与国力》,指出只有科学可以使国家的局面转危为安:“然窃以为有一术,可以转危为安,要视国人之努力何如,此术为何?曰科学是也。”他认为我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科学不发达。想要国家强大应当从五个方面发展,即国防、民力、政事、实业、生活,而这五个方面的发展皆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吾国今日之困难,指不胜屈,然无论其为何种困难,未有不可由科学解决之者,盖科学者,解决困难之利器也,现在科学虽未臻于万能,然其发达,故日进不已,久而久之,终有至于万能之一日。今日世界人类之幸福,何者非由科学所致,吾国之弱不足尤,倘能使科学发达,则转弱有方也,吾国之贫不足虑,倘能使科学发达,则疗贫有术也,吾国一切困难,尽可诉诸科学,以图解决,目前虽危急万分,欲得救济之法,亦惟求诸科学而已。”[5]
国家层面:发展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
发展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是科学救国思想在国家层面的方法论,是一整套有步骤的具体方略。要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造就一大批科学家。《科学》从创刊至15卷,仅关于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论文就有104篇,其中专门论及算学、生物、化学、地理等自然科学教育、教育方法以及实验教学、师资培训的论文就有62篇之多。从科学教育层次来看,涉及博十教育1篇,大学教育7篇,中等教育3篇,小学教育4篇,以及留学教育5篇和职业教育8篇《科学》还设立了“科学教育”专栏,并出版“科学教育”专号。[6]
另外,科学研究是推进科学救国的重要举措。1918年秋,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回国,任鸿隽在《科学》上连续发表《发明与研究》《科学研究之又一法》等文章,呼吁科学研究。杨铨也撰文呼吁科学研究是发展中国科学的唯一正途,1920年他连续在《科学》上发表《科学与研究》《战后之科学研究》等文章。
《科学》科学救国思想传播的特色
《科学》杂志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学救国思想体系,是中国近代科学救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凸显出了自身的特色。
传播内容的整体性
《科学》传播的科学知识涵盖了整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是从整体上介绍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杂志。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纯粹科学与实用科学关系的讨论贯穿始终。很多学者是基于對中国近代一直滞后的深入探讨基础上,提出应该重视纯粹科学研究,以推动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最终实现科学救国的目的。然而在这一时期,提倡应用科学是科学救国思潮的主流,很多科学家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在抗战的危急时刻应用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应用科学的紧迫性。任鸿隽认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是科学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因此《科学》既重视应用科学的传播,也同样重视纯粹科学的发展。据统计,《科学》截至1950年前的32卷共刊发论文2795篇,其中技术类的文章占总数的22.61,共计632篇。相关介绍门类相当齐全,涉及冶金、化工、机械制造、土木工程、水利、农林等。《科学》同样重视纯粹科学。在理论学说方面,《科学》介绍的内容几乎涉及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全部基础学科领域和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如细胞学、微生物学、热力学等。
传播主张的包容性
《科学》大力宣传科学救国主张,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大力抨击阻碍科学发展的消极力量。在科学救国思潮发展过程中,更是有相当一部分团体矫枉过正,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思想。然而《科学》在这一方面却相当理性,体现了传播主张上的包容性特征。
这种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对待西方近代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爆发的“科玄论战”即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唯科学主义的质疑。《科学》虽也参与了“科玄论战”,但并没有体现出唯科学的思想。任鸿隽认为“科学有他的界限,凡笼统混沌的思想,或未经分析的事实,都非科学所能支配。但是科学的职务,就在要分析及弄清楚这些思想事实上。”与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不同,《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其缺乏科学理性的批判,主张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和求实精神。
其次,《科学》传播主张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对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作为一份以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为己任的杂志,《科学》并没有忽略社会科学的作用,“文学与科学之于教育,乃并行而不可偏废”,认为抹杀社会科学的教育价值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必须同等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教育价值。
传播策略的渐进性
从《科学》呈现的科学救国思想体系来看,其对科学救国思想的传播体现了传播策略上的渐进性特征,即由浅人深,由外及里,渐进发展。《科学》的初创阶段以科学宣传为主,通过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传播,向国人全面介绍西方的近代科学,破除封建愚昧思想,倡导科学理性精神。而后,科学教育宣传的比重逐渐加大,内容涵盖科学教育的功能和重要性以及科学教育体系建立的实际方法,从1920年代开始,《科学》开始重视科学研究,不仅发表了多篇强调科学研究重要性的文章,还亲自实践建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由科学宣传到科学教育再到科学研究,这一步骤符合了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结语
《科学》完整的内容结构,包容并蓄的宣传主张以及大胆创新的办刊风格,大大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普及,深化了国人对科学观念尤其是科学精神的认识,以及发展科学对于推动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使科学救国思想成为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科学》传播科学救国的主张,使国人认识到科学发展对国家商业、实业、军事等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更加重视科学,激励青年献身科学事业,孕育了一批科学精英, 投身救国事业的精神支柱,引导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1]朱华.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7-68.
[2]蒋道平,徐飞.“科学救国”的先驱探索及当代启示.科学学研究,2014(10):1441.
[3]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3):223.
[4]南宁波.论科学救囚理论的体系结构及其价值.学术交流,2004(7):19-24.
[5]秉志.科学与国力.科学,1932(7):1012-1020.
[6]李晓霞,姚远.《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理念的引入.西北大学学报,2011(2):175-180.
关键词:《科学》杂志 中国科学社 科学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