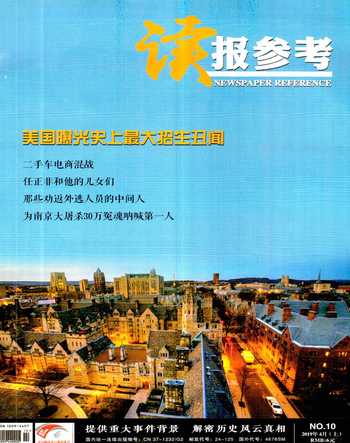雨花台大战:曾国藩一生最焦灼的46天
《曾国藩传》(张宏杰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一书,详细记述了曾国藩是如何成为清王朝的最后领航者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本刊特摘编部分章节,以飨渎者。
孤军深入的曾国荃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太平天国首都金陵(今南京)。这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
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他让曾国荃围城,让多隆阿、鲍超、李继宜等其他人打援。
曾国荃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后,先回乡招募士兵扩大部队,然后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率吉字营循大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斩将夺关,先后攻陷含山、秣陵关、大胜关等地,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扎下营盘。
然而,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不如曾国荃快,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没有一路跟得上来,一时间形成了曾国荃孤军深入之势。
曾国藩大惊。他早就多次命令曾国荃先停一停,等等其他几支援军。但曾国荃全然不管。
在湘军将领中,曾国藩最难指挥的就是这个亲弟弟。兄弟俩的性格大不相同。曾国藩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便已看到结尾。曾国荃只是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去过北京,没出过远门,没办过大事,年轻,见识窄。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较多: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
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完全得益于哥哥的指授安排。然而,弟弟对哥哥却不是很佩服,认为哥哥做事过于迟缓迂拙,因此根本不把曾国藩的命令当回事。
他违抗军令一路猛攻,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营盘挖好壕沟、修好长墙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领略一下江南名城的风采,同时估计一下挖多长的沟才能围起来。
这一走才发现大事不好。
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当初明太祖修这座城池,前后花了21年。它周长96里,城墙基础宽14米,最宽处达30米,高14至21米。基础用巨大的条石砌起,墙体用巨砖筑成,规模极其宏大。
曾国荃几个人走了一整天,也没能周览金陵城墙全貌。这下曾国荃傻了眼,他的吉字营不过两万人,撒在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大锅里,根本看不到影。他这才明白哥哥所说“金陵城大贼众,合围不易”的意味,后悔不该轻率进兵。
但事已至此,倔强自负的曾国荃也不肯轻易退兵,轻进轻退,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硬着头皮先挺下去,等其他几路湘军到来。
最焦灼的46天
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令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惊心。正在上海作战的忠王李秀成奉命回援,率军十余万,迅速抵达,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了猛攻。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事后统计,两万湘军中,约一万人得了传染病。
至此,雨花台之战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占绝对优势,且从上海获得大量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很多。湘军武器落后,而且疾病减员严重。
太平军援军联营数百里,以西洋开花炮昼息夜攻。曾国荃留下患病的湘军守帐篷,能战者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此时,曾国荃终于认错了:不该孤军深入!他请求哥哥急调救兵:“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
其实,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然而,各路均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最后,曾国藩居然把自己的亲兵护卫400人派了过来,但这点儿人只能起到壮胆作用。
雨花台大战共持续46天,是曾国荃一生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46天。曾国荃在金陵日日焦灼,曾国藩在后方的焦苦一点也不比曾国荃少。
从大势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消耗60吨米,然而,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控制。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李部至少十万人,每天需吃上千石的米。如无船队运输,怎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时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有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三万石也极其困难。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米可以运出。因此,李秀成挺不了太久。
从此信可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
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没有把握。曾家已死了一个曾国华,他深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
曾国藩并不怕死,自帶兵以来,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但他承受不起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荃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
恩将仇报的沈葆桢
哪知就在此时,军饷供应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四万两军饷。少了采购经费,曾国荃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
这大出曾国藩的意料。
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曾入过曾国藩幕府,后任广信知府。因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欣赏。
按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沈应该感激涕零并大力回报,不想却在此时作出断饷之举。
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个原因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同。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目的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
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中最头疼的问题。他对江西的供饷能力寄予极大希望,希望沈葆桢能源源不断地供给湘军军饷。
但沈葆桢不这样想。沈极有主见,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功业。
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不想把命运交由别人掌握,因此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军队。供养军队需大量金钱,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因此,沈葆桢决定每月截留四万两军饷,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截留四万两军饷本已出格,更出格的是,沈葆桢事前未与曾国藩商量。他知道,独立建军违反了曾国藩的指示,因此干脆不商而行。
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報。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是两个字——恩与义。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也从没有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在日记中记道:
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三更睡,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终于顶过来了
这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白天,他频繁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他在后院的小房间里,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上了床又常常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地痛。
内心愤怒纠缠,但曾国藩的外在反应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因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过一段话,大意为:这些天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愤懑。但是我细思古人办事,岂不也是与我一样,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来磨砺自己的心性。
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曾国藩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他有意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在给明友的信中,也经常请求他们“常惠箴言,并赐危论”。
经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非常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的,现在又进行参奏,不仅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也是为公,所争毕竟不过四万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
曾国藩念起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寅谊”。他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
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主要是因为太平军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远没有英王陈玉成部凶悍耐战。
此次战役双方相持到10月4日,天气已寒,太平军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好撤退。
曾国荃终于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46天。
但是,湘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湘军“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曾国藩之助手郭嵩焘亦认为此“极古今之恶战”,特别是随曾国荃作战的曾国葆,战后不久就因操劳患病而死,令曾国藩又失掉了一个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