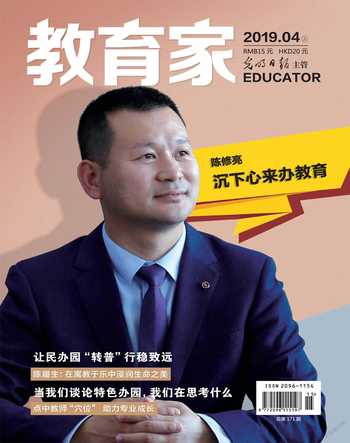陈履生:在寓教于乐中浸润生命之美
王妍妍
儒雅、健谈、严谨,陈履生给人的初次印象一如老派的传统文人。无论是绘画、摄影,抑或油灯收藏,他总能在时空转换中游刃有余,仿佛自带天然的统筹能力。如此活法,倒也生出许多浪漫。
2016年8月,陈履生正式从国家博物馆退休,但他没有“退而休,退而止”。对于博物馆,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感情,走访、参观过全世界300多家博物馆;他将自己收藏的4000余件油灯精品拿出来建立油灯博物馆;他希望博物馆的教育能融入家族的家教家风,代代相传。
“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虽然感觉很累,可是能够回首,也是一种幸福。”于陈履生而言,未来依旧任重而道远。
把握美育内涵 塑造美好心灵
《教育家》:在新时代,美育被赋予了怎样的新内涵?
陈履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美育在学校,可通过音乐、图画、游戏来实现,在社会,则通过博物馆、美术馆、剧院、公园来实现。”作为一种教育,其方式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文化传承,家庭文化影响,都是推动美育的重要组成。美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美的感知和认识,美的发现与创作,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从社会到个人,从言行举止到美化自身,其雅和俗、美与丑是最为主要的审美范畴。社会的价值判断会影响美育,因此,用教育的方式来提升审美应该是发展中的常态。而对于个人来说,美育就是为了人的美好心灵与美好生活品质的修饰。
《教育家》: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大力加强和改进美育教学工作,再一次成为热议话题。在您看来,目前的美育处在哪种发展阶段?如何将美育渗透到其他课程,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陈履生:美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属于短板,基础美育教育存在缺失和偏差。在具体的美育工作中,以技代艺、重应试轻素养等现象依旧存在;在社会上,以博物馆的教育为例,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博物馆只是一个象征,并没有成为教育的刚需。许多学生并不习惯逛博物馆,甚至有不少年轻人在北京读了4年大学,却未曾进过博物馆……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深圳拥有近2000万人口,但博物馆与美术馆的访客一年却不及百万。然而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个城市人口20余万的城市,国家博物馆一年的参观人数却以百万计。
教育部政策的出台,不仅成为高等学校美育的工作重点,也激发了全社会对美育的重视。不论是校园里的美育课、家庭中的亲子绘画,还是博物馆、美术馆里孩子们的身影,都反映了“以美育人”的深入人心。学校应该把艺术教育当成重要的教育手段,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和文化气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文化修养,助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博物馆式教育 尚需形成文化依赖
《教育家》:当下应该如何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美育功能?您又如何看待“博物馆式教育”?
陈履生:博物馆作为文物、艺术品的“家”,是供人们瞻仰和欣赏的殿堂,是使文物艺术品有“尊严”的储存空间和展示空间。区别于街边古董店,它们不是商品,而是发挥着教育、研究意义的负有文化传承责任的阵地。博物馆里的典藏都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及其背后的入藏故事,博物馆的出现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首先,当下博物馆的美育功能与其专业性和自身定位相关,应当通过知识性的传递以及美的形式、美的方法等来展现博物馆的价值观。在博物馆,具有独特的藏品、宏伟的建筑、多功能的设施,它应该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第二课堂。
如今,为了孩子,也是从娃娃抓起,很多博物馆、美术馆紧跟时代的脚步,运用与时代相符的手段来吸引孩子们的进入,满足孩子们多样化的需求,以培养他们自觉的博物馆意识和依赖感,多去博物馆参观学习。
其次,博物馆在一个城市中应該保持自己独特的地位,它不仅应成为孩子的第二课堂,还应形成持之久远的、让几代人相关联的一种文化依赖。显然,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和自己去看博物馆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作为父母、老师的教育职能。孩子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与书本知识相关联的实物,通过对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欣赏,感受到教科书里曾经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历史和艺术的问题,引发他们的憧憬和想象。在博物馆中,我们既可以获得很多历史、艺术方面的知识,还可以获得人文环境的享受。博物馆的综合文化属性决定其本身的建筑、展陈,包括餐饮、纪念品等都不同于外部。这种早期教育可能会伴随着孩子终身的成长。
“博物馆式教育”要求管理者应以更主动的姿态努力办好博物馆、美术馆,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孩子们的审美能力,让真正的文化之美浸润自己的生命。以阿姆斯特丹美术馆为例,他们把国际品牌乐嘉玩具引进到美术馆,建立了乐嘉玩具屋;还有“与恐龙睡一晚”等活动,通过特别的方式吸引孩子进入美术馆和博物馆之中。博物馆、美术馆中的游乐有其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这些都关联到博物馆、美术馆的专业内容,表现出其专业特色。“寓教于乐”,可能正是美术馆、博物馆需要面对的。
总之,博物馆中的每一件藏品都是历史的见证,它所折射出的内涵,告诉孩子们的知识是真实而客观的。因此,参观博物馆不能匆匆走过,需要有意识地观光或者学习,需要用自己的步履慢慢丈量美学的长度。
《教育家》:您参观、考察过全世界300多家博物馆,在公共教育方面,国外的博物馆与国内相比有哪些特点?
陈履生:中国的博物馆起步较晚,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博物馆有两三百年历史,博物馆及藏品的数量、品类、规模都远远超过我们。因此,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在西方是一种常态化教育,孩子走进博物馆接受教育比较普遍。
第一,西方的博物馆有各自的特色和发展路径,反观我们的省市级博物馆在公共教育方面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个性。第二,西方的博物馆注重社会的教育功能,而我们的博物馆教育功能薄弱,并且由于教育资源的差异,博物馆教育在一些中小城市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这也反映了中国博物馆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特点。第三,西方国家博物馆在城市中的文化影响力巨大,而我们尚未建立起与社会和公众乃至学生之间的紧密联系,难以成为公众文化消费的依赖。
建立“四观” 立德最重要
《教育家》:无论中外,都较早地认识到了美育的重要性,并且为此付诸实践。比如课外、校外艺术教育都是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点看,国内外关于美育的侧重点似乎并不一致?
陈履生:从基础教育的层面来看,国内比较注重知识性和技法性的培养,国外则更多展现的是审美能力方面的培养,他们着重培养孩子们的博物馆意识,从小接受其熏陶,陶冶性情,从而形成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在国外的博物馆中常常能看到孩子们在展品前上课。不过,国内的博物馆也在发生着这样的变化。到博物馆来的中小学生不断增加,尤其是北京在制度上确定了中小学生每年进入博物馆的次数,说明了博物馆已经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但我们对待博物馆的教育方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不是来看画,而是来画画,没有把博物馆和教育结合起来,启发孩子思索与展品相关联的一些其他问题。在这方面,国外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方式却更加多元化。比如在英国,博物馆被视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参观博物馆历来是英国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我希望国内的一些中小学能与博物馆合作开展更多系列课程,让更多的孩子受益于博物馆的教育。
《教育家》:您曾说,在当代中国,从教育入手不仅是蔡元培时代提倡的美育,更重要的是在新时代以美育带动建立一个“四观”正确的主流价值观,从而为塑造健全的美的心灵而完善当代中国人的品质。那么,如何建立“四观”正确的主流价值观?
陈履生:与人相连的“四观”都是德的表现,立德最为重要。“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一直都是社会中的问题,而美育的根本就是在德的基础上“饰其性”。如果违背特点和规律,变成说教和形式,那么,就不可能达到美育的目的,就可能蜕变为“修其容”。
无疑,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是具体的,需要从基础教育做起,从小抓起,需要用多种方法,包括古已有之的《女史箴图》那样的图像观想法。当今只有充分发挥美育的社会作用,完善审美观,才有可能根治那些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出现严重问题的疑难杂症,才能使受到严重破坏的“四观”不正的社会生态得到恢复,让风清气正遍布神州大地,让我们的国家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