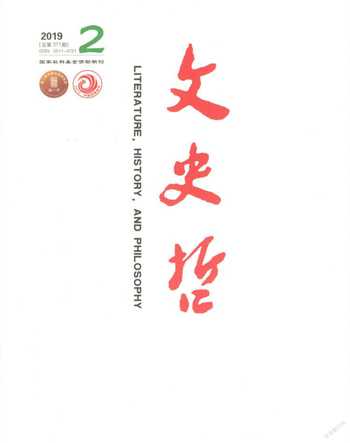生成还是指导:老子论“无”的新探究


摘 要:对老子“无”观念的研究,除了生成论的角度,更应从价值问题入手。因为老子更多谈论的不是等同于“道”本身的作为宇宙万“有”之根源的生成之“无”,而是关联于“道”之“德”的指导性的“无”。这样的“无”,是对“道”之“德”的非掌控特征的总概括(即从动词性的“上德不德”或“玄德”之“不有”“不恃”“不宰”,走到名词性的“无名”“无欲”“无为”“无以为”,最后概括为“无”)。而所谓“无”的指导性,正是针对政权如何“长久”的问题来说。
关键词:道;德;有;无;老子
认为《老子》书的“无”不只是日常的“有无”之“无”,更涉及作为万物抽象根源的生成论的“无”,是古今解老者的通见。作此解释的依据,固然可以举出许多,但首先是传世本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这句话,在注释或关涉《老子》的早期文本中已被视为支持抽象解释的关键证据,因此会用“无形”“无名”“无声”“无味”等词汇来刻画众“有”所出之“无”的抽象性[ 关于“无”之抽象性的刻画,详见《老子河上公章句·德经·去用》、《老子指归》卷二、卷三、《黄帝四经·经法·道法》、《淮南子·原道训》。此外,要充分理解“无”的抽象意谓,还要考虑字源问题,尤其是“无”与“亡”“無”的关系,参见庞朴:“说‘无’”,收于《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270-284页;王中江:“有无之辨”,收于《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3-108页。]。而这个“无”,同样在传统解释中,是被当做“道”的同义语,即作为万物根源的“道”,也能在“无名”(《老子》第一、三十七、四十一章)“不可名”(《老子》第十四章)或“不知其名”(《老子》第二十五章)的意义上被说成一个实体性的“无”[ 如《尹文子·大道上》所谓“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就是将“有生于无”的“无”视为“不称”者,并将这“不称”者说成是“道”。因此,“道”就在“不称”或“无名”的意义上被看做一种“无”。这种思路,在王弼对《老子》首章的解释中最突出,所谓“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老子道德经注·第一章》),正是以“无名”为中介,将作为“万物之始”的“道”等同于“有生于无”的“无”。当然,如果采用司马光、王安石对今本首章的断句,可更直接地断定“道”是“无”。当然在先秦,“道”通常也被直接说成是“无”,如《管子·心术上》之“虚无无形之谓道”,《列子·天瑞》“《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道终乎本无始,进乎本不久。有生则复于不生,有形则复于无形”。只是在《老子》中,并没有直接断言“道”是“无”的语句。肯定这一点,主要是基于“道”作为超言绝相之存在的推论,因此解释者经常提及的就是老子关于“无名”“不可名”的论述。]。并且,因为“道”是老子明确论述的生成根源(参见《老子》第四十二章),则越能肯定“道”是“无”,就越能说明“有”为何会“生于无”。可见,传统关于“无”的抽象解释,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基本能说是以“道”即“无”为前提,以“有生于无”为依据的解释。
在现代老子研究中,由于出土文献的引入,传统的抽象解释的确面临一些疑问。但总的说来,这种解释非但没有削弱[ 比如,比对出土和传世文献,可知道经首章更应以“无名”“有名”“常无欲”“常有欲”断句,这至少从字面上消除了能被解释为抽象根源的“无”;再有,《老子》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在郭店简中写作“天下之物生于又(有),生于亡(无)”,并列式的表达似乎也弱化了“无”的根源意谓。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要紧。因为即便首章没有单独讲“无”,但所谓“无名”,就其意指没有名称或不可命名之物来说,与“无”的抽象意谓毫无差别;至于四十章,虽然在竹简中作“生于有,生于无”,李若晖及相关论者认为这仍应按“有生于无”理解(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2页;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0-521页)],反而还被强化。这大概正因为现代老子学首先是纳入哲学史学科的研究,而哲学通常就被看做探索抽象事物的学问,所以要揭示老子思想的哲学内涵,就必须关注文本中的抽象表达(如“大”“一”等)。这其中,最具抽象性的莫过于“无”,当然也就是最有哲学意味的概念[ 参见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2-73页;任继愈:《老子绎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4页);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7页;刘笑敢,《老子古今》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22-423页。]。但即便如此,抽象解释仍有需要反思的空间。尤其是,它可能会引导读者在理解老子“无”观念时过于偏重生成问题,却忽略了本来更为重要的价值问题。这就是本文意欲证成的,老子真正关注的与其说是作为万物根源的生成之“无”,不如说是关于政权如何“长久”的指导之“无”。因此,除了抽象解释,提出某种非抽象的,或说是唯名论性质的解释,对于理解老子的“无”观念,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当然,这并非要否定传统观点的合理性,而是要揭示老子论“无”的更多面向。
一、“无”与“道”
如前述,认为“道”本身就是一种“无”,这只能就“道”作为超言绝相的事物来说。问题是,老子说的“无名”“不可名”或“吾不知其名”,果真就是对“道”的超言绝相的描述吗?如果是,则“无名”等表述中的“名”必须是名称,这才能在“道”无名称、不可命名的意义上,将之等同于抽象的“无”。但此前提是否牢固,要看对“名”本身的理解。就先秦典籍来说,名称之“名”只是一种,此外还有名位、名分、功名、名号、名声之“名”[ 如《左传·庄十八年》之“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商君书·定分》之“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韩非子·八经》之“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荀子·议兵》之“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强国》之“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这其中,“名位”之“名”又是根本,其他则是有“名位”者所具有的“名号”“名声”与“功名”。],前者可说是指称对象的“名”,后一类则都是指导言行的“名”,代表着特定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纵观先秦名思想的发展,相对于指称性的“名”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引起重视,指导性的“名”始终都是被关注的焦点[ 类似地,曹峰则区分了两种“名家”,一是“政论型名家”,一是“知识型名家”,并认为前者更重要。参见氏著:“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如荀子,他将正名的目的界定为“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荀子·正名》),这“上”“下”之分作为一种价值分判,就是以指导性(“明贵贱”)的“名”比指称性(“别同异”)的“名”更重要。回溯到孔子,正名幾乎只是针对指导性的“名”来说,即需要校正的,不主要是名称对事物的指称,而是名位、名分等对言行的指导,这才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的推论。而此类指导性的“名”,在《老子》书中也常出现,如所谓“功成不名有”(第三十四章)、“名与身孰亲”(第四十四章)、“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等,正是就具有指导功能的名位、功名来说。因此对老子所谓“无名”“不可名”与“不知其名”的解释,除了能从指称性的“名”出发,也可试从指导性的“名”来考虑。
先说“无名”,仅就这个表达在《老子》书中的特定呈现看,就不只是“没有名称”这么简单。如所谓:
无名天地之始,……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眇/小)。[ 今本首章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帛书与北大简俱做“眇”,整理者多读为“妙” ,实应如本字看。“眇”义为“小”,如《庄子·德充符》之“眇乎小哉”,《荀子·王制篇》之“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则“常无欲,以观其眇”即“常无欲,可名于小”之义。当然,如仍作“妙”读,亦可训为“小”,参见陈梦家:《老子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5页。](《老子》第一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老子》第三十二章)
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老子》第三十七章)
“无名”总与“无欲”和“小”关联出现,其涵义必有和此二者相关之处。所谓“无欲”,对“道”来说,不是没有任何欲求,而是没有掌控万物的欲求;所谓“小”,则是对“无欲”的进一步界定,如所谓: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老子》第三十四章)
这就是把“道”没有掌控万物的欲望,界定为以小角色自居的姿态。是故,在涵义上与“无欲”或“小”相关的“无名”,与其说是没有名称(指称之“名”),毋宁说是“功成不名有”,即没有或不要主宰万物的名位与功名(指导之“名”),也就是低调谦卑、默默无名。正如太史公父子所谓:
道家无为,……光耀天下,复反(返)无名。(《史记·太史公自序》)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都是在“默默无名”的意思上讲“无名”。不过,老子的“无名”主要是形容“道”的“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这既是动机上的“无欲”掌控,也是姿态上的自名于“小”。
由此再看“不可名”,见诸《老子》第十四章的这个表达,恐怕仍然不是对名称之“名”来说。因为正如前述,“道”不可命名,只能在超言绝相的抽象意义上讲。但正如《老子》第十四章所谓: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这恰恰是以“道”之抽象仍然可“名”。相反“不可名”的,不是其抽象,而是“道”所表现既无上限(“其上不徼”)、亦无下限(“其下不昧”)、绵延不绝(“繩繩”)的功德作用。这意味着,“夷”“希”“微”之“名”以及“不可名”之“名”,不是名称(指称之“名”),而是名号(指导之“名”)。名号就其可被称谓来说,有与名称相似之处。但本质差别在于,名号不主要作指称之用,而是评价之用,如《逸周书·谥法解》所谓:“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因此,名号之“名”还是指导性的“名”,即与某种名位或功名相匹配的,并且是有约定表达的名声。故上引十四章实际是说:“道”的精微玄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仍然可用“夷”“希”“微”的名号称颂;但其彻上彻下、绵延不绝的功德,没有名号可以匹配,这才是“不可名”的意思。
此外,如果将“不可名”视为“无名”的同义语,可知老子所谓“无名”,除了是无名位、无功名,也有无名号之义。如今本《老子》第四十一章的“道隐无名”,应如帛书作“道褒无名”,就是以“道”的功德盛大(“褒”),没有名号可以称颂。这也是先秦典籍中的常见用法,如所谓“民无能名曰神”(《谥法解》)、“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循此,可知《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吾不知其名”,并非不知道命名“道”的名称,而是不知道称颂其功德的名号,所以勉强用“大”表示:
有物(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与“夷”“希”“微”一样,仍是名号。至于“道”的名称,即指称这个对象的语词,实际就是“道亦其字”的“字”。正因为“道”这个“字”仅是标记或指称“有状混成”者的符号,却没有“功之表”的作用,这才要“名曰大”。但所以是“强为之名”,因为“道”的功德实“不可名”,因此即便称“大”,也依旧“无名”。这再次映证了“无名”的两层意思,一是就名位、功名来说,“道”以其“小”(姿态谦卑)而“无名”(不要主宰万物的名位、功名);一是就名号、名声来说,“道”以其“大”(功德盛大)而“无名”(没有名号可以称颂)。
但不管怎么说,按以上解读的老子所谓“无名”“不可名”与“吾不知其名”,并不是对“道”的超言绝相的描述。当然,老子的确是将“道”看做一种抽象事物,但此抽象事物是否已被抽象成作为“无”的存在,是大可怀疑的。如前述,“道”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却仍然能够“名曰夷”“名曰希”“名曰微”——这足以说明,作为抽象者的“道”,在老子眼中还没有抽象成一个实体性的“无”。事实上,观察《老子》书单独言“无”的例子,如“有无相生”的“无”(第二章)、“当其无,有室之用”(第十一章)的“无”,都是特征或属性之“无”,并没有实体义。并且,也不能因为老子将“无”用作名词[ 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上,第423页。],就认为它能表示实体。因为一个语词的词性是语法规则决定的,其指称则是语义规则决定的,两种规则并不等同,所以“无”是不是名词,并不能说明它指什么。这时,要验证老子究竟有没有论及实体性的“无”,关键要看他所谓“道”——作为最可能被等同于“无”的实体——究竟能不能被说成一种“无”。此前所述,就是说明把“道”视为超言绝相的“无”,文本依据并不充分。
二、“无”与“德”
不过,《老子》第十四章“绳绳不可名”之后,明确以“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来形容“道”,难道还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无”吗?其实,以“无物”“无状”“恍惚”等描述非确定性的语词为据,也无法论证“道”本身就是“无”。非但不能,反倒有利于說明“道”不等于“无”,即所谓“无”并非实体,而是属性,是作为“道”之特征的“德”。因为单就表达看,“无物之象”“无状之状”,以及《老子》第四十一章的“大象无形”,被说成“无X”的东西仍然是一种“状”或“象”,而不是“无”。因此所谓“无物”“无状”“无形”,明显是事物属性或特征上的“无”。“道”有这种“无”的特征,并不意味其本身就是实体性的“无”。当然,老子也将“道”说成“恍惚”之物。类似的描述,还有《老子》第二十一章所谓: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据此,还不能说明“道”是一种“无”吗?或许可以,但这样看,又该如何解释老子所谓“道之为物”的“物”和前引《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状混成”的“状”?这个“物”或“状”,也即十四章“无物之象”“无状之状”的“象”和“状”[ 参见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2·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8页。],毕竟不等于“无物”“无状”。所以,即便将“恍惚”等描述词视为“无”的同义语,也不应用来指谓“道”本身,而应指谓其属性,即“道之为物”在样态上的“无定”。但此样态“无定”所反映的,也不主要是“道”的抽象性,而是对万物的包容“无限”。正如上引文所示,“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描述的,就是“道”的“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也可说是“道”作为“有状混成”的“状”、“大象无形”的“象”,包容了一切可能的“状”和“象”。
因此关于“道”的特征之“无”,除了有样态上的“无定”之“无”,更有应有包容性的“无限”之“无”。而且,也只有包容“无限”,才会有样态“无定”。正如“大象无形”,就是作为包容一切形象的“象”,不呈现特定的形状;再如“大方无隅”(《老子》第四十一章)“大制不(无)割”(《老子》第二十八章),这类“大X无Y”形式的语句,都能如此解释。因此最终的,第二十五章以“大”称“道”,就其“功之表”来说,不是一般性地称颂,就是在称颂“道”对万物的“无限”包容[ 参见李巍:《〈道德经〉中的“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这种“无限”包容,如果看做一种“无”的话,并非作为实体的“道”本身,而是作为属性的“道”之“德”。如所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孔德”即“大德”,“容”则取包容义,即“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之“容”[ 于省吾以“容庸古字通。……孔德之庸,惟道是从。言大德之用,惟道是从也。河上公以容为容受之容,与下句惟道是从,义不相贯矣”(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12页)。但参照上引《书·君陈》语,可知河上公本的解释是正确的,以“容德”归属于“道”即“惟道是从”,并非“义不相贯”。]。因此老子以“大”称“道”的实质,就是以“容德”附属于“道”。笔者亦曾指出,此一“容德”涉及三个层次,即:
“道”潜藏了万物的一切可能。
“道”总览了万物的一切生成。
“道”保全了万物的一切价值。[ 参见李巍:《〈道德经〉中的“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最后一点最为重要。且正就此点来说,“道”之“容德”表现为“无”,又应进一步解释为“无名”之“无”。因为从第三十四章说的“常无欲,可名为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来看,“道”以“小”角色自居——这种默默“无名”的姿态——表现对就是对万物在价值上的无限包容(故曰“大”)。可见,“无名”正是“道”之“德”能被说成一种“无”的重要意谓。
但要证成这一点,需要关注两个对应:一是早期中国思想中“名”与“德”的对应,另一是《老子》道经首章之“名”与德经首章之“德”的对应。先说名德相应,这是先秦名思想中比名实相应更古老也更重要的观念。名实相应是针对指称之“名”来说,名德相应则是对指导之“名”来说。如三代信仰中有“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尚书·尧典》)的说法,“位”即名位,而能否得“位”或得“名”,就取决于当事人的“德”,故《礼记·中庸》亦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名”的說法。此种“名”“德”相应的观念,在《老子》书中也能看到,尤其是道经首章的对“名”的论述与德经首章对“德”的论述,就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参见李巍:《“名”“德”相应:〈老子〉道经首章的新解读》,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页。]。这里,主要就前者所谓“无名”与后者所谓“不德”来谈。《老子》德经首章说: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谓“上德”者(即“道”)不以世俗德行为“德”,因此有真正的“德”。故所谓“不德”,就是对世俗德行的否定,即将之判为“下德”。所以如此看,大概正因为通常被肯定的道德影响力,在老子眼中却是负面的掌控力量。比如“仁”的感化,这已经是一种掌控,只是比较微弱,即推崇仁爱的人(“上仁”)只要自身践行(“为之”)而别无他求(“无以为”),就能使“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义”的掌控则变强,不再是感化,而是教化,即推崇义道的人(“上义”)不仅自身遵守(“为之”),还有推之天下即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的责任感(“有以为”);最后,“礼”的掌控最强,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已经是一种约束。但约束越强、抵触越大,这就叫“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可见,老子将“仁”“义”“礼”判为“下德”,就是在越掌控、越难治的意义上说。因此所谓“不德”,就是否定具有掌控作用的世俗之“德”。
那么,如何理解德经首章的“不德”与道经首章的“无名”的关系呢?关键要知道,“德”的影响正是以“名”为载体实现的,如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个“君子”不只是有德者,更是有位者。因而“德”的风化,正是建立在“名”(名位)的基础上;又如《左传·襄二十四年》记郑子产与范匄书言“令名,德之舆也,……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把“名”(名声)比喻为“德”之车,则所谓德治,就是“名”的传播有多远,“德”的影响有多大。但正因为这种世俗肯定的道德影响力,在老子眼中是一种负面的掌控力量,则否定世俗推崇的“德”,势必要放弃世俗尊奉的“名”,这就呈现了“不德”与“无名”的逻辑对应。由此,“道”之“德”能被视为一种“无”,就是“上德不德”(否定世俗德行)所反映的“无名”(放弃世俗名位、功名)的姿态。当然,除了“上德不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十、五十一章)也是老子对“道”之“德”的描述。如果将“玄德”之“不有”“不恃”“不宰”看做“上德不德”的具体表现,自然也能与“无名”构成对应。是故可以说,“无名”正是对“不德”或“不有”“不恃”“不宰”这些“不X”表达的名词性概括。
但除了“无名”,“无为”也是这样一种名词性概括。因为德经首章中,“上德不德”又被表述成“上德无为”,则与“不德”对应的“无名”亦可替换成“无为”。而“无名”与“无为”,就其都与“上德”相关来说,正是互为表里的一对表达,即不取世俗尊奉的名位、功名(“无名”),就是不对人民庶物有掌控的作为(“无为”)。故正如《老子》第三十二章讲“道常无名”,第三十七章则讲“道常无为”,后者帛书本又写作“道恒无名”。论者对此莫衷一是,其实没有看到,“无名”“无为”非但没有本质差别,反而在“交换使用”中呈现了含义的同构[ 主张《老子》第三十七章作“无为”或“亡为”读的论者,理由之一是今本《老子》第三十二章已言“道常无名”,已经“突出道的‘无名’特性”,则“此章不应与之完全重复”(参见古棣、周英:《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这显然默认了“无名”与“无为”不同,所以按“无为”看才能避免重复。但强调应作“无名”的论者,也同样默认二者不同,只是认为此章要讲的是“无名之道”,而非“无为无不为”(参见李水海:《帛书老子校笺译评》下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28页)。要之,以往论者将“无名”“无为”当做不同概念,正因为将“无名”理解为没有名称。但依据前述,“无名”实为无名位、无名号,以小角色自居的姿态。则以之描述“道”的特征,就是要表现“道”对万物没有任何干涉,这也就是“无为”的意思。]。而从前引司马谈所谓“道家无为,……复反(返)无名”以及《庄子·则阳》说的“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来看,也能发现“无名”与“无为”的含义同构。因此,“道”之“德”作为一种“无”,除了能说是“无名”之“无”,也应说是“无为”之“无”。不过,德经首章谈“无为”,不只是没有掌控的作为,更是没有掌控的意愿,是谓“无为而无以为”。这个“无以为”,就是老子所谓“无欲”的同义语。如前引道经首章和第三十四章所示,由“道”的“常无欲”而“观其眇”,就是看到她“可名于小”的谦卑姿态,所以“无欲”不是一般意义的清心寡欲,而是没有掌控欲。这个意义上,“道”的属性之“无”又能界定为“无欲”(或“无以为”)之“无”。
说到这里,应能对“无”概念在老子思想中如何“出场”,有些许的体会吧。基于“无”指“德”(属性)而非“道”(实体)的判断,可知“无”概念的提炼,必须从“上德不德”或“玄德”之“不有”“不恃”“不宰”出发,将这些动词性表达转化为名词性的“无名”“无欲”或“无为而无以为”。至于“无”,就是对这些名词性表达的进一步概括,即:
不X:不德、不有、不恃、不宰
无X:无名、无欲、无为而无以为
无
但是,“无”并非只是一个语法缩略词,毋宁说,它是老子对“道”之“德”的非掌控特征(“无为”“无以为”或“无名”“无欲”)给出的一个纲领性表述。
三、“无”与“有”
由上可知,作为抽象解释前提的“道”是“无”,并非直观上的那么合理。现在要说的是,支撑这种解释的重要依据,即《老子》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也不必定看做生成论的命题。因为考虑到“无”概念的提炼,很可能是从动词性的“不X”出发(进而转化为名词性的“无X”,再到“无”)。那么对“有生于无”的解释,首先就能理解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上德”之“有德”是出于其“不德”,亦即“道”成就万物的功德(“有德”),是出于不掌控万物的姿态(“不德”)。此外,因为“玄德”也是对“道”之“德”的描述,则“有德”出于“不德”,也能说是“道”使万物“生”“为”“长”的功德,是出于“不有”“不恃”“不宰”的姿态。但不管怎么说,“生”不必定解释为生成,而能看做因果上的引发、导致,如“唯逆生福,唯顺生祸”(中山王壶)之“生”。
进而,注意到“无”概念的提炼是从动词表达“不X”走到名词表达“无X”,则将“有生于无”解释为“道”的“有X”(“有德”或“生”“為”“长”)出于“不X”(“不德”或“不有”“不恃”“不宰”),又能进一步解释为“有X”出于“无X”。比如“有名”出于“无名”。以道经首章为例,这二者正可说是“常名”的特征。“常名”不同于世俗尊奉的“名”,后者是被“命与”或敕封(“可名”或“可命”[ 传世本的“名可名”,北大简作“名可命”,相关差异参见曹峰:《〈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的名位、功名[ 《左传·文十八年》“公命与之邑”、《公羊传·襄二十九年》“先君之命与”,“命与”即敕封、赐予。《老子》五十一章“莫之命”的“命”,帛书作“爵”,就是此义。]。但因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自然不能恒久不失。那么,“常名”作为恒久的名位、功名,必定区别于一切世俗生活中的“可名(命)”之“名”,是只有“道”才享有的终极的“名”。但正因为“道”有“常名”不是占有任何世俗之“名”,则以世俗标准衡量,“常名”反而是默默“无名”。可老子的观点是,断不能轻视这貌似“无名”的“小”角色(“道”),因为她才是真正的“万物之始”;并正因为居于“万物之始”,所能充当“万物之母”。由此谈及“有名”,就是把“道”有“常名”界定为具有作为“万物之母”的名位、功名。可见,“无名”“有名”正是对“常名”的两种描述,“无名”是将“常名”区别于一切世俗之“名”(即“道”有“常名”,不是具有任何世俗名位、功名,故曰“无名”),“有名”则是说这超越世俗标准的“常名”是什么(即作为万物之母亲、母体的名位、功名)。
如此看,“无名”“有名”不是先后关系,也非并列关系[ 做先后关系理解,古注已然,近人蒋锡昌则明确强调“‘无名’、‘有名’纯以宇宙演进之时期言”。参见蒋锡昌:《老子校诂》,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但老子明言“道常无名”,则“无名”并非某个阶段。刘笑敢有见于此,遂提出并列关系说,认为道经首章“无名”“有名”云云,“讲的是道的‘无名’、‘有名’两个并列方面,即是说道作为万物之‘之始’、‘之母’既有‘无名’的特点,又有‘有名’的特点”。参见刘笑敢:《简帛本〈老子〉的思想与学术价值——以北大汉简为契机的新考察》,《国学学刊》2014年第2期。但所谓“并列”实在是太宽泛的说法,一是并列者不必定具有关系;另一是,即便构成并列关系,也不意味并列者没有表现上的先后。],只能是因果关系,即正因为“道”不取任何世俗“命与”的非恒久之“名”(“无名”),所以能具有真正恒久的“名”(“有名”或“有常名”)。是故可以设想,因为“无名”所以“有名”,就是“有生于无”的意谓之一。不过,主张“无名”“有名”是因果关系,只是基于道经首章的推论,是否还有更充分的依据呢?这要再回到前述“名”“德”相应的问题上。那就是,如果将道经首章的“道”之“常名”对应于德经首章的“道”之“上德”(《老子》第二十八章则称“常德”),则可知,“常名”的两种特征即“无名”“有名”正对应于“上德”的两种特征即“不德”“有德”:
“常名”(道之名) “上德”(道之德)
“无名”(没有世俗之“名”) “不德”(否定世俗之“德”)
“有名”(具有真正的“名”) “有德”(具有真正的“德”)
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以”二字正表明“不德”“有德”是一因果关系,则与之对应的“无名”“有名”也该如是,即也可说“常名无名,是以有名”。正如《老子》第三十二章所示: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前文论及,“道”之“无名”有两层意思,一是姿态上的“小”而“无名”(无名位、无功名),一是功德上的“大”而“无名”。此处要强调的,是这两层意思也构成因果关系,如第三十四章的“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就是指以“小”而“无名”的姿态(“不自为大”)成就“大”而“无名”的功德。由此再看上引“始制有名”一语,其实就是“大”而“无名”的另一表达,即“道”的无以称颂的大功德,就是令万物各得名位、各成功名。而令万物“有名”,也正是“道”作为“万物之母”的“有名”的表现。但不论何种“有名”,就其都是出于“道”以“小”自居的“无名”姿态来说,正可见“无名”“有名”的因果关系。而此关系能用“有生于无”表示,又因为上引文明言“名亦既有”,则“无名”即“无”。
顺藤摸瓜,既然能用“有名”出于“无名”解释“有生于无”,自然也能用道经首章的“有欲”“无欲”来解释。因为正如前述,“无名”或不取世俗的名位、功名,这种以“小”自居的姿态反映的就是“道”恒常没有掌控万物的欲求(“常无欲,以观其眇”);而“有名”,无论是“道”具有作为“万物之母”的“常名”,还是令万物各得其所的“始制有名”,反映的就是“道”恒常只有成就万物的欲求(“常有欲,以观其噭/所侥”)。是故,只要“无名”“有名”构成因果关系,“无欲”“有欲”亦必然如此,即正因为“道”恒常没有掌控万物的欲求,所以恒常只有成就万物的欲求。不过,也有人认为老子是主张“无欲”否定“有欲”的[ 参见王安石注,罗家湘辑校:《王安石老子注辑佚会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59页。]。但实际上,老子所谓“无欲”,尤其对“道”来说,不是没有任何欲求,而是没有过分的欲求[ 吕惠卿所谓“方其无欲也,……可名于小矣。方其有欲也,则万物并作而芸芸,……故曰万物皆往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矣”(吕惠卿著、张钰翰点校:《老子吕惠卿注》,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第2页),正是把“常有欲”看做是“道”成就万物的欲求,故老子绝非一概否定“有欲”,古人已有见之。]。如前引之“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强调的就是“道”只要万物各得其所(“始制有名”),却绝不会从成就万物走向掌控万物。这也就是“玄德”所表现的“道”对万物的“生”“为”“长”,始终只在“不有”“不恃”“不宰”的限度内。因此从“知止”来看,“道”对万物的“常无欲”,恰恰揭示出一种至诚至公的“常有欲”。因而,“有生于无”也能进一步解释为“有欲”生于“无欲”。
最后,因为已经指出道经首章的“无名”“无欲”,正是德经首章“无为而无以为”的同义语,则“有生于无”亦能解释为“道”对万物的“有为”是出于“无为而无以为”。后者也就是老子通常说的“无为”,只是德经首章的复杂表述,揭示了这种“无为”既针对行动、也针对动机。至于前者,即出乎“无为”的“有为”,并不是老子通常批判的“有为”,如“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二十九章)的“为”或“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的“妄作”,而是“无为”在结果或效果上的“有为”,亦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的“无不为”。不过,《老子》第三十七章的“无不为”并不见于帛书和郭店简,所以有论者认为它并非老子的主张,而是出于黄老或庄子学派的添加[ 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25页;郑良树:《老子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4-155页;李水海:《帛书老子校笺译评》下册,第927-928页。]。但问题是,正如今本《老子》第三章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帛书作“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北大简作“弗为,则无不治矣”)、第四十八章有“无为而无不为”(郭店简作“亡为而亡不为”),虽然是针对“圣人”与“为道者”来说,却足以证明老子谈及了作为“无为”之效果的“有为”。并且,如果“圣人”與“为道者”的“无为”会有“无不治”“无不为”的效果,他们所依循的“道”岂不更应如此。所以,虽然《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后的“无不为”可能来自后加,却并不违背老学宗旨。因此将“有生于无”解释为“道”之“有为”出于“无为”,原则上没有问题,只是必须限定这“有为”乃是“无为”在结果或效果上的“为”。而此意义的“有为”一定是非掌控的,因为它所从出的“无为”正是对掌控行为及其动机的双重否定(“无为而无以为”)。
由上述,可见从“无”是“德”(特性)而非“道”(实体)的前提出发,不必定把“有生于无”看做生成论的命题,而能说是老子对“道”以不掌控的方式来成就万物的概括,即:
但如此解释“有生于无”,又该如何解释老子紧接着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呢?坚持抽象解释的论者[ 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226页、第235-236页;刘笑敢:《老子古今》上,第419-420、439页。],不仅是将“无”解释为“道”,也将“有”解释为“道”,即“有生于无”是无形之“道”转化为有形之“道”,继而说“天下万物生于有”,就是生于这有形之“道”。而此过程,亦被类比于《老子》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理解。但是,如果“无”是“德”而非“道”,也就能相应地将“有”区别于“道”,即不再解释为有形之“道”,而是理解为“道”之“有德”、“有名”(“名亦既有”)、“有欲”和“有为”(“无不为”)。这样看,“天下万物生于有”同样不是讲生成,而是指“道”以“有”的方式成就万物。但这种“有”绝非掌控性的“有”,相反正是以“不有”“不恃”“不宰”“不德”或“无名”“无欲”“无为”而“有”,这就叫“有生于无”。
四、“无”与“侯王”
再回到“无”的抽象解释上,可以说,认为老子有见于作为生成根源的实体性的“无”,不仅前提未稳,依据也不十分牢靠。故正如本文最初提及的,应该把解释老子“无”观念的重心从生成问题转到价值问题上,即指出老子最关注的不是生成之“无”,而是指导之“无”。后者主要是对当权者来说,即老子论“道”的主要目的,就是期盼“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第三十四章)。“守之”的关键,无疑就是遵循“道”之“德”,即效法“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以同样的“无”的方式治理百姓。正如《老子》第五十七章所示,这一方面就是与“上德无为”相应的对当权者在行动上要求的“我无为”“我无事”,另一方面是与“无以为”相应的在动机上要求的“我好静”“我无欲”。可见老子论“无”,不仅有作为“道”之德行的“无”(“无为而无以为”或“无名”“无欲”),也有作为“侯王”德行的“无”(“我无为”“我无欲”)。因此,贯彻“无”的指导,也就是将“道”之“无”落实为“侯王”之“无”。怎样落实呢?老子说的“为无为,事无事”(《老子》第六十三章)以及“欲不欲,……学不学,……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正透露出“侯王”之“无”的实现,还是以否定掌控行为及欲求为中心。
因此,老子也强调“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 曹峰特别强调“损之又损”,按北大简作“损之又损之”讲,更为清楚。“损”即减损功夫,“之”则是“损”的对象,指代“为学日益”的东西,如“仁”“义”“礼”。参见氏著:《“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 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3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从先秦“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基本倾向看,“为学日益”但“为道日损”的,应该就是对人民庶物有所掌控的行动和欲求。而这,又主要是减损对名利的占有,故说: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这里,“知止”不再只是前述“道”对万物只成就但不掌控的态度(即“常无欲”),更是对侯王的一种要求,即效法“道”之“无”,首先是减损名利心。但又不同于儒家“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的修养功夫,而是基于“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利害权衡。因此对“道”之“无”的效法,目标就被设定为避免侮辱与危险,以求“可以长久”。而从下文看,老子最关心的就是政权的“长久”,即所谓: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第五十九章)
对“侯王”的“治人事天”提出“啬”的要求,正是以“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为目标。但“啬”不是一般意义的“爱惜”(《老子河上公章句·守道》),也不是心术上讲的“爱其精神,啬其智识”(《韩非子·解老》),而仍应从“为道日损”的角度理解,就是把掌控人民庶物的行动与欲求降到最低。由此引出“重积德”的建议,就是让当权者重视和积蓄“道”所体现的“无”之“德”。这说明,“无”的指导主要是对政权如何“长久”的指导。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长久”,恰恰也是周人最关心的问题,正如周公对成王的告诫: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诰》)
周人忧患天命,核心就是“历年”。若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则其崇尚“长久”,必与周人相关。不仅如此,周人“祈天永命”靠的是“德”(“疾敬德”);老子论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也是讲“德”(“重积德”)。因之,理解老子以“无”论“德”的用意,必须参考周人的观念。而其核心,就是双方对“德”的不同理解[ 对此,郑开已就周人重“明德”与老子重“玄德”展开对比,可参见氏著:《玄德论——关于老子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解读与阐释》,《商丘师范學院学报》2009年第1期。]。如前述,早期中国将“德”看做“得其名”“得其位”的根据,是能对天下人产生正面影响的东西,在老子眼中却是负面的掌控性因素。在德经首章中,这看似是针对儒家来说,但儒家相信“德”的影响力(“仁”的感化、“义”的教化和“礼”的约束),尤其是强调“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根源就在周人的“疾敬德”。而勤政有为,正是“疾敬德”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所谓:
勤用明德。(《尚书·梓材》)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尚书·旅獒》)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尚书·洛诰》)
对“勤”的倡导,最能表现周人所“敬”的是一种大有为之“德”。
但在老子,勤政有为之“德”却明显是被当做掌控人民庶物的“下德”。而这,不仅是对周人的挑战,也是对常识的挑战。因为不仅是在周人眼中,就是一般看来,越要维系政权的“长久”,就越应该“夙夜罔或不勤”,哪还有无为无事反得“受天永命”的道理呢?那么,老子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按以下论述: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第四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
据此,如果说强硬者死、柔弱者生是自然与人间的基本定则,则老子从周人“勤用明德”的大有为之治中,看到的就是“强”而不“久”的危险。正如《老子》第五十七章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就是以强力的掌控与禁止越多,造成的麻烦和危险也越大。这与德经首章强调的从“仁”治到“礼”治,掌控越强、抵触越大的逻辑完全一致。不过,老子所谓“守柔曰强”(《老子》第五十二章)或“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并不是对“柔弱”的过分夸张,即并不是真的主张弱能胜强,而毋宁说,他眼中有待“守柔”的人本身并不“柔弱”,反倒可能是现实生活中能影响人民庶物的权力阶层。因此,“守柔”或崇尚“柔弱”,实际是让强者懂得示弱,以维系“长生久视”的建议。而这,很可能就是针对周人来说。
当然,不能说周人的“德”治完全就是“刚强”之治。如《尚书·洪范》所见: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兇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上论为政“三德”,是周人对殷商治理经验的继承与总结。其中,除了对有德者是以“正直”的方式对待,对多数人的统治则或刚或柔。这包括,对政治盟友或地位高的人,要以“柔克”待之;对不服从和地位低的人,则以“刚克”制之。但在西周统治者眼中,说是要以“柔克”待之的“燮友”和“高明”之人,在维系君主权威的根本方面,仍是需要“刚克”的对象。如铭文所记成王告诫臣下不可享乐,要朝夕勤政的命辞:“汝勿伪余,乃辟一人”“刑禀于文王政德,若文王令二三正”“敬雍德,……畏天威”(二十三祀盂鼎),这种居高临下的威吓口气,堪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的生动写照。可见周人的为政“三德”,实以“刚克”为本,仍如铭文所记:
圉(刚强威武)武王,遹征四方。……圣成王,左右,(刚强)鲧(强御)用(开始)(治理)周邦。(共王·史墙盘)
这正是把“刚克”看做周先王的立国之本。而标榜先王“鲧用周邦”,固然与周政权伐东夷、征鬼方的紧迫任务有关,但与其说是战时的权益之计,不如说是周人的一贯诉求,即常态政治生活也离不开刚硬权威,亦即“建用皇极”时要求的“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尚书·洪范》)。
从以上背景看,老子倡导“柔”“弱”,可能就是出于对周人重“”但“刚克”不能“长久”的反思。此时,作为概念的“无”被提炼出来就绝非偶然,因为正如前述,它实际是老子对“道”之“德”所呈现的非掌控特征(“无名”“无欲”“无为而无以为”)的纲领性表述。因此,让当权者以“守柔”“示弱”的方式“长生久视”,就是在遵循“无”的指导。这种指导性的“无”,才是老子“无”观念的核心。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