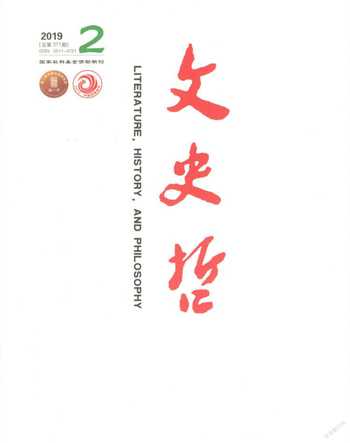《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文的文本结构与学术建构:以小说家为核心的考察
张昊苏 陈洪
摘要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小序在文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体例,其中的“九流框架”与“王官体系”均为后设,蕴含有刘歆以经学思想作为主导,重新建构子学分类体系与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和著录的深入解读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艺文志》在新创小说家并将其纳入九流框架的基础上,还同时尝试融合小说的方术属性与子学属性为一手。这一汇通之举实质上造成了部分的文本失控,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和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 小说家 文本失控
一 引言
作为目录学和学术史的重要文献,《汉书·艺文志》(下简称《艺文志》)向为学界重点研究对象。且由于民国以来诸子学研究的兴起,《艺文志》诸子略(下简称诸子略)更得到深刻地关注。概言之,则主要可分为如下数类:1.传统的笺注之学,包括对诸子略的注释、通解、考证、辨伪[作者简介:张昊苏,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代表性研究有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5—311页;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三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6—373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6—347页。];2.以诸子略为核心还原先秦子学的起源、流别、发展,更进而从学术史高度反思子学发展历程[ 代表性研究有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5—306页;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331-340页,;傅斯年:《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战国子家”与<史记>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13页;李锐:《九流:从创建的目录名称到虚构的历史事实》,《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42页。];3.对诸子略分类方式的探析与批判[ 代表性研究有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辨》,《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五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7—272页。];4.对诸子略中某类或某几类序文和著录的专题研究[ 代表性研究有程千帆:《杂家名实辨证》,《程千帆全集 第7卷 闲堂文薮》,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8—207页。]。另外值得特别单独提出的是,由于“小说”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不可绕过的话题,对“小说家”内涵的讨论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 本文所指“小说”“小说家”,如非特别说明,皆指《艺文志》中概念,并不涉及今天文学史的小说观。]。研究者从学术流派、文体特性两方面予其综合性的解读,产生诸多思考结构近似的假设与歧说。概言之,主要有1.学派说[ 即认为小说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小学派,持此说者如陈卫星:《学说之别而非文体之分——<汉书·艺文志>小说观探原》,《天府新论》2006年第1期。];2.资料库说[ 即认为小说的内容是著录九流黜落的文本,持此说者如徐建委:《说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文体说[ 即认为小說是一种具有某种特殊文字形式的文类,持此说者如罗宁:《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4.琐碎说[ 持此说者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孟昭连:《“小说”考辨》,《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从小说的起源来看,基于对“稗官”的不同理解及扬弃,又有出自传说说、出自民意说、出自祝官说、出自方士说、出自训方氏说等观点。
前人研究成果颇为浩繁,此特举其大端而已。然而仅就此回溯而言,从中可看出的是,尽管在认同《艺文志》具有体系性的大背景下[ 近人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五卷,第215—224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释例》(《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第108-132页)等均为专门探讨《汉书》体例之著,此外单篇涉及该问题者尚甚多。但从这些著作的影响力和证据效力来看,目前学界仍只是概括认定《艺文志》的体系性,但对于究竟具备哪些“体系”还无深入论证。说详张昊苏:《<史记>早期流传补论》,《文献》2018年第2期;《“有录无书”与<史记>亡篇新考》,台北:《史原》复刊第九辑,2018年9月。],不少学者旨在追求其文本结构的内在理路;但这一追求常常只是作为回溯先秦思想的工具而存在的。因此,在发现诸子略九流十家框架殊不能反映先秦学术之实以后,学者多对其加以扬弃,而转向王官制度与诸子渊源的研究。当诸子略作为学术史论著的意义得以耗罄后,学界较少继续将其当作一重要的学术文本加以看待。因此相关的材料虽已被前人拈出,但似乎并未引出相应之结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之浩繁反而容易引发真相的淆乱与遮蔽:淆乱并非“百家争鸣”,而是缺乏研究评价标准的体现。而所谓歧说,不过是基于某一观念而自由心证的产物,缺乏应有的逻辑理路与文献依据。因此,本文除行文中必要之征引而外,无意重新梳理学术史——细致的梳理或有助于条列前人疏失,但却对于解决核心问题毫无帮助:在根本研究方法存在漏洞、核心思考进路及大前提存在混乱的时候,自甘低层次的研究综述只可能是基于某种成见的叠床架屋;惟有重新反思研究方法,方有进一步推进研究之可能性。这里并非一味否定前贤的探索,而是欲将聚焦点集中于问题本身,故不必过度涉足学术史领域而令本末倒置。本文旨趣在于研究一“学术问题”而非“学术史问题”。
平心而论,前人看似广博的材料征引实际上忽略了对文本语境的考察。由于文献片段之上下文联系被忽视,其文本信息未能得到全面解读,而所征引的材料也十九居于外围,并未深入该问题之核心领域。具体言之,即在于对诸子略之“序”的性质与深层含义缺乏深考,故所论必多粗疏。故本文尝试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以诸子略序文为进路,对其文本结构与学术建构进行分析。其旨趣如下:
其一,将诸子略文本重归于其历史语境之中。诸子略序文虽然是研究先秦子学发展的重要学术史文献,但其生成于西汉之末,写定于东汉之初;其内容也兼及上古以至于校书当时的全部子学文献,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本质上是汉代学术思想的产物,内容则是对上古以至于西汉末期全部学术文本的再整理。将诸子略置于其时代中加以考察,即复归于汉代学术思想环境中加以解读,本是文献研究的基本常识。然而在目录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学者却极易忽视目录文本的后设性,故而运用此法展开研究确有其急迫性。[ 类似的理论见解可参考周彦文的相关论述,惜其虽有宏大的文献学理论分析,但对具体问题的考论却微嫌不足。参周彦文:《中国文献学理论》,台北:学生书局,2011年,第44—55页。]
其二,以诸子略为一例证,解析《艺文志》的体系性与层累生成性[ 李锐的研究对本文的论述颇有启发。李锐:《刘向、刘歆校书差别》,《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第185—194页。]。《艺文志》具有一定的分类体系、著录规范和思想体系,乃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合法性所系。然而仅就《艺文志》本身的成书过程而言,一般来说学者公认《艺文志》为删削刘歆《七略》而成,而《七略》又源于刘向《别录》[ 程千帆认为《七略》先成,而后别有《别录》,(《<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程千帆全集 第7卷 闲堂文薮》,第180-181页。)但其说似并未得到学界承认。考虑到对本文论述问题并未产生特殊冲击,暂依通行说法将今本《艺文志》内容的实质作者归属于刘歆。如遇具体问题,再单独加以讨论。],其层累造成特性导致文本内容究竟反映何时、何人的学术旨趣,应有更具体而微的讨论。就本文所涉课题的先行研究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复原的方法仍然不免原始,没能首先厘清所使用材料之史料价值及可运用之限度。对此,本文的方法是借助《艺文志》的直接记载进行文本细读。而本文所讨论者,也不仅仅在乎对结论的“创新”,而意图同时在于对现有考据方法及文献学理论进行反思。[ 说详张昊苏:《“有录无书”与<史记>亡篇新考》。]
由于对上述问题缺乏共识,导致对于研究《艺文志》本身的情况,都留下了诸多未解之处。对所研究之对象缺乏合乎历史语境的定义,缺乏循名责实的能力,这正是“学术现代化”以来不少论著文不对题的根源所在。本文虽不敢言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但尝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稍加反思,希望能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
二 重考诸子略小序的叙述架构
前人对诸子略小序的理解多有缺失。因其多缺失,故结论亦莫衷一是。仅以近代以来学术史家成果观之:认为诸子略“王官之学”说基本客观反映了先秦子学面貌并间有修订者,有章太炎[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等;其说仅借助《艺文志》的思路,并未专注于论证其框架建构的是非。明确批驳“王官之学”,而又以己意提出诸子“所出”者,有胡适[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論》,《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以“职业”代替“王官”,其核心是将子学时代后移,其解释框架亦深受《艺文志》影响。故除柳诒征[ 柳诒征:《论今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见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132页。 ]等学者当时已对胡适之说作出回应外,近人沈文倬[ 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25—501页。]亦承其绪,重新回归对王官之学的分析,然沈氏之论述仅涉及王官之学,而并未沟通子学,或已意识到诸子略说法的不可信据。认为诸子略之说法毫无学术意义,仅是一种分类方式者有梁启超。梁氏认为《艺文志》的文献著录值得注意,但其分类“不过目录学一种利便”,对王官之学的探讨“殊不必重视”[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辨》,第269页。],今人李锐[ 李锐:《九流:从创建的目录名称到虚构的历史事实》,《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第22—42页。]等复对梁说加以推进。然这一思路实有过度简化问题之嫌[ 梁启超的见解可以找出多种反例:首先,典型的“分类利便”方法服务于文献整理实务,故著录当考虑卷数均衡、储藏位置等,相对较少接受以前的学术分类方式(乃至如明代目录直接按柜子编号),而诸子略各部类的卷数实际上极不均衡,似无“利便”可言。第二,诸子略小序中对每类都有所定义,且有具有学理意义的讨论,如果单纯利便起见,则这些话毫无刻意编造的意义,且不具备任何价值。这与诸子略小序的文本性质是抵牾的。]。此外雷戈[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重于思辨的研究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面貌提出了新颖的推想,其中不乏切中肯綮的论断。
从先秦思想研究的角度看,九流框架殊不能反映学术之实,亟需加以颠覆,前人对此知之已稔。但旧的批评或立足于从制度入手讨论“王官”之所指、或否定其与九流之关系,及重新追溯九流十家之本来所出,考据虽详,但仍是运用西汉材料以解决先秦学术思想问题,其实存在认识论上的误区,未免迂远。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对于理解《艺文志》所涉问题则毫无帮助。形成这一研究局面的主要原因乃学者究心的内容乃先秦学术史,本质上并非对古典目录文本自身的研究。是以,九流框架究竟是刘歆学术识力不足导致的研究失误?抑或其主观对学术加以有意的重构?其核心材料虽已被前人拈出,但并未引出相应之结论。事实上,前人的关注点罕能及于此处。
但应特别提出的是,前人研究中有两处核心见解极为重要:
其一,王官皆虚拟。诸子略所及王官,皆虚拟或泛指,并不直接指向某一上古职官,这一“诸子出于王官说”亦不见此前学术史著。足见王官只是刘歆理想所悬拟,以表示一种学术理解的态度,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其二,九流为后设。九流之家数命名此前已有,但以九流[ 值得注意的是,“九流”而非“十家”的数字,很可能即含有泛指之意。]总括子学全部流派,实为此前所无。取之以衡战国诸子,当前的多种研究表明此种截然而分的学理叙事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且汉人的学派观念淡薄,学者多杂糅各家,流派更为难定。《艺文志》著录之流派划分,亦往往与时人观点不符——如《淮南子》自认为道家,而《艺文志》著录为杂家,足见其并非当时公认之见解。
由此观之,九流框架为刘歆所自创,此前依傍极薄,当可想见。以学术史的角度看,九流框架提出的依据及时代背景为何?其框架是自具系统还是仅属利便?九流框架究竟是仅具学术史影响而无学理可言,抑或其本身应属于西汉后期重要的学术著作,尚属颇为重要的争议性命题,亦即本文需要首先解决者。
《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小序云: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8页。]
其文可理解为诸子略小序写作的“范本”。在写作结构上,各类之小序实大同小异,兹不具引。据此初步分析诸子略小序的大致书法如下:
1.以“x家者流,盖出于xx之官,xxxx者也”之语标明“x家”与“xx王官”的可能渊源关系及王官执掌,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2.引孔子或六经之语说明该派学术在三代政治上之重要价值,实际即指出子学应附属于经学。
3.以“x者为之,则xxx”之贬义词说明该派的末流倾向及恶劣影响,实际即以经学为标准批评子学的见解。
诸子略小序的这一基本书写结构暗含了下述学术发展思维模式:王官执掌→形成学派→六经及孔子对该学派功用的论述→该学派的错误倾向及危害。
对此思维模式,前贤多注意到刘歆用子学比附王官之学的错误,但却忽略了小序中另一重要的观念:即用经学思想观念衡量各个子学流派的是非高下,而并非以子学本身的发展流变与内在缺陷作为评判标准,这一思维模式是刘歆以前的学术史论著所罕见的,盖生成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 雷戈认为:“战国诸子在后战国被皇权主义规范成一种大一统式的思想方式。这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和观点分歧,而是说,皇权主义秩序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最大限度的政治-思想共识边界。这种大一统式的政治-思想共识几乎覆盖了人们之间的一切观念分歧,从而使之成为无关宏旨的话语碎片……在皇权意识形态中,诸子皆由道而退化或简化为术,而无原则之分殊”,这一观点指出批评背后的政治背景,恰可与本文关注学术思想本身的进路形成某种形式的互补。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第9页。]
刘歆这一批评并非意图指出该学派存在本质缺陷的“同行评议”,而是将其目为违背经学理想的末流;换言之,即主张该学派的核心理念应然且实然地合乎经学要求。如序文中批评“道家者流”的“放者”为“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2页。],其指向显为《道德经》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绝仁弃义”等思想;“墨家者流”的“蔽者”为“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8页。],亦指向《墨子》的“节用”“兼爱”“非乐”等思想。其他各派也同样具有上述特性,战国诸子思想成为诸子略小序的直接批判对象。
刘歆以经学思想批判道家、墨家,不过属门户之见,无足为奇;但将老子、墨子等学派宗主批评为学派的末流,这一见解无疑具有特殊意义。诸子略序指出: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6页。]
既然刘歆认为诸子学是六经支流,那么要求其理想状态当合乎经学要求就再合适不过了。六经既为王官之学,那么诸子亦当由王官衍生而出,故老子、墨子等既非三代王官,显然不能具备流派创始人的地位。诸子出于王官史无明证,故刘歆漫取职官以比附之,并以“盖”表明出于推度。这里须注意的是,作为《周礼》名家,刘歆并未以《周礼》中的官职与诸子略的王官之学对应,而仅用不甚明确的职官称谓加以含混比附,恰可证明这一比附欠缺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证据。[ 另外,考虑到《周礼》在王莽时方立学官,而《七略》成于此前,则似可怀疑此时的刘歆是否对《周礼》有较深入之了解,并对“刘歆伪《周礼》”一问题提出新的启发。]后世重要目录著作中,惟《隋书·经籍志》强改《艺文志》王官之说,以《周礼》比附子学,余嘉锡已力言其非,可见其在事实上的不足信据。
由此观之,诸子略的学术体系并非基于严密的学术史考察,而是刘歆以儒家政治偏见凌驾当时文献面貌的人为产物。诸子出于王官说仅是一种人为建构而非历史还原。刘歆将诸子著作判分为十类,并为其强赋渊源,从而缔造出王官之学→九流十家→百家著述的思想发展体系。“百家著述”反映的是西汉后期见存文献的面貌,“九流十家”则是刘歆基于该面貌而总结出的新的学术体系。换言之,《艺文志》中所谓“诸子”流派分类非先秦诸子亦非西汉诸子(关于其不尽合乎西汉子学面目,下别有说),而是经过刘歆重构的不同于任何时期的理想化诸子学面貌。这一杂糅了各时期且又加新构的体系悬拟恰是经学家之所长——《周礼》即同样是以上述思维所拟构的政治制度体系。刘歆之分类亦非基于先秦学术演进的擘画,而是将古人著述强行纳入当代分类,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近代以来用“中图法”为传统四部典籍定性之举。也正因如此,各派的宗主也难免成为“末流”的命运。从政治角度看,这大抵即“诸子皆王官”这一政治现状的学术史表达,即用以消解各派思想的独立性,而将其纳入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中。换言之,其本质是经学的。
然刘歆的九流体系虽出个人悬拟,实亦受到早期学术史论著之深刻影响。《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各家之违道,却未能指出任何有力之反驳,甚而有“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之语,足见其先拟定了某种有唯一性与先验性的真理,然后再施以批评。荀子的批评理论见解只是门户之见,但从中却可看出荀子欲抨击“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亦即注重政治之实效。这一将治理“天下”的“政治效用”作为核心的方式,无疑是天下走势日趋明朗后的产物,亦引导了刘歆评判九流得失的思想理路。此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不特举具体某人某说,可见其关注点亦非哲学的,乃聚焦于“我有以治天下”之途径,进一步明确表明其学术立场在于政治维度。相较而言,诸子略小序及班氏注文更近于《论六家要旨》,其言涉及各派政治实践“术”的问题,并未探讨诸子之学的理论得失。这种重效验而轻理论的思维模式,可见其学术史渊源。刘歆在批评中又以为“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6页。],并依此观念做出从“道通于一”(经学)到“王纲解纽”(诸子)式的解读,这一解读方式又明显受到《庄子·天下》的影响。《庄子·天下》明言“道术将为天下裂”,然后于具体评述各家学说时必加“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将各派皆评为有思维局限性的一曲之士(即“博大”之老庄亦莫能自免),而又承认其独特之优长,以求上溯古之大体大道,显为刘歆思想因緣之一。此复与《论六家要旨》中“虽百家弗能废也”之见解相似,然司马谈乃就百家以衡一家之独特性,《庄子·天下》及《艺文志》乃用悬拟之上古道术以批评一家之局限性,其立场又有所不同也。
综上所述,刘歆之体系并非全出臆造,实乃继承早期学术史论的集大成之作,其所谓“九流十家”盖即近似于现在之“政治流派”。通过上述的文本分析,亦可证明刘歆所建立的体系并非单纯的利便起见。
此见解尚可由刘歆所设类目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必须结合此前之学术史论著进行整体观照方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还是《论六家要旨》,其针对的都是当时的学术现状,而无意作严密的学术史考量。与之相同,诸子略同样是针对西汉后期学术而建构的学术体系。而鉴于诸子略又同时代表了一份集大成的文献整理工作,故刘歆在建构新体系的同时,亦不得不将早期著作纳入到九流之中,其间的种种附会与混乱,即因此历时性而生。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足见西汉中期已逐渐将“百家”合并成为较具代表性的“六家”。将早期具体指师法的“家”(此类见《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等)抽象为某种范围较广的学术宗旨,以“家”为流派,这一思路明显对刘歆有重要影响。与《论六家要旨》相比,《艺文志》所增为杂、农、纵横、小说四家。其中著录“纵横十二家,百七篇”[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9页。]“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3页。],数量与法、名、墨略等;著录“杂二十家,四百三卷”[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1页。]与阴阳家略等;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数量超过儒、道两家,为诸子之最。上述篇数的巨大差异,显然绝非单纯为了分类或图书庋藏的方便。前文既已否认其反映先秦学术客观面貌的可能性,故只能理解为刘歆基于西汉后期子学发展情势的某种学术体系观念,换言之,这一体系即对《论六家要旨》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诸子略之“杂家”实对应《论六家要旨》之“道德家”,此见解与西汉中期人之学术理解相违[ 劳思光指出“足见自西汉初年起,谈论‘道家’者实已将‘道家’原旨失去,而予以‘杂家化’。……(《淮南子》)处处以‘道家’自居……《淮南》一书恰代表《论六家要指》中所论之‘道家’,亦即‘杂家化’之道家,绝非先秦道家之本来面目。”其说至精。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90—91页。],该点之学术史意义亦多为前人所忽略。由此一名实不合之倾向,可知刘歆并非漫无义例观念,而实有重构学术体系的深意存焉。
三 王官系统下的小说家性质再探
如上节所说,诸子略实为一种新式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必须结合此前之学术史论著进行整体观照方能理解。“十家”之中“九流”易于理解,然若依据今人对小说家之解读,则适足以成为前说之枝指,故欲进一步说明本文论点,对小说家进行具体解释,实甚必要。九流之内容既然关注政治效用而轻视哲学思想,则小说家在刘歆眼中亦当属于一种政治流派。然近人往往以舶来之“哲学”理解子学,未谙其核心实乃政治维度,更复有由哲学而随意羼入同样舶来之“文学”者,所论适足误导。惟因“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已将小说家归于“不可观”,其究竟具有在刘歆的子学体系中占据何种地位尚存问题。小说家是附属于九流的资料性文本,不具备独立成学资格?抑或小说家本可属于子学/政治哲学之“十家”之一,只是因其水平较低而被贬斥为“不可观”?这一争议的背后,实际上是诸子略“小说家”究竟有学派属性还是单纯贬义词的问题。在这里顺带说明的是,鉴于此前典籍无“小说家”一词,“小说”一词亦无大致明确的公认定义,已可确定“小说家”实为刘歆所新建构之一种特别概念,而“小说”的理解亦与此前的称引不同。
对于小说家性质的问题,同样应从诸子略小说家之序文入手考察。其言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
小序所指出之核心问题有二事:
其一,小说家的内容是“街谈巷语”,其作者是“道听途说者”,亦即生成于“野”而非“王官”。所谓“出于稗官”,则仅指稗官对“街谈巷语”的记录与上奏,并未提及存在加工、修订等编辑工作。这与前揭各类皆直接出于王官的渊源有明显不同。稗官,赵岩、张世超基于对睡虎地、龙岗出土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的考察,指出稗官的原初意为与“正官”相对的“别官”,“小”只是其后起义[ 赵岩、张世超:《论秦汉简牍中的“稗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这一见解后出转精。那么,依照小序的论述,小说家的渊源、内容,都与王官无涉,即使其传播是一度经过“稗官”之手,亦只是边缘化的“别官”而非王官。
其二,小说家的学术水平为“君子弗为”的“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即使“一言可采”亦不代表有太大价值,即仅作文献的保存而不加以较高评价,因此才有“九流十家”之别。诸子略序言“九家之学,不犹愈于野乎?”,则小说家即“不愈于野”的在野者。故其“一言可采”的“礼失求诸野”特性兼指其渊源与价值。这里是否暗示了小说家的文体特性,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在“诸子出于王官说”全出刘歆悬拟的思想背景下,小说家依然未被纳入王官系统,则存在两种理解可能:(1)由于小说家与王官毫无比附之可能,刘歆客观上确无力将其纳入王官系统,仅能用“稗官说”这一擦边球方式展开解说,故立足于王官价值本位极力批评其学术价值;(2)小说家本有纳入王官系统之可能(如《隋书·经籍志》的尝试),但由于刘歆对小说家的学术价值极度轻视,已预设“一家不可观”的成见,故主观拒斥其进入王官系统,并借此进一步贬低其价值。
二者目前皆为或然的判断,但可确定的是,小说家在刘歆的王官系统中处于“枝指”的尴尬位置,独立而与“九家”所构成的子学思想体系形成对立。从逻辑上推断,小说家既然根本不应从属于上述之子学思想体系,则其非各家黜落之文本杂汇可知。因若仅为黜落而无其他含义,那么强为立类实际上殊有害于体系的建构;且从《艺文志》著录看,各家中亦有颇多值得黜落之文本,足证“黜落说”之难以成立。那么,小说家既非可与各家并列的“王官之学”,又非各家黜落文本的集合,而仍得以单独立类,似只有唯一可能:即西汉后期小说家之独立已成事实,故刘歆不得不立小说一家以安置该类文献。由是观之,则小说家当有其相对独立之定义且在当时必已形成相当基础,这一基础直接体现于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之文献。
由于王官说的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学派宗主”如老子、墨子等皆不能成为诸子略所承认的学派始祖,而必须上溯至上古,或至少须极度接近于王官。而诸子略的著录也基本遵循了这一规律。如道家首《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然后及《老子》;墨家首“《尹佚》二篇”等才最后著录及《墨子》,皆属其例。此类书籍多不存,然必多为后世依托、修订之产物。对此类文献在年代上的不可靠,汉人实已有一定辨别能力,如《艺文志》班固注《太公》即言“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9页。];又如注杂家《大禹》亦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0页。]。班固注十九皆本于刘向歆父子的结论,则从间接证据与理势推论,刘歆必当具备分辨此类作品依托与否的能力。但诸子略犹将上述作品按照所依托作者的年代先后,次序著录于该类之首,则是出于为“王官说”寻找渊源的必然之举,若依古史辨派的惯用语,盖属于建立“传说时代之学术”的举措。先秦学术本无“十家”之说,故不论诸子略所设流派此前是否已有其名,都需要重新审定其应该归属于何类。故可推测刘歆编辑诸子略的工作顺序当如下:
确定“诸子类”文献大致情况→人为规定“九流十家”的分类方式→确定其性质并上溯至某一王官→根据性质与王官执掌之相近,除按照后世家派分类外,倒填难以归类的“传说”文献的派别归属
某一著作归入某种流派,实际存在三种可能:(1)该文献或其作者本身已足以确定应属某类;(2)该文献被其述者或学界普遍认为应属某类;(3)刘歆依据其学术体系理论,判定该文献应属某类。其中(2)(3)两种可能较难具体区分,但皆属于汉人重新规定战国学术流派的结果,体现在著录上的作用是一致的,即诸子略著录表现出一种汉人为战国学派上溯至传说时代的倾向。由于刘歆独特的学术判派标准,这一上溯必然有与当时通说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诸子略既依照书名所指作者的先后顺序排列,那么“传说时代之学术”以后,著录的则自然是该学派的始祖人物。[ 以之衡诸子略著录,《墨子》而外,似无反例。按《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在墨家类最末,位于“墨翟弟子”所作的《随巢子》、《胡非子》之后,疑为流传错简使然,未必定存深意,似可存而不论。]
兹以此考察诸子略小说家类之著录,《伊尹说》至《黄帝说》[ 《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托名“黄帝”诸著作,并未依黄帝传说之时代排序,则刘歆似否认黄帝作为学派始祖的可能。由此观之,《黄帝说》之“依托”虽同于其上诸书,亦极可能应归于下述“小说始祖”一类,因武帝之封禅实受方士撺掇以仿效黄帝也。]九家多言“依托”[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4页。],殆即所谓“传说时代之小说”;《封禅方说》以下六家多以“武帝时”等语标明时代,即刘歆所认定的“小说文献”。除不可考定时代的依托著作外(其著录标准似亦难以考察),小说家著录皆武帝以后书,则可知小说家之起源当在武帝时矣。衡量诸子略所涉及之小说家定义,当以武帝以降六部著作为主要依据,并参以其余九部。惟小说家著录之诸书皆已亡佚,即所涉之只言片语亦难考察,稍可考者似仅有《虞初周说》、《百家》二种,下尝试以此二书为中心,对小说家著录情况加以进一步考释。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云“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张衡《西京赋》有“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 萧统编:《文选》卷第二《张平子西京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8页。]之语。过去小说史家仅从时代演进观之,认为其说代表了诸子略小说家序的演进,并未予以特别关注。但本文既指出“王官之学”等演进模式的纯出悬拟,则可对斯言进行更深入之解读。在张衡这样的一般读者来看,小说家实始于“虞初”,而只有这类“一般读者”之认知在刘歆以前即具相当影响,方可能有刘歆上溯其学术渊源及著录类似性质典籍之举。這一逻辑与前文论证相合。《西京赋》所谓“秘书”“九百”既为《艺文志》著录所证实,“实俟实储”亦合乎小序“缀而不忘”的悬拟,则“本自虞初”虽不见于《艺文志》,当亦有其据。按虞初为武帝时人,合乎上文小说起源在武帝时的推测;其著录于宣帝时之《臣寿周纪》以后,盖因其九百四十三篇并非皆出虞初之手,而为后世小说集大成之著作,特托名于虞初耳[ 作为旁证,诸子略墨家类将《墨子》列为最末,甚至在“墨翟弟子”所著的《随巢子》、《胡非子》之后,可能是认为《墨子》并非墨子本人著作,而且结集较晚。]。因此,“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似可理解为九百篇发源于虞初,而非虞初尽撰九百篇之《周说》,是以后世小说家咸托其名以进行小说创作。应认为,《虞初周说》具备“小说起源”的学术史意义,可作为两汉人之小说观的重要代表。根据较早材料所引,及诸子略著录诸书情况,《虞初周说》似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虞初的职业属于方士,大抵为民间求干禄者之特殊方式,其职位多为“待诏”,即介于平民与职官之间。其所著小说为“医巫厌祝之术”[ 萧统编:《文选》卷第二《张平子西京赋》,第68页。],以神仙方技为核心。顺带指出,此类方士并无严密理论指导,其身份即汉人常提及的“燕齐海上之方士”(《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与持阴阳五行说者(悬拟的王官背景即“祝官”)不同。同时期之《封禅方说》、同类之《黄帝说》盖与之近似,《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二种或可存疑;
其二,《虞初周说》以上古史事与帝王神话作为其宣讲方术的历史语境,应劭注“其说以周书为本”[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西京赋》写内容包括“于是蚩尤秉钺,奋鬛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蝄蜽,莫能逢旃”[ 萧统编:《文选》卷第二《张平子西京赋》,第68页。]。仅从其含有载史之内容考量,同时期之《臣寿周纪》、同类之《周考》、《青史子》很可能与之近似;
其三,其书为备天子顾问之用,“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 萧统编:《文选》卷第二《张平子西京赋》,第68页。]。同时期之诸书如盖皆与之近似,《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尤为明显,然似无直接证据支持。
三点之中,似以一、二两点最为重要。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虞初周说》所代表之“小说家”殆即某种史事与方术的共同体,是以其既不等同于后世之“史部小说”,亦不等同于《艺文志》之“方技略”或“数术略”。王瑶指出“小说本出于方士对闾里传说的改造和修饰,所以……也是凭借于史的”[ 王瑶:《小说与方术》,《王瑶文论选》,第24页。],其对方士之理解较深刻,最接近上文对《虞初周说》的考察结论。
然若骤然认为上揭《虞初周说》的性质即等同于早期小说或小说家的性质,则尚存颇多问题难以圆满解决。
首先是小说家与方技略之关系。初看,小说家似即某种“方技理论”(如陈槃指出“伎术”、“方技”、“方”为互文[ 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4页。],《艺文志》方技略神仙家亦指出其“诞欺怪迂”),由于与作为技术的方技有所区别,故被刘歆拔擢入诸子略中。但《艺文志》数术略序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75页。],与阴阳家小序“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4页。]云云恰可对应。方技略序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80页。],虽未指出本来所出,然仍以王官与之相比附,以“王官系统”观之,似反较小说家地位为高。且刘歆既为数术、方技寻出王官渊源,则无单纯刻意贬低小说家之理由。如果小说家即单纯是“方技理论”一流,何以产生此等结构上的矛盾?
其二,《虞初周说》一类方士书与小说家著录之其他文本产生矛盾。在小说家著录之十五种书中,明确可见与方术有关者惟六种,其余诸书虽近似道家一流,但却无证据说明即言神仙方术者。如《周考》班注“考周事也”、《青史子》班注“古史官记事也”、《宋子》班注“其言黄老意”云云[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4页。],其性质袁行霈总结为“近乎史”、“近乎子”,与《虞初周说》的方士气味不属,对其间所具备的区别与共性究竟应如何理解,目前的研究并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今人所谓“相似”多出于结论先行的勉强比附,必须对其矛盾展开另一较具说服力之解释。
如果我们完全接受王瑶的观点,当然可以基于方术维度继续展开循环论证式的推理。然《百家》的存在可能推翻上述循环论证。
四 《百家》及小说家的子学维度
对此,复当对《百家》一书的性质作较为深入的考察,探讨其究竟有无作为反证的资格。《百家》一书的直接材料实较《虞初周说》为多,但由于其位在小说家之末,其证据效力必须结合《艺文志》著录之特色参观。
《百家》百三十九卷,刘向《说苑叙录》言:“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 刘向、刘歆撰,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按诸子略多有“x家言”之书,其《儒家言》、《道家言》、《杂阴阳》、《法家言》、《杂家言》,班注并云“不知作者”,盖皆聚合某流派之逸说而成书者,惟《百家》无此语,盖因《说苑叙录》已明言《百家》之编者为刘向(或该书另有叙录),不必更为指出也。又按赵善诒《说苑疏证》录《叙录》作“别集以为百家后”,孙诒让、姚振宗等皆以为“后”当从下读,为“复”字之讹,较之卢文弨认为“后”下有阙文说更进一步。然此仅就文义推度,尚别有一证可补充。若原本确当作“百家后”,则此句实指上述诸书皆刘向所编,并将其各自归入某类中。然刘向校书时似无十家细类,则不可能将各书分别归入各家之后。即使刘向已新拟九流十家之目,却有意依旧将“九流”泛称为“百家”,于义亦不甚通。则《说苑叙录》所指“百家”,当确为小说家类著录之《百家》无疑。],则此书编次为刘向所定,且与《说苑》有同样来源及性质,惟思想深浅是非有所不同,因有高下之判别耳。由于《说苑》曾经过刘向“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 刘向、刘歆撰,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47页。]的工作,因此《说苑》被认为属于刘向的著述。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百家》虽经刘向“别集”,但其文本尚不失原始面貌,而这一面貌当与《说苑》中并非刘向所“造新事”的文本大抵近似,即《说苑叙录》所提及的“中书《說苑杂事》”。[ 此处将《说苑杂事》认为是一部书(向宗鲁《说苑校证》标点似将其看作两部。参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是因为:若“说苑杂事”为《说苑》《杂事》两部,则其间文体当有“说”与“事”之不同,《说苑》为刘向《说苑》所本,《杂事》为刘向《新序》所本。《新序》有“杂事”五篇,当即出于上述提及之“与《新序》复重者”的《杂事》。复考今本《说苑》诸章内容,“事”显多于“说”,刘向亦言“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则其亦以“事”为主,犹以“说苑”命书名,实不可通。故《说苑》《杂事》即为二书,内容性质亦必然极相近。且后人引《说苑》或名《世说》,则知“说”具有汉人普遍承认之文类性质,“事”则不具独立意义上的文类价值,而仅属于“说”的内容。由此推论,“杂事”盖无独立为一书之可能,刘向所整理中书为《说苑杂事》的概率较大。]
徐建委基于袁行霈之观点,进一步指出“《说苑》与《百家》的区别在于中不中义理……‘小说’就是‘不中义理的说’。”[ 徐建委:《说苑研究》,第97頁。]以这一见解衡量《说苑》与《百家》的区别则甚是,但若以之区分“说”与“小说”,则未免武断。因《说苑》与《百家》的区别为刘向所人为规定,但目前并无证据认定今《艺文志》之分类亦是刘向所定。如果依前述认为分类方式乃刘歆所定的话,那么《说苑》归入儒家很有可能不过是刘歆褒扬父亲著作之举,则以之作为学术划分的依据,未免失之草率。李锐指出《说苑》、《百家言》的关系近似于内外篇[ 李锐:《刘向、刘歆校书差别》,《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第188—189页。],如以内外篇角度观之,两书在理论上应依《艺文志》著录体例划归同类,即《说苑》亦当属于小说家著作,而刘向所整理的《说苑杂事》更是典型的符合刘歆定义的小说家书。徐建委还认为“说”即诸子杂记,“至晚在秦时已经具备文体或文类的含义”,并认为其属“为阐发义理的‘经’而准备的资料库”,虽概以“荀子与战国齐学”[ 徐建委:《说苑研究》,第69、71、79页。]为上源,但若以《艺文志》流派观衡量,则“说”仅具备服务功能,并不具备单独的学派意义。因此《艺文志》多类中均有以“说”命名之著作。徐氏上述见解皆旨在论述“说”体在当时之普遍性。
然这一观点实存不少似是而非之处。以“说”为书名者虽散见于《艺文志》著录之各类中,但如忽略具体所指的差异而骤以为书名凡含“说”字者皆大致相同,在逻辑论证上恐不能成立。[ 如群经中有传,《史记》中亦有“传”,两者虽有某种共同之远源,但若作为一种封域较为分明的文体,实不能认为属于同种性质。对“说”之考察似亦应如是观。]徐氏引及《艺文志》中以“说”命书名者甚多,然似皆只能理解为一种近似于传的解经体式,无一可坐实为资料库之性质,则其征引之证据效力殊为有限。
探讨《百家》之小说家性质,仍应归本诸子略的类目设置:前文既已述及小说为方士产物,那么《百家》显然无方术渊源,何以被刘歆列入该类?
这里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刘歆编《七略》时,《说苑》与《百家》已成为两部各自独立的书籍,故不论《说苑》因何归入儒家类,其性质都可以与小说家定义毫无关系;其二是《说苑》、《百家》皆出于《说苑杂事》,因此二书实际上在刘向以前是具有某种共性的整体,尽管已被拆分,但其性质当仍类似。基于刘歆的拟类思想以推理《百家》及小说家、小说的实然性质时,要认识到这一基于推论的定义不得与《说苑》产生明显的抵牾。
对此,《百家》究竟确属小说家类,抑或无类可分不得不姑且附于小说家类,则为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
假设《百家》无类可分,似即暗示《百家》的思想并不符合“兼儒、墨,合名、法”[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2页。]的杂家要求,故连“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最低标准都无法适用。如此则小说家只能是一种不合乎上述九家的流派。从《百家》与《虞初周说》的纳入同类,可以断定小说家代表的“流派”仅是出于分类方便的虚拟,其内容是杂录各种不值一提的“小”说,故无任何学理意义可言。这一见解虽已经前人论文提出,但前文已提及其违背“王官系统”的悬拟,且与小说家的实际著录相相违背。如小说家著录之《宋子》,班注“言黄老意”;《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应劭注“道家也”,则小说家并非专门著录“无宗旨”或“不同于九家”者。如将“无宗旨”引申为“无高明的宗旨”,恐亦不能成立。因各家典籍亦必多有浅薄者,不应仅有道家才有浅薄之书。以《艺文志》著录看,至少似应将各类“x家言”之属贬为“小说”[ 李锐认为“x家言”皆刘歆,“将校书之余的或数十篇或一二篇难以归类者,缀为一书而施加一总名”,其推测颇有理。李锐:《刘向、刘歆校书差别》,《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第189页。]。
那么,《百家》归入小说家而不归入杂家,就只能理解为刘歆认为《百家》相较于兼摄各家的杂家,确更合乎小说家之定义。那么,必须基于小说家类的小序为《百家》给出较合理的解释。
仅据上文考察的结论,可知《百家》具备下述特征:
其一,其文本性质基本类似于刘向所定《说苑》之文本,二者皆出于《说苑杂事》,因之文本性质是相同的。
其二,其名既为“百家”,似可推测作者非一人一派,而为刘向校书时所编定之不符合儒家观念的“百家”杂汇,故一定程度上合乎“资料库”之性质。
其三,其文本归类至少依刘歆的学术定义属于小说家类,因此必须从“小说家”之政治流派角度给其一较合理的解释。
因本文已反复说明,刘歆之分类实立足于政治流派而非文类,故其中以第三点尤须进一步阐释,方能避免旧说将刘歆理解之“小说”、传统文人一般观念下之“小说”及现代“小说研究”之“小说”三种观念混杂不清之病。且小说家著录诸书,惟《虞初周说》、《百家》之材料相对较多,《虞初周说》既与小序宗旨乖违,则《百家》与小序之关系就成为理解刘歆“小说家”观念的核心所系。
对此则首先须释“百家”篇名之义。
先秦言“百家”,盖即以一家为一种诸子学术流派,百家即泛指各种学术流派。《荀子·解蔽》言“百家异说”、《庄子·天下》言“百家众技”等皆是。具体到语境当中,似多指不属于本流派的其他流派。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于每家评价之末,皆言其长处“虽百家弗能易也”云云,似即斯义。以经学家角度观之,则百家与六艺圣人之旨相对,故秦有收去“诗书百家之语”,汉有“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皆此义,则“百家”亦为“诸子”之代名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之说。刘向既为儒家立场,则“百家言”犹“儒家以外诸子之说”,在此处之性质实际等同于《说苑》之外篇,亦可进一步证明二书确为内外篇之关系。徐建委取《百家》与《说苑》对照,认为“中义理”为二者的区分标准,实为刘向之儒家立场所惑。按应劭《风俗通义》亦引及《百家书》两条,即诸子略著录《百家》。其中一则为“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故事,观点为“喻恶之滋并中伤量谨也”[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十六《鳞介部上》引《风俗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72页。],虽难据此断定其思想流派,似亦并非“不中义理”者,更非纯粹无意义之故事。故刘向不采之入《说苑》,盖仅因其不符合刘向所认同之儒家义理,并非《百家》所言皆毫无义理可言也。
兹再试探讨《说苑杂事》之性质。据刘向《说苑叙录》,则《说苑杂事》之内容实际即等同于“《说苑》中未经刘向所增之部分”加上“与《新序》复重之部分”(应即《杂事》五篇)再加上“《百家》全書”之和。《说苑》《新序》皆入诸子略儒家类,则《百家》内容为不合乎儒家标准的“说苑”与“杂事”,而原始之《说苑杂事》则为子学各家之“说苑”与“杂事”。如此则可认定,不论是《百家》抑或《说苑杂事》,皆无某一特定之学术宗主,故其内涵兼有百家之语(区别唯有是否含儒家之言),并非与百家皆有区别。也正是因此,学者通过对《百家》之考查,进而推理认为小说家为诸子百家之资料库,实有内在根据在焉。
然存在内在根据实不等同于结论之正确。九流中既已有杂家一类,那么资料库性质的《百家》自应附入,毋庸归入小说家。姚振宗认为杂家类的《解子簿书》可能为“所簿杂书三十五篇”或“簿录诸子书而杂解之”;《推杂书》可能为“刘中垒类推诸杂书之无书名撰人者裒为此编”[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第290—291页。],虽无实据,然亦可侧面说明杂家确能收录《百家》一类著作。小说家得以在刘歆极度贬抑的情况下自立,当有其不可抹杀之特定畛域。
今人多惑于此,以为该畛域无界限可寻,实因将诸子简单等同于某种哲学思想,而忽略哲学之外的可能性。实际诸子略小序所重并不在哲学思想,而在于政治学的功用。政治功用可兼具哲学维度与技术维度,而诸子略之关注核心在乎技术维度,技术本身不必具有(今天意义上的)理论价值。故政治功用既不同,则自有独立成类之必要。[ 雷戈指出“后战国是思想试验的时代……即政治作用覆盖思想效应”(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第8—11页。),其说甚精。如纵横家小序仅言“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同时期书亦多言“短长纵横之术”,实际仅指依靠辩才进行政治活动,并无哲学思想或政治思想可言。即,其功用上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故无实际的学理可寻。所谓“实践”,即通过口头说话的方式达成某种劝说之目的(如宣传方术、讲述道理等)。但由于其“实践”方面具有共性,因此得以与其他流派区分。在九流之中,惟纵横家与小说家不少近似之处,或可推测小说家亦即类似于纵横家的一种“话术”,强以学术思想理论的角度为小说家下定义,亦无异于胶柱鼓瑟。傅斯年指出小说家出自“以说故事为职业之诸侯客”(傅斯年:《“战国子家”与<史记>讲义》,第13页。),其论述逻辑虽与本文不同,但其结论亦可得到本文之支持。]探讨小说家之定义、思考小说家与诸子各家的核心区分度,应从技术角度出发加以考察。
五 小说家定义的合流:方士与子学之间
基于上述的分析与对读,可发现诸子略小说家序文之“本质”更接近《百家》。如以《百家》作为小说家的代表,那么序文中“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等语则皆有较明确之着落。换言之,以现在可见之材料论,《百家》是唯一基本完全合乎刘歆小说家定义的著作。而其既然与其他“方士书”性质迥异,而又同为一类,那么其内在必有核心逻辑,以使得刘歆将其当作同性质的文献而加以分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桓谭《新论》,鉴于其“小说家”的提法与具体分析皆与刘歆之说有极高相似度,故似可认为《新论》相关文本实际上是对《艺文志》观念的发展。
其言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对“小说家”特征的描述更趋明确。徐建委已立足于《说苑》文本加以讨论,兹略补充:
1.合丛残小语:按“丛残”一词别见《论衡·书解篇》:“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违传之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寳。’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二十八《书解篇》第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7—1158页。]“丛残”即形容思想的琐碎凌乱。这一点合乎诸子略小序认为小说家是“小道”的看法。“小语”亦可能有篇幅长短的含义。
2.近取譬论:按譬论一词在古甚罕见,似为“譬谕”之讹。“譬喻”即“譬”,
说明小说家借某事以说明某理或另一事之修辞方式。考《战国策》、《说苑》、《汉书》诸书言“譬”者,似主要即依靠常识以说明道理。[ 陈洪认为譬论即古小说,实际上乃以现代“譬论”的眼光看待古之文本,故这一见解不能反映早期“譬”的具体所指含义。本文对“譬”、“譬喻”的理解,仅以原文明标“譬”以为限度。陈洪:《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以《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譬论的定型——以《说苑》为例》,《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出于同样的原因,笔者亦不能认同徐建委将《说苑》“枭逢鸠”寓言当作“譬论”的观点,这一故事不仅非“譬论”,似乎亦不合乎“近取”之意。徐建委:《说苑研究》,第97页。]如《说苑》卷七“宓子贱为单父宰”条“譬如高山深渊”;卷九“吴王濞反”条“譬犹抱薪救火”;《战国策》卷一“赵取周之祭地”条“譬之如张罗者”;《汉书·古今人表》“譬如尧舜禹稷禼,与之为善则行”,其中虽有虚构之动作或人物,但皆是借某一常识以说明道理,非有意虚构故事之文学史意义的“小说”。[ 徐建委认为“《说苑》中有虚构的故事,虚构的对话,却很难找到虚构的人物……可见这类故事并不是作为虚构的事类来创作和流传的……因此从性质上看,它们更像是口头流传的故事或传说的文字记录。”徐建委:《说苑研究》,第96页。]
3.以作短书:短书,字面意义即篇幅短小,内涵意则与“小说”同。《新论》言“为妄作……短书不可用”[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页。],所举例子为《庄子·寓言》“尧问孔子”及《淮南子》“共工争帝”,则《庄子》、《淮南子》并为桓谭定义之“短书”,其特性虽虚诞,却有善可择。又《论衡·书虚篇》批评“短书”乃“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四《书虚篇》第十六,第167页。]的“虚言”。此类虚妄之说可能与方士之说关系密切。而《谢短篇》言“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十二《谢短篇》第三十六,第558页。]此处言当时一般人叙“汉事”者为“短书”,与经书相对,儒者不屑于观,这里的“短书”则指一般意义上的诸子之书。故“短书”兼具二义,即:凡小说家所作皆为“短书”,但作为一般子书的“短书”作者则来源于诸子九流,并不仅出于小说家。这种杂糅的观念可代表汉人的一般思维方式。而在这种杂糅的观念下,方士之书及《百家》之书当然均可以目为“短书”,其同时也属于子学著作。换言之,“短书”、“小说”在一般运用中只是一种无明确界限的泛语。
4.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指其功用主要集中于身、家层次,未提及其是否可应用于国家政治,可说是一种有限的实践效用。此似与《艺文志》小序“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接近。
是故综合上述考论,可认为小说家的定义大致如下:
首先,如前文对《百家》文本性质的讨论,小说家在形式上当具备篇幅较短的特性。按《新论》“丛残”一词别见《论衡·书解》:“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违传之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二十八《书解篇》第八十二,第1157—1158页。]“丛残”即形容思想的琐碎凌乱。这一点合乎诸子略小序认为小说家是“小道”的看法。“小语”、“短书”等亦可能有篇幅长短的含义。
其次,考虑到《百家》文本是不入《说苑》的汰余,则当带有对其学术价值的贬低,即所谓“短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短书”与“小说”在表述上有类似之处:既可以泛指用来指代诸子之书,又可以具体贬义地指示“小说”这一类文本。《庄子·外物》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则“小说”一词最初是对异己学派政治活动的一种蔑称,与《荀子·正名》之“小家珍说”同类。其核心在于形容“说”之“小”。“小说”的意义皆为类似上述“短书”的泛指——即学者的一般称说并无“小说家”的定义,这也仍然可以加强“刘歆创小说家”的论证。
再次,小说当为一种技术,与纵横家略有类似,是一种政治技术而非理论流派。按“纵横家”一名后起,早期策士皆言“纵横短长之术”,则是“术”而非“学”。“纵横”即合纵连横,而“短长”一词费解。《汉书·张汤传》“边通学短长,刚暴人也,官至济南相。”张晏注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短术也。”[ 班固:《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2645页。]按《战国策书录》言《战国策》一本作“短长”。而张晏注“趣彼为短,归此为长”实为贬义词,取以自名,于理可疑。“短长”疑即纵横家所学之两种不同话术,代表所讲内容的长短。“小说”则是其“短”的一面,落成文字,即为“短书”。以《战国策》文本看,故事确有篇幅长短之明显差别。[ 按当“短”指内容性质时,则与经书之“长”相对;单指“说”体篇幅之长短时,似又可与纵横家“长书”“修书”之名形成对比。从内容言,纵横家与小说家亦存甚多近似之处,差别更多地在乎篇幅之长短。]“短书”既为“小说”别称,则其性质似有可类比之处。且纵横家至大一统时期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游说人主的风气及技能并未失传,取而代之产生影响的乃言行夸诞之“燕齐方士”。《后汉书·方术列传》言“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又言光武帝时谶纬流行,说者“驰骋穿凿,争谈之也”[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705页。],则方士之“小说”可能因此而成为小说话术之总代表,与“纵横家”之命名相类也。
最后,由于其内容的虚构性,小说与方士的关系格外密切。《新论》言“为妄作……短书不可用”[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页。],所举例子为《庄子·寓言》“尧问孔子”及《淮南子》“共工争帝”,则《庄子》、《淮南子》并为桓谭定义之“短书”,其特性则虚诞而近似于方士之言,这似可说明小说文本与方士的密切关系。而《虞初周说》篇幅达九百四十三篇之巨,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方士对于小说创作的热心与贡献。进一步可推测,方士说人主以神仙,盖策士说人主以纵横之变体,其兴盛时间乃在汉武帝时,故此时才有方士之话术文本流传。其历史背景乃天下大一统格局渐定,皇权高张压倒士的自我张扬,故策士所言的纵横之术语凌厉修辞均不复适应于时代,而方士所言的求仙方术与滑稽夸诞的小说言语得以取而代之。而方士之善于讲说神仙吉凶,依托传说,亦即善于“说”者,其夸诞表演的倾向似超过其实践方术的倾向,因此同样属于诸子一流,与方技、数术不同。
六 诸子略小序的文本控制与文本失控
在此基础上,似可以进一步探讨刘歆在诸子略写作中控制文本的努力。
首先,应该确认的是诸子略序文明显展露的学术建构努力。所谓“九流十家”与“出于王官”,皆为作者的悬拟,并不反映任何一个时期学术史的事实。对这些文本加以统合,并通过小序建立解释框架,正是以经学立场主导思想史解释的政治背景与学术立场的表现。即,用经学思想观念衡量各个子学流派的是非高下,并以统治的意识形态加以褒贬,而并非以子学本身的发展流变与内在缺陷作为评判标准。因此,作为一份具有“后设性”的学术文本,在阅读中应当回归其特定的时代,按照文献的本质加以分析,而非沿用旧说,圆凿方枘地用西汉末期的思想建构以解读先秦的子学世界。
其次,以小说家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其文本失控的另一面向[ 对于早期文献可能存在的文本失控现象,可参程苏东:《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失控的文本與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在研究小说家定义和起源的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两条不同的路线,而两条路线却在《艺文志》中汇合了。其一为《虞初周说》为代表的方士小说。随着皇权高张背景下的子学衰微,这一话术逐渐仅为方士一流专门游说人主者所专。方士保留其讲故事的特性,剥离其理论内涵并代以神仙思想;但其所重视在神仙故事的夸诞,又不仅在于方技本身,因此并不等同于“方技理论”。此类小说文本兴起的政治思想史背景是身体想象、神仙传说与现实政体的联系,但具体表现时倾向于一种无明确政治目的的“说”,主要供干禄之用,因此与谶纬等体虽出同源却实有区别。其二为《百家》为代表的子部小说。此即小说“资料库”的早期性质,以“可采”作为目标,又以“刍荛狂夫”等语对此深表批判。其中可能合乎儒家义理的故事既被刘向采入《说苑》(或可理解为小说文献上的去思想化),则剩余的《百家》自然仅具黜落意义,无“中义理”之内容可言。故桓谭、王充进一步推衍之,则认为小说除“可采”以外,必具备“征实”之特性,于是“史部小说”随之而兴焉。这只是代表了汉人认识小说的两种维度,其间存在理论的递进性。以观念言之,两种“小说家”的定义变化存在某种思想逻辑;但以“小说”本身之发展言之,则定义的变化实际上有意造成了“小说”实然的断裂与混乱,并成为后世小说观念芜杂的始作俑者。[ 不妨举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以进一步类比:经书本为王官之书,为先秦各家所共同掌握的知识文本。但随着各家的消歇,经书逐渐被儒家所垄断,且儒家的传记论文如《学》《庸》等更进而以经的形式进入到经学中。小说起源与发展的混乱,与此有某种形式的类似之处。]
此外,对本问题的讨论或许可以增进对《艺文志》层累过程及当时政治生态的理解。旧说多认为刘歆学术旨在为王莽篡权提供理论依据,从客观来看,《艺文志》建构学术体系与强调学术正统的工作实际上很可能产生此类效果,即话语结构对权力执行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而诸子略的编纂乃其中一部分。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艺文志》六艺略对古文经学的著录和评价,当与诸子略的著述互为表里。这一推论目前尚缺乏实证,但似有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空间。
值得顺带一提的是,在重新认识刘歆小说家定义的基础上,仍可进一步对小说理论史研究之重要问题加以更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亦必将引发对文学史研究方法论若干重要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限于篇幅,笔者将另为文章申论之。
[责任编辑 刘 培]